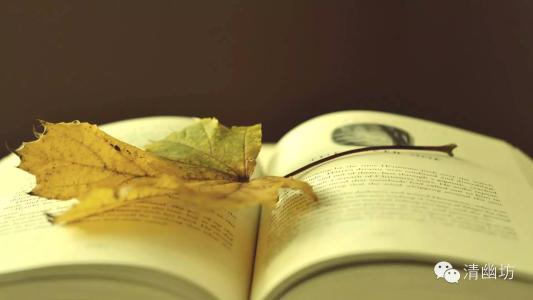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一段时期来, 中外学界出现了一种文化“世界主义”倾向, 受其影响, 在一定范围内, “世界文学”成了文学“世界主义”之代名词, 其所指是少数经济强国的文学。然而, 马克思、恩格斯、歌德等有关“世界文学”之论断告诉我们, 世界文学是多民族文学相对独立基础上的多元共存, 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即便是在“网络化—全球化”持续演进的未来, 各民族文化也将是和而不同的多元统一体, 而不是“世界主义”所期许的“强国文化”之一统天下, 世界文学也不是少数经济强国之文学。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将促进多民族文学与异质文化的互渗互补, 并拒斥文学与文化的“世界主义”倾向, 助推世界文学向“人类审美共同体”的境界发展。
关键词:
世界文学; 世界主义; 网络化—全球化; 比较文学; 人类审美共同体;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 (项目编号:15ZDB086) 的阶段性成果;
World Literature is not the Literary Cosmopolitanism
Jiang Chengyong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世界文学”“世界主义”成了中外学界尤其是欧美学界较为热门的话题, 这与全球化浪潮的演进有直接关系。“世界文学”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 对其基本内涵学界也有一定共识, 但在新语境下却被不断重新阐释并赋予新的含义 (1) 。在“网络化—全球化”背景下, 文学一方面濒于“边缘化”的处境, 另一方面, 受一种过于狭隘的“世界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 在一些研究者视野中, “世界文学”几乎成了西方少数经济大国和综合实力强国之文学, 因而文学的民族性、本土化遭到了挤压。正如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大卫·达莫若什 (David Damroch) 在《世界文学有多少美国成分?》一文中所指出的, “世界文学正在快速地变化为美国集团资本主义的怪兽” (2) 。国内学者对此也提出了警示:“世界文学”口号的背后隐藏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单一性”企图, “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明显具有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 (3) ;“世界文学”成了“‘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文学’, 或‘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学’” (4) 。在这种语境下, “世界文学”几乎成了文学上的“世界主义”之代名词, 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
如果“世界文学”仅仅是这种“世界主义”所期许的整一化的少数资本强国之文学的话, 那么, 以文学的他者性、异质性为存在与研究前提的比较文学也就毫无立锥之地, “消亡”便是其必然归宿, 若此, 它也许就是全球化和“世界主义”酿就的文学领域的牺牲品。人类文学的发展果真会如此吗?这是亟待深究与澄清的重要问题。对此, 我以为, 回顾“世界文学”术语与观念产生及传播的历史, 特别是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和歌德等关于“世界文学”的重要论断, 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全球化势头日显强劲的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发展趋势, 探究文学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 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何谓“世界文学的时代”?
在我国学界, 一说到“世界文学”, 往往首先会想到歌德, 因为, 虽然歌德并不是第一个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术语的人 (5) , 但他的关于“世界文学”之论断的影响, 却大大超过了前人。因此, 究竟谁先使用这个术语已显得无关紧要, 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 有必要首先分析歌德对“世界文学”的理解。
1827年, 歌德在与秘书爱克曼谈话时提到了“世界文学” (Weltliteratur) 一词:“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 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 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 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 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 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 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 (6) 当时, 歌德是在阅读了中国的传奇小说《风月好逑传》等作品之后, 说出上述这番长期以来被学者们广为引用的著名论断的。在歌德一生的文学评论言说中, 他曾经20多次提到“世界文学”这一术语。
总体而言, 歌德对“世界文学的时代”的展望, 是基于国与国之间封闭、隔阂的日渐被破除, 从而使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与文学交流不断成为可能而言的, 其前提是诸多具有文化差异性的民族文学的存在。因此, 歌德说的“世界文学的时代”的人类文学, 并不是消解了民族特性与差异性的文学之大一统, 而是带有不同文明与文化印记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学同生共存的联合体, 是一个减少了原有的封闭与隔阂后形成的多民族异质文学的多元统一。正是在这意义上, 歌德又说:“我愈来愈深信, 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 (7) 因为, 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超越民族文化价值和审美趣味的局限, 为异民族的读者所接受, 为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从而促进异质文化与文学的交流。歌德说:“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 充满朝气并努力奋进的文学家们彼此间十分了解, 并且由于爱好和集体感而觉得自己的活动应具有社会性质。” (8) “我们想只重复这么一句:这并不是说, 各个民族应该思想一致;而是说, 各个民族应当相互了解, 彼此理解, 即使不能相互喜爱也至少能彼此容忍。” (9) 这里, 歌德认为不仅仅是个体的作家在“彼此间十分了解”的基础上保持了各自独特的创作个性, 而且, 异民族、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也是在“彼此理解”“彼此容忍”———实际上是包容———的基础上, 保持了自己独特性的同时又以其超越民族与文化的优秀个性而开放于世界文学之大花园。就当时的歌德来说, 他不仅展望和预言“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而且尤其期待“德意志人在这方面能够、也应该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并且将在这一伟大的共同事业中扮演美好的角色” (10) 。他还相信:“在未来的世界文学中, 将为我们德国人保留一个光荣的席位。” (11) 此处, “共同事业”、“扮演美好的角色”和“保留一个光荣的席位”, 都意味着“世界文学的时代”的“世界文学”是一个由不同民族之文学经典组成的文学共同体, 而在这个“共同体”里, 以歌德自己已有的成就以及他对德国民族文学的信心与期待, 德国人创造的文学经典将会独树一帜、光彩夺目, 进而拥有“光荣的席位”。对此, 丁国旗的分析是精当的:“各民族的文学‘经典’不过是‘世界文学’属下的一个个‘范本’, 正是这些无数个‘范本’向我们展现了‘世界文学’所应该具有的存在方式。” (12) 今天看来, 不仅歌德已经成为世界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家, 而且, 德国文学也已然是世界文学大花园里的一朵鲜艳的奇葩, 为世界文学的存在“范式”提供了经典的样本。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时代”, 展望的是生发于诸多异民族、异质文化的文学经典众声合唱的世界文学大家庭, 那显然不是同质化、一体化、整一性的文学存在形态;歌德“世界文学设想的中心意义, 首先意味着文学的国际交流和互相接受” (13) 。
二何谓“世界的文学”?
在我国学界, 比歌德“世界文学的时代”的概念更有影响力和指导意义的“世界文学”观念, 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的文学”的论断。对此, 我国学界的同仁已颇为了然, 但是, 在“网络化—全球化”的当下重提“世界文学”的话题, 我们有必要重温并细辨其精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 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 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 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 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 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 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替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14)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 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他们上述的论断, 一方面指出了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物质、经济的世界性发展总特征, 指出了带有国际性质的经济运行方式使各民族、各地区和各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已纳入到了世界性大格局之中, 于是, 那种封闭的、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宗法制和田园牧歌式的经济体制、生存方式乃至生活方式, 逐步走向了边缘乃至消亡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特定时代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是受这个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的, 不仅物质生产, 而且包括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在内, 都受资本主义世界性生产的影响, 这些社会意识形态乃至所隶属的一切思想、思潮和观念, 都是从它们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扩张与征服, 不仅存在于商品交换涉及的领域, 而且也涉及精神、文化领域。这意味着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也会在物质、经济的世界性扩张与征服中趋于世界化。虽然, 人类精神的生产有自身的规律,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存在着不平衡性, 但是, 精神生产不可抗拒、不同程度地要受制于物质生产之大趋势的影响。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在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的背景下, 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在经济和物质生产方式国际化强势的推动下, 将形成“世界的文学”, 于是“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15) 。
值得仔细辨析的是, 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世界的文学”, 是在“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 (16) 的基础上形成的, 换句话说, “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的独立存在与互补融合, 是“世界的文学”产生与形成的前提。因此, 在马恩的“世界文学”观念中,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世界文学”是基于文化相异的多民族文学各自保持相对独立性基础上的多元统一之文学共同体, 是民族性与人类性 (世界性) 的辩证统一, 而不是大一统、整一性的人类总体文学。这与别林斯基的观点不谋而合。别林斯基说:“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 才是真正的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的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 才是真正人类的。” (17) 也正如美国当代著名比较文学专家大卫·达莫若什所言, 世界文学是“在本民族文化以外传播的文学作品” (18) , 或如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雷泽 (Matthias Freise) 所言, 世界文学的“核心问题是普适性与地方性的关系……世界文学的理解首先是从差异性开始的” (19) 。这些学者和理论家的论断, 都从不同时代的不同立场和角度说明:世界文学不是整一化的人类文学统一体, 而是诸多国家和民族文学的多元融合体。虽然国内外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解迄今仍然是众说纷纭, 但上述关于“世界文学”的基本内涵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文学研究者们已达成的一种基本共识, 其中,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无疑更具前瞻性和普遍指导意义。
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从文化交流与影响的角度看, “这种片面性”和“局限性”之“成为不可能”, 不等于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独特性的消失, 而主要是指在不同质的文化与文学彼此取长补短基础上的优化发展与演变, 使既有民族性又有人类性的元素得以在交流中弘扬;也就是说, “成为不可能”或者在交流中“消失”的, 是各民族文化中惰性和狭隘性意义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元素, 而不是足以彰显其独特性、优质性意义上的特色与优势元素。因此, 从总体趋势看, 在人类文学朝着世界文学方向发展的同时, 或者说在“世界的文学”形成的同时, 民族文学的个性、特色与优势会不同程度地得以保留抑或彰显而不是销蚀。不仅如此, 不同的文学与文化并不存在优劣之分, 而只有特色之别, 有包容性与互鉴性, 其生存与发展并不像自然界那样遵循自然选择的“丛林原则”。即使是面对物竞天择的自然界, 人类也有责任保护和捍卫自然物种的多样性存在, “当前, 有关环境恶化的全球化最可怕的问题或许是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而“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背景” (20) 。因此, 站在人道的高度看, 人类必须维持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发展, 其间体现的是生态伦理观念。与之相仿, 站在人类文学与文化存在之多样性、多元化之必然前提看, 各民族文学的特色与优势也更须得到有效尊重与保护, 使其有各自生存、延续与发展的空间, 其间体现的是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文化伦理观念。由是, 人类文明也就不一定必然表现为“文明的冲突”, 而是互补、融合、共存, 世界文学也就有了多元共存的文化伦理前提。正如杜威·佛克马 (Douwe W.Fokkema) 所言, “世界文学的概念本身预设了一种人类拥有共同的秉赋与能力这一普适性观念” (21) 。
三“世界文学”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在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以往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观的理解, 一般只认为那是他们对人类文学发展趋势的预测与展望, “世界文学”仅仅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预言”而已, 实际上是无法实现和实证的, 甚至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22) 。其实, 我认为, 从19世纪欧洲和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看, 马恩的这种展望和预言,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以实现和验证, 因而这种理论有其科学性和普遍真理性。在此, 我们不妨以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思潮的演变为例略做阐述。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最波澜壮阔的文学思潮, 也是欧洲近代文学的两座高峰。就欧洲文学或西方文学而言, “文学思潮”通常都是蔓延于多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 同时, 它必然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某种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大致相同的美学倾向、创作方法、艺术追求和广泛影响的文学潮流。更具体地说, 凝结为哲学、世界观的特定社会文化思潮 (其核心是关于人的观念) , 乃文学思潮产生发展的深层文化逻辑 (“文学是人学”) ;完整、独特的诗学系统, 乃文学思潮的理论表达;流派、社团的大量涌现, 并往往以运动的形式推进文学的发展, 乃文学思潮在作家生态层面的现象显现;新的文本实验和技巧创新, 乃文学思潮推进文学创作发展的最终成果展示。笔者如此细致地解说“文学思潮”, 意在强调:19世纪欧洲和西方的“文学思潮”通常是在跨国阈限下蔓延的———它们每每由欧洲扩展到美洲乃至东方国家———其内涵既丰富又复杂,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才可能深度理解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思潮所拥有的跨文化、跨民族、跨语种的“世界性”效应及其“世界文学”之特征与意义。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wenxuelunwen/3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