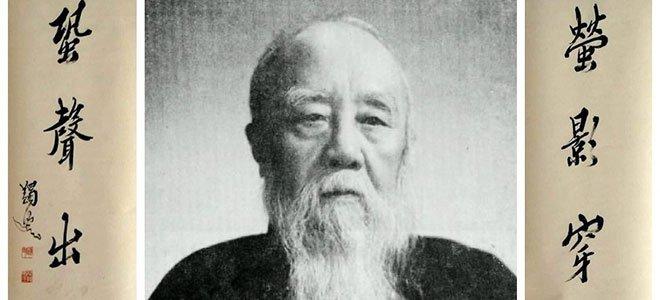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日常生活诗学的核心内涵, 是揭示日常生活内部所蕴藏的各种微妙繁富的生命镜像, 重构人类身与心、人与物的统一性。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 这一诗学逐渐成为中国当代作家的自觉追求, 并在创作实践中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趋于成熟期等三个阶段。在具体创作中, 它体现出辩证而多元的价值观、平等而质朴的生命观、自由而精细的文本形态等主要审美特征, 但也暴露出作家对世俗欲望的过度张扬、创作主体审美视野狭窄、一些作品审美意蕴单薄等审美局限。随着日常生活本身的不断丰富和作家们对其自觉地强调, 可以看出, 日常生活诗学的重构, 已反映出当代作家对生命整体性的关注, 也预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趋势。
关键词:
日常生活; 诗学; 重构; 当代文学; 整体性;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研究” (项目编号14AZW002) 之阶段性成果;
Discourse on Reconstruction of Daily Life Poetics
Hong Zhigang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 琐碎而平淡的日常生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受到作家们的重视。有些作品虽然以日常生活为底色, 但创作主体所追求的, 仍是其背后所负载的社会或历史意义, 并非日常生活本身的审美价值。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 随着“南方生活流”诗歌和“新写实”小说的兴起, 当代作家逐渐转向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密切关注与表达。90年代之后的“个人化写作”思潮, 再度强化了这一审美特征。新世纪以来, 随着“70后”“80后”等青年作家群的不断崛起, 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更是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审美倾向。认真审视这一审美倾向, 我们会发现, 它既体现了当代作家对重构人类生活完整性的自觉追求, 也隐含了创作主体对身与心、人与物之间统一性的重建理想, 同时还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趋势。
一
所谓日常生活诗学的重构, 是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念之上的一种创作实践。它的核心内涵并不是否定或回避重大的社会或历史生活, 也不是刻意排斥或颠覆一切宏大话语, 而是在尊重它们的同时, 更加自觉地立足于普通个体的生存经验和存在境遇, 注重物质性、身体性和体验性的审美表达, 突出那些看似琐碎、惯常的世俗生活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意义, 揭示日常经验内部所蕴藏的各种微妙繁富的生命镜像。它的主要目标, 是强调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注, 发掘并展示日常生活中极为丰盈的生命质感和人生意绪, 以便重构人类在身与心、人与物上的统一性, 即杜威所强调的“一个经验” (1) 。
从表面上看, 日常生活似乎平淡无奇, 千篇一律, 充满了程式化和世俗性的特征, 但它却是一个包容性和消融性都极强的概念。按照本·海默尔的说法, 日常生活一方面“指的是那些人们司空见惯、反反复复出现的行为, 那些游客熙攘、摩肩接踵的旅途, 那些人口稠密的空间, 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天又一天 (但是并不对它们作出判断) 。这是和我们最为切近的那道风景, 我们随时可以触摸、遭遇到的世界” (2) 。然而, 它并非稳固不变, 而是在现代性的进程中, 以不易觉察的动态方式, 呈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和消融性, “使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了;逐渐对习俗的溃决习以为常;努力抗争以把新事物整合进来;调整以适应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日常就是这个过程或成功或挫败的足迹。它目睹了最具有革命精神的创新如何堕入鄙俗不堪的境地。生活中所有领域中的激进变革都变成了‘第二自然’。新事物变成了传统, 而过去的残剩物在变得陈旧、过时之后又足资新兴的时尚之用” (3) 。正是这种复杂多变的包容与消融, 才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异常驳杂, 同时又摇曳多姿。所以, 伊格尔顿由衷地说道:“日常生活就像瓦格纳的歌剧, 错综复杂、深不可测、晦涩难懂。” (4)
日常生活的复杂与晦涩, 不仅在于它以动态化的方式, 承载了人类社会演进与文化变迁的丰富信息, 还在于它以无穷无尽的手段, 对每个个体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进行了潜在的文化规约。“在人类社会, 不仅是性, 人类废弃物的排泄也受文化的管制……若一个人对于某事的反应是习得的, 那么他就是被一种文化规范所塑造而不是被‘本性’塑造的。” (5) (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因此, “要理解日常生活, 我们就要明白, 日常活动的形塑不仅受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 而且受人们身处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 每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情境都是多元的、并且是交叉重叠的。” (6) 每个人既是生命的存在, 也是文化的存在, 日常生活在其程式化的内部蕴含了无限丰富的文化信息, 使每个人像鱼活在水中一样生活于其中。同时, 这些文化经过不断地消融与发酵, 还滋生出更为高级的文化形式。卢卡契就曾指出:“如果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 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而且, 这两种更高形式的文化之最终目标, 还是“为了更丰富、更深入地解决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 (7) 。因此, 在卢卡契看来,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 “人们的日常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 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 (8) 。的确, 就每个个体的人来说, 无论他的生命有多么漫长, 也无论他的身份或地位有多么特殊, 日常生活都将占据他全部生活的核心地位, 而他面对日常生活的态度, 也将展示他的生命情趣、文化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品质。文学作为“人学”, 若要揭示人性深处的各种奥秘, 若要发掘生命内部的各种矛盾性及其可能性, 就不能忽略日常生活特有的价值。因此, 一个优秀的作家, 在关注一切社会历史重大问题的同时, 还应该放低自己的精神姿态, 沉入各种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 体察与捕捉不同生命特有的生存镜像。只有这样, 他才有可能在更为深广的视野与丰沛的情感中, 真正地揭示人性的微妙与生活的丰饶, 并有效传达创作主体对人类生存及其可能性状态的探索与思考。
应该说, 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 日常生活虽然没有作为一种理论问题被系统地建构出来, 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 仍一直得到诗人和作家们的自觉尊崇。这一点, 从唐诗、宋词中的大量作品一直到《金瓶梅》《红楼梦》等, 都可以得到印证。然而, 我们也必须承认, 受到特定历史文化使命的影响, 自20世纪以来,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中国文学的主脉都是沿着民族化、集体化的“载道”意愿在发展。这是由中国社会不断变革的政治文化思潮所决定的。在这种共识性的“载道”思维影响下, 人们已习惯于从宏观的历史语境中来认识生活的价值, 并形成了一种“集体生活观”。这种生活观的特点是, 突出集体意志和社会历史需要对于大众生活的重要作用, 强调个体存在的共识性价值和理性意义, 生活的核心价值常常被等同于社会的主导性价值, 并呈现出明确的形而上的精神特质;而作为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和丰盈独特的生命体验, 因其带有形而下的世俗意味, 则一直处于遮蔽状态。这种生活观无疑是有些片面的, 它呈现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对文艺创作的特殊要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 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尊崇宏大而理性的群体性生活书写, 聚焦社会或历史的重大问题, 强调个体生存的理性意义, 追求全景式、史诗性的写作方式, 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然而, 到了20世纪8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 中国作家开始逐渐认识到, 要让文学真正地回到“人学”轨道, 日常生活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审美领域。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无数个体的人组成的, 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取决于每个个体生活的丰富性, 尤其是日常生活的丰富性, 包括物质需求、身体觉醒、感官满足等形而下的世俗欲求。一个真正完整的人的生活, 应该既包括集体性、共识性的“宏大生活”, 也包括个人化、碎片化甚至是非理性的“私人生活”, 就像列斐伏尔所说的那样, 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纽带和共同根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 才能以完整的形态或方式体现出来” (9) 。不错, 日常生活在经验化的表象上确实具有高度的同质化特征, 但是, 如果从理性层面上来认真思考, 我们就会发现, 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状态可能被经验为避难所, 它既可以使人困惑不解, 又可以使人欢欣雀跃, 既可以让人喜出望外, 又可以使人沮丧不堪” (10) 。可以说, 日常生活使每个人作为生命与文化存在的丰富性, 都获得了极为生动的呈现。而且, 社会结构变化愈快, 经济行为愈活跃, 人们的日常生活便会愈显活力, 其包容性和消融性也会变得愈加强大, 每个个体的生存形态及其精神风貌也因此变得异常丰实和复杂。
进入90年代以后,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 特别是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兴起, 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为纷繁复杂, 人们对日常生活质量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 选择的空间也越来越大。这也使当代作家们进一步意识到, 以前那种特定情境下被简化了的“宏大生活”, 已不能涵盖今天生活的全部;物质、欲望、技术、情感等在现代社会里所占据的地位日益重要, 也成为每个个体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那些看似庸常的普通生活, 不仅对于个体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且其本身也蕴含了无限丰富的生命镜像及其艺术特质。在这种认识的驱动下, 越来越多的作家对日常生活诗学有了相对明晰的认知, 并形成了高度自觉的创作理念。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说, 日常生活诗学的重构, 体现了中国当代作家对人的完整生活的一种审美建构, 对变动不居的现代生活的严重关切, 以及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全面理解和尊重。它既体现了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 也试图对文学过度专注于宏大生活书写进行自觉的纠偏。这一诗学观念的形成, 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也是文学自身的历史诉求。
二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 真正触及日常生活诗学的创作实践, 应该是新时期之后的80年代初期。当时, 汪曾祺、孙犁、林斤澜等少数经验丰富的作家, 开始在《受戒》《大淖记事》《芸斋小说》《矮凳桥风情》等短篇小说中, 自觉捕捉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细微之处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微妙的生命情态, 努力发掘日常生活本身所蕴含的各种富有深意的“滋味”, 展示各种小人物在世态民情、伦理风俗中的命运变化, 对日常生活诗学体现出较为明确的自觉意识。但是, 当代作家在整体上自觉形成日常生活的诗学观念, 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 并且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趋于成熟期这样三个阶段。
在新时期文学初期, 作家们主要是沿着“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这两个维度来展开创作的。无论是“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还是“改革文学”, 都表达了人们终结过去、开创未来的强烈意愿, 并与整个社会的集体意志形成了紧密的共振。当然, 其中也有不少作品展示了人们对个体尊严、个人情感的强烈吁求, 并透露出某种人本主义的启蒙倾向, 如舒婷的《神女峰》等诗歌, 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 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到快车道, 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变得日趋丰富, 个人的生活空间在不断扩大, 人们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变得自由、宽松而从容。“南方生活流”诗歌适时而生, 其代表诗人有于坚、韩东、柯平、伊甸、王小龙、傅天琳、李钢、筱敏, 等等。尽管这个群体十分松散, 不存在任何组织和宣言, 但他们一反“朦胧诗”的理性化和象征化, 注重对日常生活情趣的发掘, 强调对生活本体的诗意呈现, 并以贴近生活的口语化方式, 消解诗歌语言的过度象征与隐喻。“他们无意教训人们什么, 或者开导人们什么, 只是作为一个目击者、亲身参与者, 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经验的平民感受, 拿来和你交谈交谈, 信不信由你。” (11) 像韩东的《我们的朋友》、于坚的《尚义街六号》、柯平的《中国农村纪事:1985》, 等等, 都是将情节化的叙事融入抒情之中, 努力呈现日常生活的原生态韵致, 看似平淡无奇, 却又耐人咀嚼。所以, 有学者认为:“从‘今天’派到‘生活流’, 给人的感觉似乎从一个辉煌的理性高度一下子直坠平地, 揪人心肺的悲剧美被稀释成了日常的悲欢离合、柴米油盐、恩恩怨怨, 遇罗克式的悲壮的殉身, 被无穷无尽的日常烦恼所置换, 温情脉脉的优雅诗意被更加实在、更难对付的世俗人情所取代, 人的价值不是在生死抉择的片刻之间受到考验, 而是在千头万绪的外界周旋和内部耗损中受到检验。” (12) 的确, 盘旋于日常生存感受的“南方生活流”诗歌, 多少有些琐碎、平实, 个体性的感受远大于理性的思考, 但它无疑较早地体现了创作主体对日常生活诗学的建构意愿。可以说, 这一群体, 明确超越了“朦胧诗”的理性启蒙与英雄主义理想, 自觉返回到日常生活之中, 努力展示那些富于生机的日常生存状态, 寻找生命的自然体验和人生意绪。
比“南方生活流”诗歌稍晚兴起的“新写实”小说, 则进一步确立了日常生活的诗学价值。以方方、池莉、刘震云、刘恒等代表的新写实作家, 面对异常繁驳的现实生活, 主动放弃集体化的审视眼光, 而以极具亲和力的、平等的叙事姿态, 捕捉日常生活中各种“毛茸茸”的生存状态, 还原普通平民鲜活而灵动的生命质感。池莉就曾说道:“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 还有世俗的语言, 以便我与人们进入毫无障碍的交流, 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命的视点。” (13) 世俗性, 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标志, 它隐含了作家对人的某些自然属性的认同, 也凸现了日常生活诗学中必不可少的世俗情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陈思和强调:“新写实小说的革新意义, 首先就在于使生活现象本身成为写作对象, 作品不再去刻意追问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 而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 及生存中感性和生理层次上更为基本的人性内容, 其中强烈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学过去少有的生存意识。” (14) 尽管“新写实”小说大多表现的是底层百姓无序而又无奈的生活境况, 呈现出日常生活的灰色调, 但它从缭乱的日常内部揭示了生命在感性层面上的丰茂与芜杂, 也突出了日常生活对于个体生存的绝对意义。因此, 从“南方生活流”诗歌到“新写实”小说, 有关日常生活诗学的审美理念, 已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初步形成。
但这一审美理念获得真正的发展, 还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个人化写作”思潮的迅速崛起, 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作家对个体生存价值的深入思考, 也使他们对个体性的日常生活价值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作家们在着力表现个体存在的同时, 尤为注重个体的自我感受与体验, 强调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性、欲望化、时尚化与个体生存意识之间的紧密关系, 并带着对个人生活价值空间的重构意愿。如陈染就曾毫不含糊地说:“没有个人, 妄谈‘人民’。没有个人, 所有的高调都是空的。而所谓的代表着‘群体’的‘大我’的脸谱, 或者过度强调普遍意义的所谓‘典型性’, 这个陈旧的格式其实除了千人一面、雷同复制之外, 什么也没有。” (15) 林白也说道:“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 通过个人化的写作, 将那些曾经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 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 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集体、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 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 (16) 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的韩东也谈道:“我们对尘世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小快小乐、小财小色充满了依恋, 无法真正摒弃, 并不虚无。” (17) 从这些代表性作家的言辞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个人化写作”主要是为了证明, 任何普通卑微的个体, 其存在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任何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小快小乐、小财小色”, 都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生命存在的丰富性之所在。因此, 从本质上说, “个人化写作”思潮是试图通过探究个人世俗生活的欲求、建构个人日常生活空间的方式, 突出人们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关注, 隐含了作家对人类身与心、人与物相统一的精神诉求。
在这种“个人化写作”思潮的驱动下, 一些新历史小说也越来越注重对历史时空中日常生活诗学价值的发掘。像苏童、叶兆言、格非、李锐、杨争光、王安忆等很多作家都将眼光投向民间化的稗史, 自觉抛弃历史的可勘证性, 将原本由史料建立起来的真实性, 全部由个人想象的艺术真实所取代。他们不再将历史的反思作为主要目标, 而是沉迷于历史的皱褶之中, 着眼于民间化的逸闻轶事、个人命运、家族沉浮, 在个人化和碎片化的历史镜像中, 饶有意味地书写那些普通人的命运走向与人性景观。在这类小说中, 宏大的英雄史完全被日常情态下普通人的苦难经历和心绪所取代, 即使帝王将相, 也都在日常生活语境中脱下了“伟大”的外衣, 呈现出普通人的生命质色, 洋溢着原初、随意、自由、平凡的生存意趣, 与精英文化格格不入。如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杨争光的《棺材铺》、李锐的《银城故事》、王安忆的《长恨歌》等, 都是如此。这些微观化、碎片化和平民化的叙事, 将日常生活视野延伸到历史记忆之中, 进一步拓展了日常生活诗学的审美空间。
与此同时, 90年代后期兴起的“底层写作”, 也同样张扬了日常生活的诗学价值。不错, “底层写作”无疑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况和内心困顿的关注, 带着创作主体非常明确的道德感和责任感, 隐含了宏大生活的微观化处理策略。但是, “底层写作”中的大量作品 (像铁凝、王祥夫、刘庆邦、王安忆的一些短篇小说, 郑小琼的诗歌等) 所体现出来的对日常生活的焦虑性表达, 既揭示了市场经济驱动下的现代日常生活之无序性、混杂性和欲望化倾向, 也呈现出很多底层民众尤其是进城务工人群对于这种现代日常生活的无奈和无助。无论是其表达视点还是审美情趣来看, 都体现出作家对日常生活自身的内在发掘, 也展示了日常生活诗学应有的美学向度。因此, 就日常生活诗学的重构而言, 90年代的文学已从多方位对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推进。
新世纪之后, 随着“70后”和“80后”作家群陆续涌入文坛, 除了韩寒等极少数带着青年亚文化情绪的写手之外, 绝大多数人从写作的开始, 便自觉尊崇对日常生活的诗学表达。他们既不关注宏大的历史记忆, 也不热心于重大的现实问题, 而是专注于当下生活、个体欲望以及青春成长的审美表达。他们天生就迷恋于各种生活“小事”。他们感兴趣的, 常常是“生活中那些细微、微小的事物, 像房屋, 街道, 楼顶上的鸽子, 炒菜时的油烟味, 下午的阳光……”, 因为“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在‘日常’中, 就是说, 处在这些琐碎的、微小的事物中, 吃饭, 穿衣, 睡觉, 这些都是日常小事, 引申不出什么意义来, 但同时它又是大事儿, 是天大的事儿, 是我们的本能” (18) 。如金仁顺就说道:“我没有想过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 任何高大的理想, 跟我好像都不沾边儿。但有句话是对的, 我手写我心。正如我的写作会下意识地描摹我的生存状态, 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一样, 随着写作时间的加长和作品数量的增加, 我也在不知不觉地营造我的文学世界吧。我的文学世界就是我小说里的那些人物和事件, 它们记录了当下社会中的一小块生活空间。我希望它是有意义的, 希望有一部分读者能在这里找到认同感。” (19) 作为新生力量, 他们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力军, 这也意味着他们所追求的这一诗学理念, 将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向。
三
通过历时性的简要梳理, 可以看到日常生活诗学的重构, 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种不可忽略的发展趋势。或许它不具备广袤而宏阔的精神视野, 也缺乏一些精深博大的思想内涵, 但它在反映普通个体的生存情状及其生命形态上, 在重构人类生活的完整性上, 却更为全面地体现了人本主义的基本特质。细察这一创作实践的内在追求, 我们可以借助相关的文本分析, 揭示这种日常生活诗学所呈现出来的一些重要审美特征。
首先, 是辩证而多元的价值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经济结构的转型, 从城市到乡村, 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已变得丰富而多元, 远远超出了油盐柴米之类的简单事象, 且呈现出巨大的扩容状态和吞吐能力。这种客观的日常情境, 意味着人们对日常生活的选择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多变性, 也意味着作家们在书写日常生活时, 必然会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事实也是如此。首当其冲的, 就是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倚重。由于长期经受物质匮乏的窘迫, 当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之后, 人们的内心欲求也在不断放大。很多作家们都对这种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进行了别有意味的探讨。如池莉的“人生三部曲”中, 从婚礼的礼仪、孩子的奶粉到工资调级, 围绕印家厚夫妇的各种生活烦恼, 几乎都离不开物质和金钱。这种物质欲求不是因为他们绝对的贫穷, 而恰恰是与整个社会环境 (包括同事和朋友) 相比, 他们还难以获得内心的平衡。何顿作品中的很多人物, 如雷铁 (《告别自己》) 、何夫 (《生活无罪》) 、何斌 (《我们像葵花》) 、宁洁丽 (《太阳很好》) 、马民 (《荒原上的阳光》) 等, 也对物欲化的现实表现出强烈的企慕和积极的参与意识;在他们看来, “个体户并不费什么事且也没有丝毫愿望, 却把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改变。以前积金千两, 不如明解经书。现在, 大家都向钱看了” (《我们像葵花》) , 于是他们投身到各种商机之中, 有时甚至还玩些坑蒙拐骗, 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财富的聚集, 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这种物质生活的追求, 在“80后”作家笔下更为普遍, 并且直接转化为时尚品牌和奢侈品的炫耀, 如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中, 就充斥了各种世界名牌的表述, 几乎每个青年男女身穿手拿的东西, 作者都要指出其品牌名称, 品牌符号成为人物身份的重要表征。
与此同时, 有些作家则极力发掘普通民众内心的诗意生活, 彰显他们对精神自足的追求。如迟子建的《起舞》里, 丢丢宁愿放弃一切, 也要守着那幢象征浪漫情爱的半月楼, 并精心保存着那条舞裙。同样, 在她的《鬼魅丹青》里, 卓霞对服装剪裁的专注和执着, 也洋溢着一种浪漫、唯美和自由的理想气息。王安忆《骄傲的皮匠》里的鞋匠根海, 也是以自己的纯朴、真诚与自律, 赢得了都市人的尊敬, 甚至情爱。徐则臣的《居延》里, 少女居延只身来到茫茫的京城, 历经了无数的屈辱和磨难, 最终只是为了给爱情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些人物都是来自底层, 但他们的骨子里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生命冲动, 洋溢着物质之外的诗性气质和执着的精神信念。
对一些传统世俗伦理进行反思, 并维护现代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人性欲求, 也是一些作家重点探索的目标。如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姊妹》等, 就借助男女之间错位的情感生活, 表达了中国女性宽厚善良的内心品质与相互抚慰的体恤之情。笛安的《南方有令秧》则在历史时空中, 叙述了令秧被丈夫家族作为贞洁牌坊严加管束的抗争史。虽然令秧的反抗是静默的, 偷偷摸摸的, 但她是执着的, 无怨无悔的;她以自我的本色追求, 颠覆了牌坊在道德上的虚伪与廉价。艾伟的《小满》中的少女小满, 承受着改变家庭贫困的重任, 替人代孕生子, 结果母性意识觉醒, 使她无法践行先前的承诺, 以至被逼致疯, 体现了作者对某种庸俗家庭伦理的尖锐批判。张怡微的《细民盛宴》讲述了少女袁佳乔在成长过程中与继父继母相处的复杂情感。她参加了无数次的家族“盛宴”, 并在每一场“盛宴”中感受着市井人物之间的精明、计较、攀比, 以及虚假的客套, 琐碎的日常中尽是说不完的世态炎凉;所谓的亲情伦理只是一个空洞的外壳, 或者说只是一次次各怀心思的“盛宴”之借口。
当然, 对边缘个体独特生存方式的维护, 也是很多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极力尊崇的价值理念。像金仁顺、戴来、盛可以、李修文、孔亚雷、孙频、甫跃辉的很多小说中, 人物大多处在都市的边缘, 且置身于各种变动不居的快节奏生活中, 对都市外在的群体性环境表现漠然, 只关注于个体之间的情感纠葛, 突出个人生活方式的不可屈从。如金仁顺的《水边的阿丽狄娜》、戴来的《练习生活练习爱》、李修文的《滴泪痣》、盛可以的《道德颂》、孔亚雷的《小而温暖的死》, 等等, 都是侧重于表现青年人在变幻不定的现代都市中的内心感受, 且不乏精神上的分裂与错位, 以及情感上的漂泊感, 但他们对都市生活却又是难舍难离。这些作品其实折射了都市在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出来的另一种日常景象———独立而幽闭, 却拥有我行我素的自由。
无论是强调物质生活还是彰显诗意生存, 是重审世俗伦理还是维护个人独特的生存理念, 从本质上说, 当代作家面对日趋繁杂且异质纷呈的日常生活, 都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与表达, 而且从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而言, 具有辩证且多元的审美特征。
其次, 是平等而质朴的生命观。从“南方生活流”诗歌和“新写实”小说开始, 当代作家就明确地选择了民间化的表达立场, 以平等的眼光和心态, 着力书写一个个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甚至是一些被忽略的生存群体的生命情态, 包括进城务工群体、乡村留守妇女、普通市民、个体户, 等等, 可谓芸芸众生, 包罗万象。如池莉的“人生三部曲”和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等, 就完全以平实的语调和人物自身的心绪, 呈现了城市职工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烦恼, 包括柴米油盐、礼仪风俗、人情往来之类的力不从心。刘庆邦、王祥夫、范小青、徐则臣、郑小琼的一些作品, 常常从人物的心理意绪出发, 书写了形形色色的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尴尬与困顿;这些人物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 常常与城市秩序发生各种意想不到的冲突, 但他们依然带着自己的梦想, 努力创造自己的生活空间。毕飞宇《推拿》、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作品, 则叙述了残疾人的日常生活, 他们用自身独特的交流方式, 生动地展示了自己的喜怒哀乐, 也维护着日常的家庭伦理。孙惠芬《吉宽的马车》、林白《妇女闲聊录》等, 平实地再现了农村留守妇女在自由自在的表象之下, 内心世界的各种烦乱与焦虑, 有精神的, 情感的, 也有身体欲望的。何顿的《我们像葵花》《生活无罪》和阿来的《轻雷》等作品, 则以非道德化的叙事, 饶有意味地呈现了90年代个体户的财富梦。田耳的《天体悬浮》、艾伟的《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南飞雁的《红酒》《空位》、范小青的《你的位置在哪里》等, 生动地叙述了各种基层公职人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际遇, 包括人际间的微妙关系, 自我角色与内心欲望的冲突。王安忆的《阁楼》《逐鹿中街》《悲恸之地》, 金澄宇的《繁花》以及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 都是立足于市井之中, 以一种世俗情怀, 着力展示人们在日常生活内部的生存情状, 或精明务实, 或怀抱梦想, 或醉心俗务, 或专注巧技, 纠葛之中不乏痞气, 体恤之中亦见真情;他们是小市民, 却以自己的酸甜苦辣, 凸现了日常生活的丰厚滋味。
当然, 更多的还是青年作家笔下都市男女的日常情感生活, 像潘向黎、金仁顺、盛可以、张楚、朱辉、鲁敏、钟求是、弋舟、孙频、张悦然等作家的大量小说, 都是专注于各种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 有唯美而浪漫的, 也有恶俗而粗鄙的, 但更多的是观念与性格的错位, 是欲望与梦想的分裂。读这类作品, 我们会看到人类情感在消费主义的现实境域中, 已经被各种功利性的目标所劫持, 两性情感只是人物之间产生关联的纽带, 或者说只是人物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合理道具, 最终所推衍出来的, 则是各种尴尬而荒诞的生存景象。正是这些饱受荒诞折磨却又不断自我折腾的人物群像, 生动地呈现了现代日常生活在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上的快速变化。
如果我们再看看那些新历史小说, 如苏童的《妻妾成群》《米》, 王安忆的《长恨歌》, 须兰的《千里走单骑》《红檀板》, 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等, 其中的人物面对种种世俗性的生存选择, 也同样没有太多的理性追问, 没有尖锐的生存反思, 叙事话语仿佛从日常生活之中自然地流淌而出, 洋溢着浓郁的世俗情怀。我们所感受到的, 只是各种难以言说的人性与情感, 以及人物无法掌控的命运际遇。即使是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风中的院门》等散文集中, 我们也仍然看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足性。在这些作品中, 创作主体对人物生存及其命运的处理, 不再过度强调其中社会历史的意义建构, 而是采用平等的姿态, 更多地逼近琐碎的日常生活, 逼近庸常而又混沌的生存意绪, 呈现日益缭乱、无序同时也是丰富、蓬勃的生存景象, 展示尖锐、率性同时又是丰盈、鲜活的生命情状。日常生活诗学的内在基础是人本主义的思想, 它体现了个体生存的不可取代, 以及对个体尊严的自觉维护。
再次, 是自由而精细的文本形态。由于日常生活的琐碎、随意, 以及强烈的现场感, 在具体的审美表达中, 作家们普遍追求细节的微妙与灵动, 并不过度强调文本结构的完整性, 而是在自由随意的话语表达中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形态。像“民间写作”群体的许多诗歌, 都常常盘旋于各种琐碎而具体的细节中, 层层揭示日常生活的审美肌理。如于坚的《在牙科诊所》《那时我正骑车回家》《下午》《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等诗作, 都是从简单的日常场景或事件出发, 从各种细微的日常生活现场中发掘诗意, 并借助口语化的特殊语调和节奏, 呈现生活自身的内在意味。生活便是此在, 此在便是生命本身的意义之所在。杨克的诗歌也常常将触须探入现代生活的角角落落, 带着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 不断地想象并复原各种独特的生存感受。在那里, “汽车蝗虫般漫过大街/我的身体像只大跳蚤在城市的皮肤蹦达/‘忙’这条疯狗/一再追咬我的脚跟/这个年头/有谁不像一只野兔?” (《“缓缦的感觉”》) “在没有黑夜的南方/目睹金钱和不相识的女孩虚构爱情/他的内心有一半已经陈腐。” (《杨克的当下状态》) 欲望、梦想、冒险、惊奇……在奢侈淫糜的都市内部, 人们总是以感官享受为第一原则, 将消费时代的无深度生活打造得“万紫千红”。
小说更不例外。像潘向黎的《白水青菜》《永远的谢秋娘》, 都是利用情感的微妙冲突, 于不动声色的细节之中, 演绎了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处事智慧和达观的生存态度。林白的《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和《致一九七五》, 也一改作者以前对两性抗争的尖锐叙述, 而对日常生活进行直觉化、碎片化的细节呈现;即使是面对“上山下乡”这样的特殊历史, 作者都没有明确地给予批判或反讽, 而是洋溢着青春内在的热情。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灰鲸》、毕飞宇的《睡觉》《大雨如注》, 以及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火锅子》《春风夜》等短篇, 都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 在看似无冲突的情节演进中, 利用人物彼此之间的扯扯拽拽, 凸现当下现实中各色人等的内心际遇。类似的作品极多, 且作家们都是为了突出各种微妙的生命体验, 强调人物内心意绪的精妙拓展, 全力展示那些被庸常经验所遮蔽的、极为丰盈的生命情态, 减轻各种共识性的思想价值意义的追问。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wenxuelunwen/5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