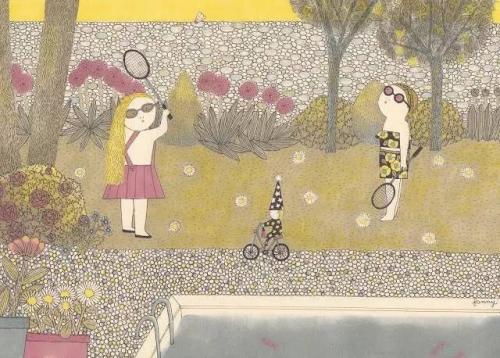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内容提要 保全其研究对象即审美生活的完整性,是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第一要务。不同于科学活动、宗教活动的无时间性、无空间性,审美生活作为兴发着的时间 视域只能奠基于特定作品的空间性构成,且以此愉悦的过程为目的,这就是审美生活 的 “时—空” 语法。文艺欣赏活动作为时间视域最为显著的特性是流畅性,在这一前提下才能陈述文艺作品空间构成的整体性,文艺作品的内容是时间化、空间化的。审 美与科学、宗教、道德之间的不同组合与历史发展,造成了文艺理论 “时—空” 语法的不同状态,可望形成新的文艺理论研究的富矿。
关键词 对象保全; 审美生活; “时—空” 语法; 时间视域; 流畅; 整体
确立研究对象并保全其完整性,是文艺理论 作为知识体系进行合乎逻辑的话语生产的唯一出 发点。就美学而言,其最高的、唯一的研究对象 是审美生活; 就文艺理论而言,其最高的、唯一的研究对象就是对文艺作品的欣赏活动。保持其 完整性就是保持其原发性的、原初的存在状态, 也就是处于反思之前的、理论化之前的原生状态。这一原生状态就是: 针对文艺作品的审美生活是一个前牵后挂的、兴发着的、涌现着的、愉悦的、域状的时间意识,且这一时间意识只能奠基于特 定的文艺作品之上,也就是只能奠基于构成这一 文艺作品诸因素之间的空间性位置关系之上。审 美生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 能、与其他生活领域的复杂关联等,这种种特性 都实现于其中并呈显其原初状态。文艺理论知识 体系的所有陈述都应在上述前提之下才有可能是 合理的,就此而言,便构成了保全文艺理论研究对象———文 艺欣赏活动之 “时间性—空间性”语法。
这里所说的 “语法”,不是狭义的语言学意义上的 “语法”,而是就文艺理论或世间一切知识必须经由语言陈述所必须遵循的本学科体系的规律、规则、规范来说的。本文拟就文艺审美生活构成方式的特殊性、时间意识与空间性构成的状态及关系、这一问题在中西方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中的复杂呈现进行阐述。
一
特定的审美对象产生特定的美感,且只有当审美主体把注意力始终指向并贯注于这一审美对象的时候才会产生美感。一旦人们把注意力从某一审美对象上移开,审美生活便戛然而止。 “意向性” 是审美生活最为根本的构成方式。这意味着在审美生活之中,绝对自足、自立的审美主体或审美客体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两者之间是一种须臾不可分离的始终指向关系。这是本文的基本前提。
迄今为止,人类创造了形形色色的意义或价值,究其主要形态,不外乎与审美、科学、宗教、道德这四大活动相对应的价值。上述基本前提还 无法把审美生活与科学活动、宗教活动、道德活 动有效区分,因为后三者作为主动性行为,其基 本构成方式同样是意向性的。因此,必须从人类 对意义或价值寻求的根本差异出发,才能解决审 美生活构成方式的特殊性问题。
具体来看,科学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 题 ( 人自身也是自然) ,探究的是客观的、一般性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 宗教解决的是人与神的关系问题,追求的是对主观的神的虔诚信仰; 道德活动解决的是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 问题,寻求的是善的行为; 而审美追寻的是自身感官所能得到的愉悦。当然,在不同的文化、地 域及历史发展状态上,以上四种价值有着不同的 分布与组合,而且这种分布与组合会造成人类文 化形态的差异。从与审美价值、审美生活相似度 高低、距离远近、区域重合的角度来看,审美与 道德价值、道德活动具有天然的相通、重合、切 近之处,因为善行也会给予人身心的愉悦。而审 美与科学活动、宗教活动有着根本差异。在科学 活动中,为保持知识的客观、中立,需要尽可能 排除感性因素诸如情感、梦想、欲望等对知识的 渗透。在宗教活动中,也要保持神的永恒不变, 不随信徒各种感性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源 出于纯粹客观或纯粹主观的科学或宗教与执着于 不同对象的审美与道德之间在构成方式上便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审美、科学、道德、宗教诸活动 在构成方式上的不同,与其在意义、价值上的差 异是紧密相关的。
具体来看,科学活动要始终保持知识的抽象、客观、普遍有效性,为此,科学家要始终保持科学 知识、科学规律的独立自足,科学家自身的心理活 动、身体感受虽处在持续变化的过程之中,但这种 属于主体的时间性因素不能渗入知识之中,可以说, 知识是无时间性的。我们无从述说 1 + 1 = 2 的结果即 “2” 自身是持续性的、变化着的、有始终的, 这种无时间性、非时间性、超时间性就是科学陈 述的广义语法或者科学哲学的广义语法。在不同 的科学论证中,起到唯一理性与秩序性作用的是 具有系统性、一般性、客观性的知识,尤其是寓居于论证中的 “规律” 与 “形式”,虽然在不同的事态中会有不同的符号、文字及其空间性构成参 与其中,但是这些科学规律、形式本身却是唯一 的、固定的、普遍有效的。这意味着科学陈述的 空间性也是不突出的。
宗教活动的核心是对超自然、超人间因而必定是超时间、超空间的彼岸的神的信仰及相应系统化的仪式活动。就超时间而言,各种主要宗教
都主张神的永恒性,神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 有永远的现在,由此,神才可能在 “世界” 之前存在并创造世界。就超空间而言,世界及其万物 是由神祇创造并赋形的,因此在基督教世界才会 存在反对 “偶像崇拜” 的思潮、运动及相应争议。即便是塑造神像,神像也不过是通达教义的手段 而已,绝不是目的。很多宗教所创造的艺术都只 不过是宣扬教义的权宜之计,若执着于此,就会 舍本逐末,让视听快感作为时间意识占据信徒的 心灵。因此,宗教往往与此岸的现世享乐为敌, 与感官及身体为敌。在各主要世界性宗教的经典 文献及其教义陈述文本里,既充满着消除欲望、消解身体、消除美感、禁绝可欲之物的思想,也 蔓延着抑制与消除欲望、身体、美感所呈显的原 初的时间性状态,以及直接取消欲望对象自身从 而消弭其空间性构成的陈述语法。
审美生活作为意向性活动的特殊之处则在于: 作为一个兴发着的、流畅的时间视域,审美生活只能由时机化的审美主体始终指向特定的审美对象所奠基。所谓兴发着的、流畅的时间视域,是指审美生活以愉悦的 “过程” 为己任,而且这一“过程” 只能由特定的审美对象所触发并持存。所谓时机化的审美主体,是指主体处在偶在化的、变动中的、在变动中提高的状态,审美能力、审 美需要绝不是像科学知识、宗教神祇一般的绝对 的、无时间性的静止存在,审美生活的兴发必定 是触机而兴发、当下即席地存在着的。与科学活 动相比,审美生活绝不提供无时间性的一般性真 理或知识,也不供给化约性的抽象空间与形式; 与宗教活动相比,审美生活寻求与流连的是当下、此岸的愉悦过程,而不是像宗教那样苦心孤诣地 拆解感官愉悦活动,在主体方面克制欲望,力图 不指向,在客体方面取消对象。审美生活的愉悦 就体现于注意力黏着在特定对象的时候,对象变 化,愉悦则变化。在审美生活中,文艺作品作为 审美对象的形式感最强,准确地说, “形式感” 正是构成文艺作品诸要素在 “位置” 之间的空间性构成。如果我们熟读王维的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当我们仅仅听到 “遥知兄弟登高处” 之时,“遍插茱萸少一人” 就会自发地、不可遏止地兴发出来,我们虽还是审美之 “主”,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俨然已为其控制,化身为 “奴” 了。
在以上对审美生活作为意向性活动之构成方 式所做的陈述中,尤其是与科学活动、宗教活动 及科学陈述、宗教陈述相比较时,一个美学的、文艺理论的 “时—空” 语法已顺其自然地生成, 那就是 “只有” 当审美主体始终指向特定的、具有固定的空间性构成的审美对象 “之时”,审美生活才会如其所是地存在,才会保持其原发性的本 貌。如此,文艺理论作为一种知识、话语体系才 有可能得到奠基。
二
构成审美生活的因素很多,对所有因素与部 分的陈述都必须在审美生活的疆域之内,或者说, 所有因素与部分一旦进入到陈述的视野,都必须在前面加上一个其所隶属的最高的主语———审美生活。
任何审美生活都是一个兴发着的、前牵后挂 的、视域性的、晕圈状的而不是点状的时间意识, 其完善的存在状态或者境界必定是流畅的,而这 一时间意识只能由特定的审美对象或构成审美对 象诸因素或质料之间独一无二的空间位置关系所 奠基,且文艺作品内容的存在状态必定是时间化 的。上述 “时—空” 语法又可具体化为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审美生活作为时间视域的流畅性。审美生活作为绵延的时间意识,其最显著的特性莫过于流畅。流畅意味着一个审美生活事件质量较高,完成的过程完美,更关键的是,流畅是审美生活在时间意识呈现上最为简捷的根本枢机。也就是说,对构成审美对象中各个不同质料的感知相状都是在一个行为级中实现的。使用域状的“时间意识” 或 “时间视域” 一词,可以较为完满地体现文艺审美生活的原初存在状态。一个心智 健全的人总会意识到自身行为、事件或心理活动 的触发、持存与终止,因此,在这里所存在的时 间就不是在计时器上独立存在的、作为衡量事物 空间运动标准的客观时间。人们总是希望得到流 畅、连贯且毫无迟滞、断裂、停顿的美感,比如 当我们正沉浸于听音乐、读小说、看电影的时候, 是不愿意被人打断的。
所有意向性都是视域性的。所有意向行为都是由 “原印象” 开始,而后 “原印象” 成为 “滞留” 且向前 “前摄”,这就是 “域状” 的 “时间意识”。 “时间意识” 并不是意识到一个孤立、自足存在的时间客体,而是意向性行为自身的开始、绵延、终止这一原发性的呈显状态。特别需要注 意的是,“滞留” 不是 “原印象” 的过去,更不是回忆; 而 “前摄” 也不是 “原印象” 的将来,而是一个有宽度的时间意识之 “域”。比如 “春花秋月何时了” 这句诗共 7 个字, “春” 这个字是整首诗的开始,在时间意识之中是一个触发点即原印 象,尔后的 “花秋月何时了” 继之而起。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先是 “春”,尔后 “春” 在时间上就成为过去,然后又分别读到了 “花” “秋” “月”“何” “时” “了”。事实上,当我们读到“月”,“春花秋” 并没有消失,只是在这个时候, “月” 在视域中显得最亮,“春花秋” 可能稍逊,甚至是同样明亮的,在 “滞留” 里得以保存,并且,从“月” 向着 “何时了” 存在着 “前摄”,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时间意识。
其二,在流畅的时间视域内陈述文艺作品空间性整体构成。当我们为李煜的 《虞美人》所叹服的时候,一定是我们正在阅读它的时候,且这 个时候一定是从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被攫取开 始,而后这种美感便持续无间地、流畅地占据我 们的身心。在此审美生活中,欣赏者始终在欣赏 诗作,且诗作中的任何组成部分、任何个别性的 属性因素都在空间里分处在如其所是的那种特定 的位置之上,每一个部分、因素都是特定的、固 定的、独一无二的,都分布、安居于特定的、固 定的、独一无二的位置之上。正是由于这一坚定 的、顽强的空间与审美主体一起,才造就了那特 定的、独一无二的、涌现着的愉悦的时间意识, 即对 《虞美人》的欣赏生活本身。从审美生活作为一种时间意识的构成来说,此空间之内任何因 素、部分所处的固定位置也就是时间意识或者时 间视域中的特定 “相位”。这一 “相位” 绝不是作为艺术作品中孤立存在的质料或者物因素,所有 这些质料或物因素形成一种亲密的、杂而不越的 整体性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审美主体把这 些质料或说物因素带入一个视域性的审美生活。而这一审美生活所具有的时间视域绝不是构成审 美对象所有要素的相加之和,因而也就不可能把审美生活还原为审美对象诸因素的相加之和。如 果构成这一空间的任何部分、因素有任何变动, 都会导致审美生活作为时间意识过程的退化、变质。
如果审美主体正在进行着或已经获得了时间 视域极为流畅的审美生活,那么,这同时就意味 着构成艺术作品的诸因素、诸质料都处在其特定 的空间位置之上,任何一个因素、质料都各得其 所,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血肉相依的整体性关系。审美生活的流畅性是根本,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 有可能对艺术作品的构成或者构成艺术作品诸因 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行陈述。在语言表达上,当 我们说一个作品在构成上无比完美时,其实就是 在说,我们从这个作品身上得到了流畅的审美感 受。反过来,当我们说我们从某一作品获得了流 畅的审美感受时,也就意味着这个作品的空间构 成是固定的、完整的。在汉语中我们往往以 “整体” “统一” “有机体” “有机整体” “有机统一”
“有机统一体” “杂而不越” 等术语来表达。
其三,在 “时—空” 语法阈限之内陈述文艺作品内容的呈显状态。对文艺作品的欣赏活动而 言,艺术作品的内容或者意蕴,应隶属于一个有 意义、有价值的审美生活或者审美行为,否则, 艺术作品的内容就会成为一种自立、自足、自为 的绝对存在,脱离审美生活这一整体而成为唯一 目的或者意义。比如对李煜的 《虞美人》,通常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往往只满足于述说李煜此 作中的 “愁” 这一意蕴,而忘记了 “愁” 隶属于、寓居于对这一作品原发性的欣赏活动。
文艺作品的 “内容” 必定是 “时间视域化” 的,且必然经由审美主体贯注于文艺作品的 “形式”,即诸物聚集的 “空间性”,才能如其所是地显现,并隶属于审美生活。缺乏 “时—空” 语法的 “内容—形式” 构成论在大多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中分属于 “作品论” 或 “作品构成论”。尤其是在科学主义文艺理论中,这种作品论往往上承或者决定于 “本质论”,其实就是纯然的认识论或者科学哲学在文艺理论中的强行运用,其惯用的语法或陈述方式是 “通过……真实地反映……”,只求反映的结果真实、客观,完全无视描述审美生活的 “时—空” 语法。因此,这种构成论与其之后的 “接受论” 完全无法贯通与沟通。“内容—形式” 之说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无法让 “形式” 在“内容” 里找到其栖居的 “位置”,更把 “内容”当作可以摆脱审美生活的抽离之物,或者把 “内容” 当作比审美生活更高、有待于从审美生活中升华出来且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一定有一个有“价值” 的 “行为” 发生在 “前” ———比如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才有可能陈述文学作品的 “内容”,而且是在对这 “一个” “行为” “中” 的“对象” ( 文学作品) 的 “内容” 作陈述。这意味着两分法绝不是自足、自持的,离开这个有价值 的行为就无从呈现。两分法往往意味着 “内容” 是第一位的,是作品或者阅读行为的目的,这会 导致对 “形式” 的忽视,且 “形式” 可以被替换而 “内容” 不变,并使用更加 “化约式” 的语言对文艺作品的 “内容” 进行总结式的替代。
三
审美、科学、宗教、道德之价值在不同文化形态中的不同分布及其所造成的独特的文化价值生态,既决定了审美文化、美学、文艺理论主要形态的差异,也决定并直接呈显为 “时—空” 语法的不同状态、内涵与演变路径。
西方传统文化在客观 ( 科学文化) 与主观( 宗教文化) 这两端都极为发达,且一直在此两端之间剧烈摇摆,却拙于对主客不分离区域的持守与阐发。在科学与宗教之间虽有强烈对立,但在无时间性上确是一脉相通的———神祇之永恒与知识之不变。他们力图消除的就是欲望呈现的时间性状态与具体事物变化、变异的属性。17 世纪末18 世纪初,西方宗教文化面临世俗化的剧烈挑战, 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感官审美文化日益 勃兴,尤其是到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作为对科学主义及心理主义的回应,现 象学哲学应运而生。
总体来说,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主要有神学美学、科学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这四大脉络。神学美学高扬的是禁欲主义旗帜,所孜孜以求的是对永恒的神的信仰,力图消除的是来自感官的愉悦,它用力最深的,一是针对审美主体,最大限度地减弱作为肉身的欲望,尤其是彻底消除来自触觉、味觉、嗅觉、动觉的愉悦,仅仅保留来自视觉、听觉的愉悦。即 便是对来自视觉、听觉的快感,也要加以严厉限 制。二是针对审美对象,力图在数量上最大限度 地减少它们的存在,仅仅保留宣扬宗教教义的宗 教艺术。科学主义美学也有两条路径: 其一是针对文艺作品的内容进行化约性的语言转述,仅仅 以结果正确与否衡量作品; 其二是专注于形式主义研究,排斥作者、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 采用描述法,分析作品的先在结构和语义关系, 追求客观化、中立化的研究立场。以上两端都会 导致将整体性的空间构成化约、转渡为抽象的、无时间性的所谓规律、结构、方法、手法、句法、模型、语法,等等,这就完全改变了作品的空间 性构成,也就同时把奠基于这一空间构成之上的 文学阅读活动的时间视域彻底改换。现象学哲学 为美学贡献了意向性理论、本质直观学说、内时 间意识现象学与审美时间哲学。就对时间哲学的 创设而言,胡塞尔长于对静态的内时间意识进行 诸如原印象、滞留、前摄、后坠、时间透视等时 间视域构成的精微分析,其缺陷在于过于冷静, 没有将赋予时间视域何以兴发的意义作为动力, 也没有把内时间意识与社会时间进行沟通。海德 格尔长于从意义作为时间绽出之动力,并从非现 成性识度及艺术作品空间性构成的整体性对文艺 作品内容的存在状态进行深思,其缺陷却恰恰在 于缺乏时间意识构成的域状识度,导致其对艺术 作品空间性构成的陈述语言过于比喻化、神秘化, 也更体现于仅仅对意义作中性的抽象研究,而不 是对意义与价值进行直接判断。
中华传统文化则在客观之科学与主观之宗教 这两端都极不发达,其执着与流连的是愉悦感觉 自身的兴发与绵延。这种感觉的主要来源有二: 其一是道德领域之中以亲子之爱即 “慈孝” 为核心的家庭温情,尤其是 “慈” 堪称人间冲动最强、持续最久、最无私、最自然的道德感,同时也是 纯然的美感。儒家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即仁, 仁的核心即亲子之爱,而仁的外在显现则是礼。其二是毫无偏见地公平对待来自艺术作品、日常 用品、空间环境、人际交往、饮食等各种审美对 象的愉悦感。尤其是当礼与乐、诗、舞、文等空 间构成性极强的艺术完全融合为礼乐制度之后,
其形式感被强化,其兴发与持存的时机愈发敏捷。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wenxuelunwen/6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