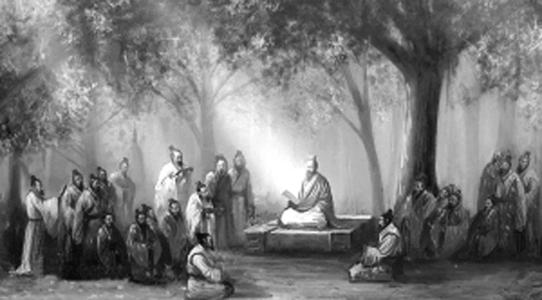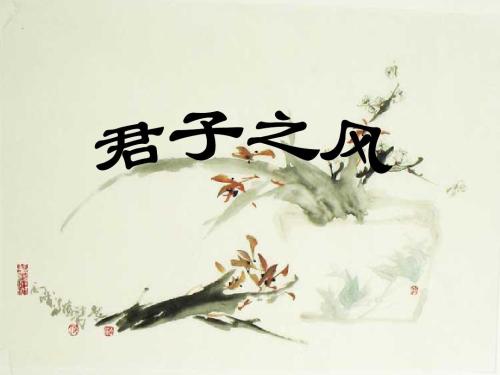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君子是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语词。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君子文学, 君子的人格追求也是中国文学的理论追求。君子一词经历了从阶级向道德意义的转化, 中国文学的主题也经历了从英雄表现向君子叙事的转变, 君子与小人的冲突, 成为中国文学基本的人格对立与矛盾叙事。新君子群体凭借道德和知识的优势, 建构了一套从哲学到文学的完整思想话语, 中国文学的人格、思想、艺术、审美等原则本质上也是一种深刻的“君子曰”。
关键词:
君子; 新君子人格; 驱逐小人; 君子曰话语;
Gentleman Personalit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on “Gentleman Saying”
Fu Daobin
引言
“人之所以道也, 君子之所道也。” (1) 君子是中国文化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心语词, 与宗教背景下按照“神的样子”的宗教人格塑造不同, 中国人的道德升华是在世俗世界里实现的, 这种世俗性成就了君子作为中国人普遍的人格追求。
中国古典人格可分为圣人—君子—小人三重境界, 君子人格不及圣人境界, 却与小人形象截然对立。圣人超迈群伦, 《中庸》谓“大哉, 圣人之道, 洋洋乎, 发育万物, 峻极于天, 优优大哉” (2) , 孔子尝感叹“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 得见君子者, 斯可矣。” (3) 对于世俗世界的普通人而言, 只能“得见君子”, 选择在世俗世界里成就具体的道德化的理想君子人格。君子是中国文化最广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精神符号, 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君子文学, 君子形象是文学世界里的典型形象。
一君子从阶级称谓到人格术语的转变
生存意义上的人, 只是人的“半成品”。人之所以为人, 必须完成思想的、道德的、智慧的、审美的等精神层面的升华与完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 (Toynbee) 将这一过程形象地概括为把“半人变成人”。他说“这个变化是比在文明社会的环境里所发生的任何一次变化都是更深刻的一次变化, 是一次更大的生长。” (4)
“君子”一词最早是阶级的, 是居住于城邑中心的宗族统治阶层, 而小人则是处于乡野的被统治者, “君子劳心, 小人劳力, 先王之制也” (5) 是上古时代普遍接受的观念。《周易·剥卦》上九爻辞谓:“硕果不食。君子得舆, 小人剥庐” (6) , “君子”与“小人”对举, 面对累累“硕果”的物质利益, 君子得舆, 收获丰厚, 小人剥庐, 惨遭掠夺, 两相比照, 境遇悬殊。《尚书·无逸》谓:“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 乃逸, 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 厥父母勤劳稼穑, 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 (7) 贵族君子, 居于城邦, 无忧无虑, 逍遥飘逸, 而乡野小人则躬耕田垄, 困苦艰难。居住于城邦的君子“锦衣狐裘” (8) “夏屋渠渠” (9) “每食击钟” (10) , 而居住于乡野的小人则过着“无衣无褐, 何以卒岁” (11)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 塞向墐户。嗟我妇子, 曰为改岁, 入此室处” (12) 的贫寒生活。
“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 (13) “无君子莫治野人, 无野人莫养君子” (14) , 巨大的阶级差别造成了君子与小人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距离。处于社会底层的所谓小人, 被剥夺的不仅是物质, 更是文化、精神与道德提升的可能性。而统治阶级则乐于用文化与道德武装自己, 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体系的建立, 本质上是政治秩序化和君子人格道德化的过程, 其结果是, 君子集团不仅站在政治的制高点, 也站在了道德与文化的制高点上。
礼乐文化一方面通过一系列仪式规定, 保持政治生活稳定有序的运行, 另一方面通过仪容、言行、道德、知识、修养的陶冶浸染, 塑造出一个支撑起整个社会骨架的君子集团。“君子”一词在《礼记》中出现329次, 其中的《曲礼》《学记》《乐记》《中庸》《表记》《儒行》《大学》等篇章,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内容各有侧重的“君子论”。这些文献从外在气度、内在修养、知识构成、艺术风范等多方面为君子画像, 为整个士大夫建立精神原型, 从而为古代士人的人格成长提供一种思想指引和人格方向。
1. 君子之容
周代礼乐文化十分注重在世俗生活中完成君子形象塑造, 在动静举止中呈现君子谦敬温雅从容祥和的外在风范。
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15)
(君子) 毋侧听, 毋噭应……寝毋伏。敛发毋髢, 冠毋免。劳毋袒, 暑毋褰裳。 (16)
君子之容舒迟, 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立容德, 色容庄。 (17)
礼乐文化对君子形象的刻画描述, 是工笔的写实的, 手足口目, 行立静卧, 声色言语, 动作的每个细节、衣着的每个佩饰、语言的每个用语都有详尽的规定和仔细的描摹, 如此则君子形象便有了优雅舒缓、从容适度的艺术属性。
2. 君子之德
周人尚德, 春秋时强调士大夫传之久远的“三不朽”, 而“三不朽”中最高的原则是“太上立德”, 道德完善中实现精神不朽成为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同时, 《礼记》从来不把道德推向玄远, 而是立足于现实, 从修身开始推及天命, 从修身开始延展至家国天下, 所谓: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 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 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 (18)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无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19)
道德虽然广泛却总从个人开始, 家国虽然广大却立足于个体生命, 从而形成了从个人品格到家庭教养到国家治理再到天下普及的逻辑线索, 道德是整个人伦社会的基本元素。
3. 君子之学
周代礼乐文化特别重视知识在君子人格成长中的作用, “学”不仅是《论语》开篇的第一个语词, “学”也是儒家最为重视的人格条件。《礼记·学记》谓:
就贤体远, 足以动众, 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乎。 (20)
不学操缦, 不能安弦……故君子之于学也,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21)
儒家强调的“学”, 是一种全面的过程, 包含思想、艺术和礼乐, 这一切又体现在实践和运用的细节中。“君子之于学也”, 就是藏身于此、修身于此、滋养于此、游憩于此, 自里自外自始至终都沐浴在知识光芒的朗照里。
4. 君子之趣
君子不仅是承担政治责任与道德使命的, 也是富有诗书教养和艺术情趣的。在儒家教育中, 诗是君子教育的重要内容, “不学诗, 无以言”是礼乐文化的根本信念。因此周代贵族君子在大型的礼乐与政治、外交、乡俗活动中, 赋诗言志, 唇齿留香, 显示出良好的诗书教养。音乐是君子区别于普通人的根本标志, 《礼记·乐记》谓:
知声而不知音者, 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 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22)
周代文化中“知乐”是君子的根本标志, 是最基础的精神修养和艺术趣味。按照《礼记·玉藻》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 (23) , 而这种佩饰不仅仅是审美装饰, 也有道德趣味, 所谓“君子于玉比德焉”, 玉佩一方面体现装饰之美, 也具有道德的象征意味。君子的行走也有艺术的旋律, 即“趋以《采齐》, 行以《肆夏》” (24) , 无论行走, 还是快步小跑, 都契合音乐的节奏, 有审美的艺术的自信和愉悦。
在礼乐文化的知识、修养、情趣、道德、容仪的塑造与规范中, 君子渐渐摆脱了阶级意义中的居高临下的傲慢粗野, 开始强调人格、道德、文化的力量, 这种变化的意义是革命式的,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清代学者崔述说:“君子云者, 本皆有位者之称, 而后世以称有德者。” (25) 从西周到春秋, 在轴心时代的文化环境里君子完成了从阶级意义向文化和道德意义的转变。《诗经》中的《雅》《颂》诗篇里, “君子”一词往往充满了贵族的身份感、优越感, “驾彼四牡, 四牡骙骙。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 (26) 、“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视” (27) , 君子乘坐战车, 威风凛凛, 而士兵们只能徒步奔走;君子气宇轩昂地走在宽敞的大路上, 而普通民众只能远远地侧视。至春秋时期, 君子的意义越来越超出身份阶级的一般意义, 而被赋予了更多道德和文化的意义, 《诗经·卫风·淇奥》中被屡屡称颂、久久难忘的“有斐君子”形象, 呈现出来的“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 (28) “如金如锡, 如圭如壁” (29) 风采, 已经不是自命不凡的政治上血缘上高贵的君子, 而是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的君子人格精神了。
《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晋景公视察军府, 看到了“南冠而絷者”的钟仪, 而钟仪与晋景公的一段楚国家乡南音演奏的对话, 征服了晋国君臣, 范文子情不自禁地称赞这位身陷囹圄的“楚囚”为君子:
文子曰:“楚囚, 君子也。……不背本, 仁也;不忘旧, 信也;无私, 忠也;尊君, 敏也。仁以接事, 信以守之, 忠以成之, 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 使合晋楚之成。” (30)
应该注意到, 这是《左传》第一次完整地系统地提出了“仁、信、忠、敏”的君子人格标准, 标志着春秋时代君子人格的成熟, 君子完成了阶级称谓到人格术语的转变。后来思想家对君子人格的阐释不断丰富, 但大体没有走出这一范围。
二《左传》与春秋时期新君子人格的形象
春秋时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意义非凡, 君子从宗法阶级的意义转向道德文化的意义, 新的君子群体开始出现。新君子人格的成熟是春秋新人文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标志性事件。
首先, 新君子群体在政治上咬断了与旧贵族联系的脐带, 实现了阶级解放。西周衰亡, 各诸侯城邦自立, 摆脱了西周政治束缚的城邦君子, 不同于旧贵族的慵懒舒缓和骄矜自持, 这一群体开始以一种新的目光审视世界, 逐渐成为摆脱西周政治束缚的新兴政治力量。其次, 新君子群体在思想上割断了与“半神半人”的宗周旧思想的关联, 完成了“哲学的突破”。面对灭亡的西周政权, 春秋时人心震荡, 对天命的怀疑和莫大的心理忧伤笼罩在新君子群体的心头。随着对天命的神圣意志的否定, 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哲学精神成长起来了。以史官为主体的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提出了“夫民, 神之主也” (31)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32) 等富有启蒙意味的哲学命题。再者, 新君子群体在文化上构建了一个新的经典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整理并诠释了传统文献, 《诗》《书》《易》《春秋》及礼乐文献得到进一步推广。时人对《周易》等哲学经典进行了新的解释, 借以传播新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仁爱精神, 新君子集团由此得到了滋养与武装。
《诗经》篇章中多见以抒情笔调歌颂君子形象者, 如《卫风·淇奥》中所载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 (33) 。《诗经》中君子的描写, 多为写意的宏观的, 而《左传》的出现则大大深化具化了君子形象, 把思想家们对君子人格抽象的理论概括, 以艺术的手法生动地呈现在文学世界里。
1. 以仁爱忠信为核心的道德追求
“德”是君子人生的最高追求。《周礼》中《大司乐》《大司徒》两次谈到所谓“六德”, 或谓“中、和、祗、庸、孝、友”, 或谓“知、仁、圣、义、忠、和”, 两者略有不同, 但都是以“仁”为核心的人格境界。正因为“德”是最高的人格精神, 因此春秋君子不惜以生命去追求道德的完满。为国家的利益, 石碏杀死弑君逆子石厚, “君子曰”称其为“大义灭亲” (34) , 这个“义”, 就是道德, 就是社会伦理和社会正义。存在于君臣家国社稷之间集体的族群的“大义”, 是高于血缘和私情的。
晋国郤缺以罪人之子而躬耕冀野, 不得为仕, 而他从容冷静, 处变不惊, 与妻子耕耘田野, 不嗟不叹, 相待如宾。奉命出使经过冀野的胥臣见此, 深受感动, 将郤缺举荐给晋文公。文公以其是罪人之子而犹豫不决, 胥臣谓:
敬, 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 承事如祭, 仁之则也。 (35)
春秋君子以实现道德的完美为第一要义, 《左传》塑造了许多以生命成就君子人格的贵族形象, 他们为实现仁爱忠孝等人格而不惜舍生。《左传》有三则故事颇有典型意义:一是桓公十六年卫国太子伋与公子朔争相赴死;一则是晋国的太子申生隐忍自缢;一则是楚国太子太傅伍奢之子伍尚归国赴死。
2. 以谦敬辞让为规范的礼仪风度
周礼的内容包括社会制度与个人修养两个部分, 礼的僭越与破坏多体现于社会的政治的制度层面, 而个人的修养的人格则是春秋贵族的自觉追求。《左传》将思想的意义付诸艺术的描写, 出现了一大批谦敬祥和、富有风雅精神的君子形象。
陈公子完 (敬仲) 因动乱而逃亡齐国, 齐桓公欲使“敬仲为卿”, 公子完以“羁旅之臣”而真诚推辞。齐桓公招其宴饮, 兴之所至, 准备举火夜饮, 欢饮达旦, 公子完则以“未卜其夜”而婉言谢绝。从而赢得了《左传》“君子曰”“以君成礼, 弗纳于淫” (36) 的称赞, 为后来陈氏代齐做了以礼乐文化为背景的历史铺垫。
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访问卫国, 有“卫多君子”的感慨。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都是季札内心喜悦的君子。《左传》中这些被称颂的卫国君子, 无不表现出正直高尚的人格精神与谦雅祥和的文明修养。
春秋君子不仅体现为礼敬辞让的风雅精神, 也体现为举手投足间优雅从容的外在气度。礼化的过程, 既是雅化的过程, 也是不断人化的过程。君子居必佩玉、行必佩剑、必配琴瑟, 剑气箫心, 气象非凡, 《诗经》所谓:“威仪抑抑, 德音秩秩。” (37) 可见春秋君子十分重视衣冠容止, 外貌气度。《左传·昭公十一年》记:
单子会韩宣子于戚, 视下言徐。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朝有着定, 会有表;衣有襘, 带有结。……不道不共, 不昭不从。无守气矣。” (38)
容貌不仅是一种装饰, 更是一种精神。一个眼光, 一句言语, 一件佩饰, 都流露出内在气质和精神修养。
3. 以诗书经典为基础的知识修养
君子是城市革命中阶级分化的产物, 是在城市革命的带动下形成的一个特有的知识阶层。周代统治阶层每每有重大选择或者政治决策时, 总是问计于知识阶层, 因此知识与学问成为周代贵族的一种追求。君子保持了对知识的浓厚兴趣, “学”成为春秋君子的基本人格。《论语》开篇就提出“学而时习之”, 学与不学是风雅和粗野、高贵和卑琐、智慧和愚陋的分域线, “学”更是儒家对贵族子弟的根本要求。《论语·阳货》孔子谓:
好仁不好学, 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刚不好学, 其蔽也狂。 (39)
人类的一切品行道德都需要学习来补充修正, 正因为如此, 周代建立了严格的子弟教育体系。
经典是春秋贵族的主要知识构成, 是士大夫必备的精神修养, 引证经典成为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潮。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认为, 知识不同于科学, “有一些知识 (这些知识既不是科学的历史雏形, 也不是它经历过的部分) 是独立于科学的” (40) , 与科学的冷静与客观不同, 在知识的空间里有主体意识的一席之地, “知识, 还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 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 (41) 。经典对于周人来说, 是知识的, 也是科学的信仰的。在经典的反复被引用中, 知识转变成科学, 转变成信仰, 确立了经典的至高无尚的权威地位。在六经中《诗》三百是被征引最多的礼乐经典, 这里的诗是知识的, 所以春秋时代常常通过赋诗言志表现礼乐文化熏陶下的贵族君子的风雅教养, 衬托着君子交往间的和乐温馨与审美愉悦, 因此《诗》三百成为春秋时代的礼乐蓝本与教育经典, 孔子特别强调“不学《诗》, 无以言”的意义。
4. 以勇武敏行为追求的英雄气度
顾颉刚说:“吾国古代之士, 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 居于国中 (即都城中) , 有统驭平民之权利, 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 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 (42) 春秋士人脱胎于武士集团, 因此这一时期的贵族君子保留了早期武士的尚武精神。依照顾颉刚的解释, 周代贵族教育有习武传统。古代学校被称为庠、序、学、校。序者, 射也。校, 即校武之地, 今天仍然有“校武”之义。贵族教育中的, 除了射、御具有习武意义之外, 六艺中大都有习武内容。
《诗经》中描写的君子形象许多是武士形象, 他们或勇武有力, 技艺超群, “有力如虎, 执轡如组” (43) ;或者俊逸潇洒、神采飞扬:“美目扬兮” (44) “射则臧兮” (45) ;或者在田猎中:“彼茁者葭, 一发五豝” (46) “彼茁者蓬, 一发五豵” (47) ;或者于战场上“江汉汤汤, 武夫洸洸。经营四方, 告成于王” (48) 。周代士人不仅仅具有儒雅温和长于辞令的风采, 更具有叱诧风云威武雄壮的气度。
比起《诗经》对周代贵族尚武精神的深情礼赞, 《左传》更倾向于对春秋君子英雄气度的具体描写, 更真实细微地揭示了其精神世界与心理活动。《左传》文公二年讲狼曋在战场上冲锋在前, 义无反顾, 而当其遭受不公平待遇时, 又不凭一己之勇来泄私愤, 而是更加冒死奋战, 最终以身殉国。“君子曰”充满敬仰地称赞狼瞫“怒不作乱, 而以从师, 可谓君子矣” (49) 。
《左传》刻画的一大批君子形象, 将春秋时期的君子人格从理性的思想追求带入文学的形象呈现, 这些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不仅为古代士人立范, 在礼赞追求的同时, 融入人们的思想价值体系中。
三驱逐小人:君子人格构成的正题和反题
在完成君子人格塑造的同时, 儒家也塑造了与君子人格相对的另一种人格———小人。与君子的渐渐脱离阶级的含义一样, 小人也渐渐摆脱了早期在田野劳作者形象。与君子人格的高尚、善良、正直、谦敬、英勇相比, 小人人格则是卑琐、邪恶、曲折、张狂、凶悍的, 儒家将君子与小人人格做了系统的完整的理论总结与说明。在《易传》《论语》《礼记》等经典文献中, 君子与小人的人格对立是很明显的。
1. 义利取舍
弘道是君子的最高精神追求和历史责任, 孔子特别强调君子道的责任, 谓“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50) , 若能明道, 则“朝闻道, 夕死可也”。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正在于此,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51) , 与君子对道与义的追求相比, 小人更注重世俗世界的物质利益。小人人格陷于利益与欲望的陷阱不能自拔, 《乐记》谓“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 以道制欲, 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 则惑而不乐” (52) , 道的神圣意义在于对人类欲望的控制, 而不是相反, 君子的意义在于能以正义的理性的力量驾驭非理性的欲望, “以道制欲”与“以欲忘道”成为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区别。
2. 和同之辨
“和”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 “和”是将有差别的事物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系。《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与史伯对话中提出了“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的哲学命题, 史伯谓:“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 尽乃弃矣。” (53) 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认识, 孔子提出了人际关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54) 人际关系上, 孔子主张调和, 但这种调和, 不是无原则的认同, 而是有差别的包容。小人之“同”, 是党人之“同”。“人之过也, 各于其党。观过, 斯知仁矣” (55) , 在孔子看来, 人们往往会陷于局部的狭隘的党争之中, 只有超越一己私利, 才能实现相互友善、相互融合的仁爱境界。
3. 诚伪之別
“修身之道, 乃诚之道。”“诚”是儒家遵循的基本伦理概念, 诚便是真, 是生命的真、思想的真, 也是情感的真。《中庸》谓“诚者, 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 (56) , 诚者是自然的本真的, 而诚之者则是人为的派生的, 也就是说自然世界的本真状态就是真诚的, 而人类世界则是后天的, 是对自然本真的模仿与追求。人性之诚是对天性之诚的模仿, 《中庸》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57)
天性是真诚的, 人性是真诚的, 天地之间生命的运转无不是真诚精神的表露, 一切脱离真诚的行为都是对自然天命与生命本真的扭曲和背叛。“忠信, 礼之本也” (58) , 忠信是诚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59) , 孔子教人总是将诚信作为人伦的总体法则。在诚的总体原则下, 儒家强调对国家的忠、对父母的孝、对朋友的信。“忠臣以事其君, 孝子以事其亲” (60) , 忠孝都属于诚信为本的君子人格的组成部分。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 礼以行之, 孙以出之, 信以成之, 君子哉” (61) , 实现君子要仁义为本, 要行为符合礼义规范, 要有谦逊的风格, 而最终成就君子人格的还是诚信的人格精神, 是自然的, 也是人伦的, 是一种总体人伦法则。
君子人格特别强调言行的一致性, 这是最根本的诚。孔子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已” (62) , 这里在名—言—行之间建立了相互印证相互联系的逻辑关系, 主张修辞立诚, 反对语言与行为的背离:“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63)
孔子对小人式的“巧言”表现出特别的反感, 主要是认为言语过于机巧, 便失去了天真, 失去了真诚, 导致言行不一行为的发生。孔子云:“巧言令色, 鲜矣仁” (64) , “巧言乱德” (65) , 动听的言词、丰富的表情往往是伪诈的表现, 是有悖于仁德的品质的。
4. 中庸正反
君子人格是平和的不对抗的, 这种人格即是中庸。中国古典哲学总是从两种对立的情绪中寻找到一种平衡, 如“直而温, 宽而栗,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 (66) “宽而栗, 柔而立, 愿而恭, 乱而敬, 扰而毅, 直而温, 简而廉, 刚而塞, 强而义” (67)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68) , 这种“A而B”或者“A而不B”正是在两种对立的情感和性格中寻找和谐, 以化解对立达到平衡、达到完美, 这就是中庸哲学的基础。中庸发现了对立, 却不激化对立, 而是调解对立, 将对立的两方融合一体, 不是彼此水火, 消灭一方, 而是兼容调解, 各有所取, 不及不过, 不偏不倚, 不卑不亢, 不疾不徐, 融为一体, 这便是中庸。“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69) 在君子道德中, 孔子将中庸推到极致, 认为是君子人格的最高准则, 《中庸》说:
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而无忌惮也。 (70)
中庸与否成了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中庸一是守中, 君子知道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 不激烈对抗, 不固持己见, 不自以为是, 在多样性的价值判断中有所取舍, 而又有所包容, 有所理解;二是居常, 庸即常, 即立足于庸常的现实生活, 君子的人格不仅见于生死之际、存亡之秋, 而更贯穿于世俗生活的动静坐卧、言谈举止寻常之中, 是朴素的、平常的、持久的, 所以孔子说中庸“民鲜久矣”;三是顺时, “君子而时中”, 所谓时中, 便是依时而动, 顺时而变, 与时偕行, 时时观察, 有所顾及。孔子嘱咐弟子“女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 (71) , 小人儒就是偏颇, 就是党见, 小人儒可以有一时之主张, 却不能长久, 这就决定了小人的无所顾忌:“小人而无忌惮。”正因为无忌惮, 无操守, 小人人格便是随波逐流, 无所依归, 便是为着一己私利无所不为了。孔子等思想家在为君子画像的同时, 也常常描绘小人的面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72)
子曰:“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戚戚。” (73)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74)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 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75)
君子居易以俟命, 小人行险以徼幸。 (76)
君子之接如水, 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 小人甘以坏。 (77)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站在君子的角度, 在《周易》《左传》《礼记》等经典著作中宣布了“驱逐小人”。《周易》中《泰》《否》两卦, 泰代表天地沟通、平安吉顺, 否代表天地不交、偃蹇不利, 在《易传》作者看来, 《泰》卦之所以是平顺的, 其卦象意味着“内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长, 小人道消也” (78) ;而《否》卦之所以是不利的, 是因为其卦象是“内小人而外君子, 小人道长, 君子道消也” (79) 。孔子谓:“放郑声, 远佞人。郑声淫, 佞人殆” (80) , 佞人是奸佞小人的另一种叫法, 在孔子的理想国里公开宣布远离奸佞、驱逐小人。如何治国安邦,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里意见纷纭,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 即驱逐小人。
君子与小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当我们称美君子时其实已经否定了小人。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事物存在着肯定—否定—综合三个范畴。黑格尔说:“康德哲学到处都展示为正题、反题和综合的图式” (81) , 在黑格尔的表述里综合图式也概括为合题, 正题是肯定的, 反题是否定的, 而合题是综合的。君子人格是正题, 小人人格是反题, 而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则是合题, 君子人格在与小人人格矛盾冲突中有了新的提升。
屈原的《离骚》等伟大作品将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的人格对立从思想领域带入文学领域。以《离骚》为例, 其矛盾主线是“我”与“党人”的政治冲突, 这种冲突在理想世界、现实世界和象征世界全面展开。作者的理想世界是君子式的:肩负道的使命, 充满美政理想。他是以一个“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82) 的君子形象出场的, 他肩负道义, 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有“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道夫先路” (83) 的政治理想, 正是周代典型的君子形象的呈现。而在现实世界里, 他却遭遇了党人的小人集团排挤打击, 造成了他缱绻不展的巨大心灵苦痛。他面对的是“党人之偷乐”“灵修之数化”的现实世界, 奸佞之徒, 竞进贪婪, 兴心嫉妒, 而自己的一片忠诚不被认同:“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谄而齌怒” (84) , 他切实感受到了“路幽昧以险隘”的绝望, 他理想的花园也众芳芜秽, 荃蕙为茅。理想在现实世界中遭受挫折之际, 他开始了象征世界的追寻。《离骚》的象征世界是历史的, 因此他向重华陈辞, 表白心曲;《离骚》的象征是神话的, 因此他凤凰飞腾, 扣问帝阍;《离骚》的象征世界是自然的, 王逸《离骚序》所谓“善鸟香草, 以配忠贞;……虬龙鸾凤, 以托君子;飘风云霓, 以为小人” (85) , 自然的芳草嘉树, 飘风云霓, 具有了人格与精神的象征意蕴, 被赋予了君子与小人的精神意义。
中国抒情文学中的自我形象是以君子为基本模型的, “我”与世界的对立往往体现为君子与小人的对立, 而叙事文学中的矛盾冲突集中于君子与小人的冲突上, 正义的一方是君子的, 而邪恶的一方则是小人的。中国叙事文学的大团圆结局, 也可以概括为君子的胜利。孔子式的君子思想理论, 屈原式的君子艺术形象, 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为中国的人格走向规定了道路。
四“君子曰”与新君子群体的思想话语
“君子曰”的出现意味着君子话语体系的建立。《左传》《礼记》《国语》《论语》等经典著作都有“君子曰”的记载, “君子曰”中的君子是谁, 是孔子, 还是左丘明?是具体的某位确切人物, 还是某种思想的寄托?尽管歧说纷纭,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一种思想、一种价值、一种评判、一种礼赞、一种指责, 只要有了君子的身份, 就有了话语的权威, 有了理论的自信, 这恰恰反映了君子的话语优势。
“君子曰”也写作“君子谓”“君子以”“君子以为”等形式, 而以“君子曰”数量最多, 最为经典。在《左传》《国语》《礼记》中, “君子曰”“君子谓”“君子以”“君子以为”频繁出现, 四者相加, 《左传》出现80处, 《国语》11处, 《礼记》20处, 这些话语有开篇即以“君子曰”的形式出现, 也有出现在文中, 而更多的则是出现在篇尾, 显示了君子总结式概括性的话语权威的特点。而与“君子曰”相类似的一种权威话语是公开标明身份的“仲尼曰”“孔子曰”, 《左传》共有23处, 《礼记》共有121次, 其构成形式与意义几乎完全与“君子曰”相同, 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君子曰”。在对“君子曰”“仲尼曰”的强势话语分析中可以看到新君子群体的思想、历史、道德和文化等方面的的优越感与自信心。
1. 思想立论
“君子曰”热衷于思想的阐释, 常常以一种启蒙者的角色站在哲学的高端, 引领教训。春秋时期流行的哲学概念“君子曰”皆有讨论, 相关论说丰富了“仁”“礼”“义”等理论命题的内涵。《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流亡到齐国, 齐桓公盛情招待喜不自胜, 酒酣耳热之际渐渐失去理智, 要求“以火继之”。却遭到公子完的婉拒, “君子曰”对此议论道:“酒以成礼, 不继以淫, 义也。”此处的“义”, 就是在生活的快乐与礼义规范之间找到平衡。鲁宣公四年, 郑公子公胁迫子家弑君, 子家初有不忍, 最终没能坚持到底, 酿成弑君惨案。因此君子议论道:“仁而不武, 无能达也” (86) , 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引发普遍的思想来思考, 仁爱也许有勇武, 君子哲学仍然体现了不偏不倚的中庸精神。
“春秋笔法”也是通过“君子曰”的形式提出的 (87) , 春秋笔法不仅仅是新的历史学方法的确立, 也是新的人文思想和美学精神在历史领域里的延伸。更是通过“仲尼曰”的形式, 鲜明地提出“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不言, 谁知其志?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88) , 文, 是文饰, 是文采, 就是通过对语言自觉的修饰, 达到传之久远的目的。如果我们把文学理解为语言的艺术, 这里已经触及到了语言与文学关系的根本问题。应该注意到“君子曰”的思想立论, 无论是礼与酒、仁与武、言与文等哲学命题, 还是微与显、志与晦等历史笔法, 或者言与文、言与志等文学观念, 看似矛盾对立, 其实更是和谐与交融。在中国古典哲学中, 从来没有绝对的东西, 没有绝对的对立, 也没有绝对的正确, 而是对立中的调合, 差别中的融合, 相互包含、相互会通, 这就是新君子群体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
2. 道德褒贬
从道德的立场出发臧否人物, 评价是非, 是“君子曰”的重要内容。“君子曰”对待历史人物, 或是激情颂扬, 或是激烈斥责, 带有鲜明的爱憎情感, 而道德观念则是斥责、或是礼赞的主要依据。按《左传》所记, 隐公元年在颖考叔的策划下, 失和的武姜与郑庄公母子相逢于大隧之中, 其乐融融, 母子如初。君子于是曰:“颖考叔, 纯孝也, 爱其母, 施及庄公。” (89) 隐公四年, 卫大夫石碏大义灭亲, 杀死与州吁一起弑君的儿子石厚。“君子曰”充满深情地称赞道:“石碏, 纯臣也。” (90) 这里的大义是臣子对君主的忠诚, 而父子之间的人伦关系则是小义, 是应当服从于君国大义的。庄公十四年记楚国忠臣鬻拳两次力谏楚文王, 强令楚文王改正错误, 而自己又为对君主的无礼行为而深深自责, 刖足自刎, 成就忠义。《左传》“君子曰”称赞道:“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 刑犹不忘纳君于善。” (91) 襄公三年晋国贤臣祁奚告老, 而在举荐贤才时他举仇举亲, 出以公心, 不计物议, 君子谓引用《尚书》《诗经》, 称赞其“于是能举善矣” (92) 。君子臧否人物时, 总感到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 正是因为他们站在“忠”“孝”“义”“勇”“公”等道德制高点上, 由此衡量是非、评判历史显得底气十足, “君子曰”以语录的形式为道德的践行者们树碑立传。
“君子曰”的批判, 也是站在君子的道德立场出发的。桓公二年宋华督父杀死孔子六世祖孔父嘉, 并趁机弑君宋殇公。对此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 (93) 而强烈谴责, 在儒家伦理中“无君”是滔天之罪, 这里有对华督父的严厉批判, 也隐隐有对孔子家族的深切同情。“君子曰”的批判有针对邦国家族的, 也有关于日常小事的。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以息妫貌美而力劝楚文王灭息, 息妫归楚后终日不言, 楚文王为取悦息妫而灭蔡。对这种以害人始而以害己终的行为, “君子曰”引用《尚书》“恶之易也, 如火之燎于原, 不可乡迩” (94) 的名句, 谴责蔡哀侯种种恶性不能收敛, 不无讥讽地嘲笑其自取灭亡的下场。宣公二年, 宋将羊斟为了发泄一点生活中的不满, 竟驾着战车将主将华元送入敌军。对此“君子谓”以罕见的愤怒, 指责“羊斟非人也” (95) , 认为羊斟已经越过了人的最低道德底线。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 “君子曰”以“礼”作为批判武器, “礼”里面不仅仅是古老的礼俗, 更是春秋新人文主义思潮背景下经过重新阐释的原始人道主义思想。鲁庄公夫人哀姜伙同庆父连弑两君, 最后为其母邦齐国所杀, 尽管其恶贯满盈, 僖公元年还是以“君子以”的形式发表意见, 认为“杀哀姜也, 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 (96) , 对女子保有一份尊重和谅解, 这是难能可贵的。“君子曰”的臧否褒奖, 一直有一种理性的精神。隐公十年、十一年, 《左传》三次以“君子谓”的形式对郑庄公的言行予以褒贬, 其中两次以“正矣”“有礼”赞扬, 而一次则是以“失政刑”予以谴责, 显然这里的“君子谓”是从是非出发, 而非个人好恶。
3. 知识立场
“君子曰”的论述里, 显示出新君子群体广阔的知识视野。以《左传》为例, 涉及“君子曰”“君子谓”“君子以”的评论共有80条, 其中引《诗》56条, 引《书》6条, 引《易》1条, 引志3条, 引《史佚》1条,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竟然出现了2次评论《春秋》的文字。而以“仲尼曰”“孔子曰”出现的23处评论形式里, 其中引《诗》6处, 引《书》3处, 引《志》1处, 引“有言”2处。从这些数字里, 可以看出君子立论征引典籍的丰富程度, 广涉文学、历史、哲学、格言、传说等诸多领域。不唯如此。有一个事实常常被研究者忽略, 就是所谓“君子曰”等对《礼》的引用, “君子曰”等引《礼》, 或明或暗, 明者如“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君子曰, 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 (97) , 暗者如“君子曰:‘服之不衷, 身之灾也。’” (98)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99) , 明者容易辨识, 暗者容易忽略, 如果加上“君子曰”引《礼》, 则整个“君子曰”的议论都是建立在礼乐经典知识基础上的, 新君子群体的思想理论是从知识的立场出发的, 君子的思想理论流淌着文化经典的书卷芳香, 这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历史趋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wenxuelunwen/5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