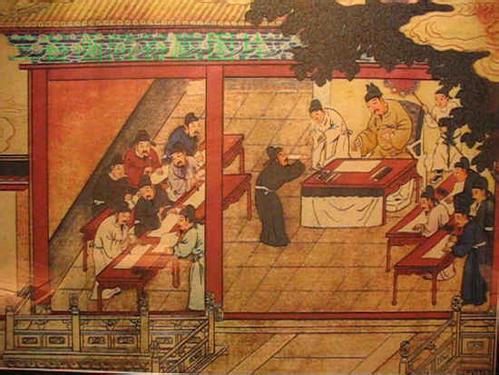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进入20世纪, 中国文学批评被带入一个新的社会场域和文化语境之中, 其社会性和变革意识越来越趋于强烈和突出, 从梁启超的“欲新民”之说, 进一步转为提出打造“舆论之母”, 接以痛失“舆论之母”的地位, 为革命党人所接替。这体现了中国社会变革对于文学批评新的诉求, 不仅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呐喊出了先声, 营造出了氛围, 也为重新思考和把握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提供了某种从文化和意识形态切入的路径。
关键词:
欲新民; 舆论之母; 文学批评; 梁启超; 《民报》;
From “The Pursuit of New Citizen”to Forging “The Mother of Public Opinion”
Yin Guoming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之所以具有先声夺人的效应, 应当说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它其实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合奏”, 是多声部的交响乐, 不仅有社会和时代变迁的历史积累, 也有经济与文化发展失衡的思想落差;不仅可视作对西方文化冲击、启发之应对, 还饱含中国人自身长期受压抑的心理郁结之内蕴。如此等等, 都为中国进入一个“发声”时代提供了契机和机遇, 使文学批评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异军突起成为可能。
当然, 这一切也促使文学批评本身发生了变化和转型, 似乎以往温柔敦厚的面目, 在一刹那间就变为满面肃杀, 义正辞严;从过去偏于内敛的精神气质, 一下子调转方向, 转为勇于、乃至急于参与社会生活的外放型模式。在观念选择、言说方式和话语形态、修辞方式等方面, 都出现了很大变化。换句话说, 无论是所谓“批评时代”的来临, 还是文学批评之能够先声夺人的态势, 都是通过特定的思想、话语和逻辑方式得以践行和实现的, 其中所蕴含的时代、历史征兆和奥秘, 就隐藏在这些具体的批评实践和展演之中。因此, 对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文化功能和效应的探究, 就不能不立足于文化和批评之间的关系加以推展, 继而深入到文学批评的论述策略和话语方式之中。
一政改诉求的驱动:走向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角度着眼, 文学批评之崛起, 实为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要求之应和与共奏, 以一种特殊方式迎合和反映了中国特殊的文化状态和历史要求。这就是说, 尽管中国已经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甚至已经聚集了足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资源和能量, 但是, 一时还未能产生有足够感召力的思想和文化力量, 构成改变中国思想状态的文化契机, 为社会变革提供整体性转型的选择和方向。这时候, 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破门而入, 使得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局, 甚至于陷入“被开除球籍”之焦虑的危机状态, 中国社会变迁很可能会继续在以往“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中循环往复, 难以真正进入“天下至变”的时代。
所以,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 西方文化的进入促使中国打破了这个瓶颈, 不仅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产生了刺激和催生作用, 而且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想象和建构的蓝图。其中, 最显著的表征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以及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形成和确立, 而这个过程亦典型体现了20世纪中国变革的最显著的特点, 即“政改驱动”自始至终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扮演着激发、驾驭和掌控一切的角色。
“政改驱动”显示了诸多问题背后的推力———其时, 政治是所有文化变动的推进器和发动机。所谓政治, 用最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关于治国理政和权力机制的学问和实践。而关于政治在人类文化, 尤其是学术和思想发展中的核心价值与意义, 恐怕在孔子和苏格拉底时代就已经成形, 历经近三千年, 至今依然没有失去意义和效应。
急于变革社会的政治激情, 无疑是促使文化意识形态日益膨胀和文人热切发声的思想激素。于是, 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发展中, 出现了明显的“政改诉求”与“意识形态先导性”相互支撑和相得益彰的情形。由于政治变革首先需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造势, 才使得文学批评能够脱颖而出, 成为社会变革的“马前卒”和“敢死队”。也正因为文学批评能够担当如此重任, 才使得自己能够在20世纪风光一时, 经历诸多历史磨难, 亦谱写了如此多的故事和传奇。
文学批评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契合和互动关系, 也为人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就世界范围来说, 随着公民政治、社会民主和大众流行文化的崛起, 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经典化和精英化意识逐渐淡化, 甚至变得不合时宜, 而政治的文学化, 乃至娱乐化倾向则日益加剧, 蔚然成风。很多政治家借助艺术创作和文学作品阐明己见, 甚至以此作秀, 用文学性的修辞方式来宣传政治主张, 推广执政理念;至于在公共场合借助各种媒体, 来一番激情演说, 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文化景观。这股潮流在世界范围内催生了众多能够激发人们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 进一步发挥实践效力, 从而影响甚至改变现实走向的文化产品和作品, 它们既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显明表征, 也是文学的, 甚至文学批评的精彩展演。
“新”的文学批评, 正是在这种语境和潮流中应声而起。其实, 在近代中国, 文学批评的先声夺人, 最初实从政论开始。它源自对于政治变革的诉求, 既迎合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现实要求, 也符合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和实际状态, 同时不断向“文学化”靠拢, 借用文学方式和元素发声和立言。这种“政改诉求”的表现和表达, 在不同社会状态中, 有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重心, 如果是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其可能以治国理政为要务, 但在社会变革的非常时期, 则会转移到对权力及其体制的质疑、颠覆等诸多方面, 在整个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域, 形成了尖锐乃至极端的话语权争夺、对峙甚至战争状态, 随时可能从思想、观念和话语范畴, 转换到用行为、肢体和暴力方式继续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 文学批评亦不断强化其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意识, 从过去注重文学鉴赏、品味和知人论世的视域, 开始转向注重社会效应、思想传播和宣传方面。对于这种转向, 梁启超、刘师培、鲁迅、茅盾、朱自清等, 都有不同角度和层面的认识和论述。从文学本体来说, 这种转向不仅意味着对于文学功能、效用, 乃至价值的新的发现, 还表现了一种文化立足点的转移, 即不再过于注重文学作品和现象本身的质地与特点、以及其艺术承传和美学效果, 而是关注其外在社会品相和思想意义, 并由此评价和判断文学及文学现象。
自然, 在中国传统文论资源中, 不仅有注重鉴赏、品味的特点, 同样也有与文化意识形态, 乃至政治互动的诉求。例如孔子文学思想就讲究兴、观、群、怨, 就体现了一种文学与政治相互融通、互动的意识。而在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中, 同样融注了这种中国传统文论意识。即便在一个社会剧变的时代, 梁启超的学术文化创新依然体现了古今文学的交接和传承, 其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先河, 而且在20世纪初成功构建了一种把政治与文学、社会效应和艺术诉求密切粘连在一起的批评模式, 在高扬文学和艺术价值和效应的同时, 把社会变革诉求和政治价值观, 推展和镶嵌到了文学之中, 实现了文学与意识形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互动和融合。
这种情景, 在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中皆有展演, 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向政治化、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转型之滥觞。
这是因为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开始把中国社会变革的焦点从政治体制转向了社会文化, 从过度依赖上层权力阶层转向了社会大众, 尤其是期待国民素质的培养和建设———也就是“欲新民”学说的提出。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欲新民”的企图, 1902年2月8日, 梁启超继《清议报》后, 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 大力推广和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从其办刊宗旨即可看出, 这是一份宣扬和推广“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的报纸, 而所开出的药方就是, 用“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 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本报以教育为主脑, 以政治为附从。……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 (1) 。这种依仗公共传播媒体, 以“为吾国前途起见, 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 持论务极公平, 不贪偏于一党派” (2) 的公共价值理念, 凸显了当时中国变革的文化转向, 一方面显示出从政治和实业向文化与意识形态转移的趋势, 另一方面也为文学批评的社会功用化、功利化乃至工具化提供了新的滋生空间。
从《新民丛报》第1期推出的《新民说》可以看出, 梁启超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崇圣尊经的模式, 不再托古以求改今, 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由此一改过去把中国未来之希望寄托于政制变法, 甚至最高统治者一人之意愿的想法, 把中国不能“屹然强立, 有左右世界之力”的原因, 一下子转移到了国民素质方面, 认为“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 所以“新民”不能不是中国当时由弱转强的“第一急务”。
这种转变积淀了梁启超从事政治变革事业的切身体验和切肤之痛, 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深刻的社会认知, 具有跨越文化局限和历史时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应当注意, 在这种以政治意图先入为主的论说和论述中, 潜藏着过度阐释的危险。由于过度强调“欲新民”的作用, 不仅有可能忽略, 甚至遮蔽了自己以往强调的政治权力和体制的重要性, 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有所漠视, 对于时下风波诡谲的时势变幻缺乏必要的理解, 且显示出了在阐释文本乃至一切可供阐释之物时, 已然先存“意图先行”“观念先行”的思维定势。
在这种思维定势中, 不仅文学, 而且几乎所有文化资料和现象都有可能被“征用”, 成为实现“欲新民”的手段和途径, 用以证明预先设定, 不容质疑的观点和意图。
“新史学”之说就蕴含着这种不容分说的极端逻辑, 一方面, 它破除了既定的旧的历史观念的禁忌, 突破了传统的历史叙述框架。另一方面, 为了突出其“新”, 采取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判断方式, 几乎完全切断了新旧之间的历史联系。例如, 对于所谓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分野, 梁启超的判断难免有过度和偏激判定之嫌: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3)
在这篇文章中, 梁启超对于“旧史学”的弊害和“新史学”的价值, 采取了最大限度的由己心出发的目的性阐释, 不仅认为中国史学著作“难读”“无感触”, 更指出其“无有激厉其爱国之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心, 团结其合群之力, 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的功能和作用, 继而呼吁:“呜呼!史界革命不起, 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4) (文中着重号为原刊所加) 从文中作者所加着重号就可看出, 梁启超之所以倡导“新史学”, 甚至可以推广到其他学说, 都是为激起人们爱国激情, 达到振兴中国之目的。由此, 学术价值判断几乎完全以政治效用为唯一依归, 文学价值评判几已全然与政治诉求化为同体。
二互动与变体:关于文学批评的文化担当
此时, 梁启超不仅意识到学术在促进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 也开始关注到文学, 并极力促成政治与文学的结合和联姻, 期待用学术、学理和文学的方式打开中国社会变革与进步的新天地。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孕育和隐藏着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机, 文学批评的蜕变也在悄然无声中进行。随着体制内政治变法的夭折, 梁启超开始借助文化和学术来助推社会变革, 他从日本等国家的实践中, 意识到了文学在政治变革中的效应, 并不断开掘其中的文化能量, 大力张扬“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意义, 进一步拓展、引进和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广阔面相, 注重政治理性与文学批评的互动效果。
马克思和尼采或许就是在这种情境中进入梁启超眼帘的。1902年10月16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期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 就关注到这两位当时在西方最有影响、也最具叛逆性的思想家, 他称马克思 (文中译为“麦喀士”) 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称尼采 (文中译为“尼志埃”) 为“个人主义”, 说马克思认为“今日社会之弊, 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 (5) , 即为当时学界所瞩目。
而就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 梁启超还用诗表达了自己励志改革的决心:
献身甘做万矢的, 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 更揅哲理牖新知;
十年之后当思我, 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 海天寥廓立多时。 (6)
这首诗正好附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之后, 表明梁启超变革社会的思想此时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换, 即从直接的政治改革路径转向了借助思想学术的力量, 因为他从历史中发现了新的“文明进化之迹”, 例如就欧洲近世以来社会变革来说, 梁启超就认为, 其首先来自于文化学术之兴盛, 人们“乃大从事于希腊语言文字之学, 不用翻译, 而能读亚理士多德诸贤之书, 思想大开, 一时学者不复为宗教迷信所束缚, 卒有路得新教之起, 全欧精神, 为之一变” (7) 。
于是, 《新民丛报》不仅成了梁启超推广自己政治主张、以学术之力推动社会变革的平台, 而且也是积极谋求与文化意识形态场域的互动, 增强传播效应的通道。梁启超不仅推出长篇政论《新民说》, 大力倡扬和宣传独立、自由、平等、公正, 以及爱国、爱社会、爱民族的思想, 从正面激励人们树立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奋发图强的意识, 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没落和腐朽因素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可说已然早于“五四”话语, 开启了“国民性批判”的先河。
不仅如此, 梁启超还与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等人, 于1902年11月, 创办了附设于《新民丛报》的文学刊物《新小说》, 并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把文学批评为社会变革造势的功能, 提高到了观念和理论层面加以阐释, 进一步打开了文学政治化、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 文学批评体现出更为激烈的革命诉求, 并以过度甚至极端的阐释方式, 开始从政治变法的层面向整个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蔓延, 逐渐渗透和扩展到了更为边缘和细末的领域, 并通过学术研究表现出来———由此, 也形成了文学批评在中国独特的“泛化”现象, 出现了文体多样化、杂文化的情景, 批评意识几乎无孔不入, 与各种非文学现象、话题和文体纠合在一起, 其中既有政论性文章, 理论性阐发, 对时下民心的呼吁, 对未来国况的诉求, 亦有通过随感、杂记、书信、日记、回忆、甚至诗文创作中的直抒胸臆、借题发挥, 几乎都能够以批评面目呈现, 或者发挥批评的功能, 与所谓“对文学文本的阐释”难解难分, 完全跨越了学科、领域和文体类型的界限, 以多种文体的千钧之势直接突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之中。
在20世纪初, 这种情形不仅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 而且也开始扩展到整个文化和学术研究范围, 即便在文章学、文字学等看似与当下社会实际相隔甚远的领域, 也出现了相应的反应, 由此, 以学术变革带动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变, 又以此类“转变”作为“反作用力”, 促使治学理念在变革之路上再行推进。即便是在看似“沉潜往复, 从容含玩”的治学领域之中, 也不时以耸人听闻或激动人心的话题和论辩方式, 在学界带动, 在现实层面搅动着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神经。
而一向不被注意的是, 这种过度或极端阐释的论述定势, 不仅表现在倾向西化、鼓吹新思想的激进和激烈言说中, 也出现在主张恪守传统、倾向守成的文化论说中。或许可以把后一种呈现, 理解为一种文化思想的反弹和回应, 意欲通过立足本土文化的学术建树, 来驳斥和矫正前一种倾向的滋生蔓延。为了使论说显得更加有力, 后者在思维定势和论辩推演方面毫不承让, 丝毫不减过度乃至极端阐释的力度。
例如, 在20世纪初, 由于西学和新观念、新话语、新名词的引进, 语言文字之学一度成为学界热点和焦点, 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都投入了论辩, 实际上, 可说在此时便已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语言文字变革的大幕。之所以这样说, 不仅在于这场论辩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新旧文化开始分庭抗礼的新语境中进行的, 而且在于其所显示出的, 是与以往中国传统文章学、文字学截然有别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在20世纪初, 此种论说一开始就毫无温柔敦厚的中庸色彩, 极力渲染中国社会和文化所面临的危机状态, 一下子就把语言文字推到了关乎“种姓存灭”、“国家兴亡”和“文化复兴”的境地, 继而也赋予相关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守护以“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梁启超语) 的政治决定意义, 渲染出一种不能不就此决一死战的悲壮气氛。
由此, 历来被视为“小学”, 在古籍中孜孜寻求推衍历程的语言文字也一跃成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敏感话题。1903年, 邓实 (8) 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就显示了这种论辩气势。首先, 这是一篇充满危机、忧患, 甚至恐惧意识的论文, 为整个论文的过度阐释提供了思想氛围;其二, 在这篇论文中, “独立”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 “不独立则苦海酷酷沦地狱而永幽, 能独立则铜像巍巍于青云而直上” (9) 。其三, 正是因为将之与整个国家命运紧密勾连, 借助“中国独立”的重要性, 语言文字的“独立”就变得非常重要, 不仅是文化家园的根基, 关乎中国人种的纯灭, 而且在全球化文化竞争中, 亦是最终决定胜负的必争之地。
把语言文字之争, 直推到如此重要、决定性的文化前台———这似乎比西方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早了很多年, 不能不说为日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营造了氛围。正是因为邓实意识到, 这种语言文字的危机可能会直接影响中国文化和精神元质, 使得后者有可能不断被消磨, 从而使得国人在现实生活层面“堕入苦海”, 所以意欲激起学界对于语言文字状态和问题的重视。不仅如此, 也正是在这种由先置的危机和忧患意识诱发的论述中, 语言文字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被层层放大、节节拔高, 甚至被带入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的战场, 成为20世纪中国乃至全球化“文化战争”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例如, 邓实就特别强调:“其亡人国也, 必先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姓”, 并把这种危机直接落实到了当时的世界情势中:“哀哉!是故古之灭人国者, 伤百万之兵, 縻大万之财, 龙争虎战, 相屠响戮数十载, 然后仅乃克之;今之灭人国也, 不过变易其国语, 扰乱其国文, 无声无臭, 不战而已。湮人国圯人种矣。此欧美列强所以多灭国之新法也。” (10)
这或许是中国学术界把“文化”“文字”与“战争”“人种”直接联系起来的最早提法, 也是最早把“文化”“文字”拖入战争和战斗思维态势的学术表述。而令人有点匪夷所思的是, 竟然是语言文字、文学, 成了引发这场决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文化战争的导火线。既然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文化战争, 那么使用何种激进和极端的论述和论辩方式, 把论题及其意义强调到何种程度和高度, 皆不再有任何推论的底线和界限, 由此也成为此后文学批评和论辩中“无限上纲上线”的动因之一。
此时的邓实不过25岁, 比1918年写《狂人日记》时的鲁迅年岁还小。
新文学运动终于在十几年后, 将此类观念在整个文化领域全方位引爆。实际上, 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不过是从相反方向, 重现或重演了这种过度或极端阐释的逻辑。例如鲁迅, 尽管用一种极其决绝的方式来反对一切“保存国粹”的论调, 但是他的恐惧却与邓实、章太炎当年有相通之处:“许多人所怕的, 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 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11) 此类论述背后的推演逻辑, 同样是将“语言文字”直接与“国家命运”相勾连, 这实则与早年的邓实并无二致。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wenxuelunwen/5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