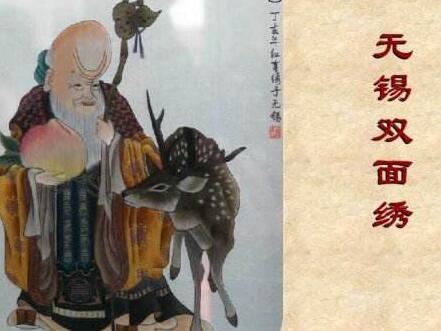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在民众生活中的口头传统和语言艺术, 具有区别于其他传统艺术的特性。要实现科学保护, 就要在尊重传统、呵护遗产的基础上, 采取有针对性且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法, 即:通过挖掘抢救, 做好基础性保护;通过宣传教育, 落实传承性保护;通过合理利用, 坚持发展性保护, 使之活在当代、融入生活、造福于民。
关键词:
民间文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 基础性保护; 传承性保护; 发展性保护;
作者简介:李荣启 (1955-) , 女, 汉, 北京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理论, 艺术学理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
基金: 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论” (项目编号:13BH076) 阶段性成果之一;
Protection of Folk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 Rong-qi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Marxism Theory,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other traditional arts, folk culture i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n oral tradition and language art living in people's life. In order to scientifically protect, we must do basic protection through digging and saving. We must implement inheriting protection through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We must make protection sustainably through a reasonable utilization so as to let it live in contemporary world and integrate it with living and be helpful to people.
Keyword:
Folk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ic Protection; Inheriting Protection; Developing Protection;
民间文学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 它是指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创作、传承、传播、共享的口头传统和语言艺术, 主要包括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叙事、谚语、谜语等, 它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源泉, 它记录了各民族起源、历史、发展及先祖的功业, 口传着历代传下来的生产生活经验与智慧, 展现了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生活实践传统、社会风俗画面, 熔铸着各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审美特性等, 既是个体的生命表述和族群的历史记忆, 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
早在正式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前, 我国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就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 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编纂和出版工作, 对我国境内各地的民间文学进行了全面采录和系统整理。2009年,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集成”省卷本90卷的编撰圆满完成并已出版发行。据不完全统计, “三套集成”共搜集民间故事184万篇, 歌谣302万首, 民间谚语478万余条。2005年开始, 在文化部的统一部署下,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建立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体系,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至2014年,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我国有《格萨 (斯) 尔》《玛纳斯》《赫哲族伊玛堪说唱》分别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中, 民间文学占有155项;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 民间文学类的代表性传承人有77名。
但是, 由于当代社会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 农耕时期的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正在解体, 以民间生活为土壤且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式微。受众群体日益减少, 代表性传承人进入了去世的高发期, 一些民间文学项目处于急需实施抢救性保护的濒危状态。面对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新形势、新挑战, 我们应该在尊重传统、呵护遗产的基础上, 立足当下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 采取有针对性且科学合理的保护方式方法, 使传承于民众中的各种民间文学再现出生机与活力,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代代相继。要使这一保护、发展的目标成为现实, 笔者认为主要应采取以下方法对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
一、挖掘抢救:做好基础性保护
虽然我国在抢救保护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是, 进一步进行挖掘抢救民间文学资源和项目仍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因为民间文学属于口头流传的“文化遗产”, 没有文字保留下来的系统文本, 是靠祖祖辈辈口耳相传、口传心授, 艺人在讲授、演唱中不断丰富、充实而积累下来的, 是一个民族或地区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承载着民间文学的传承人一旦离世, 就会造成“人亡艺绝”。如今, 不少老艺人已经带着遗憾故去, 在世的代表性传承人也都年事已高且后继乏人。面对这种情况, 抢救性保护仍需亟待加强。
实施抢救性保护要注重做好基础性保护工作, 即调查、确认、立档、保存。虽然我国自2005年至2009年开展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圆满完成, 但仍然需要深入进行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工作, 在深入进行专项调查中方能更好地对濒危项目进行抢救性保护。况且, “隔几年对以往调查过的地方做回访和重访调查, 进行比较研究, 是国际民俗学界常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和惯例。”[1]28-29因此, “采风是一项必须持之以恒的工作, 民众中的民间文学活动, 是一种不断发生着变化的文化现象。前人的采风可以说明前人所在时代里的民间文学状况, 都又不能代替今天的情形。”[2]414深入实际的调查, 还会发现和挖掘出新的口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如贵州省麻山地区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在2009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中发现的《亚鲁王》, 便是当年“中国十大文化发现之一”。《亚鲁王》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 是在苗族葬礼上唱诵, 由东郎 (歌师, 苗语音译) 传唱, 仅靠口头流传, 没有文字记录。《亚鲁亚》传唱的是西部苗人创世与迁徙征战的历史, 其主角苗人首领亚鲁王是被苗族世代颂扬的民族英雄。自发现《亚鲁王》起, 政府文化部门便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搜集、整理、保护、研究, 2011年, 《亚鲁王》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2年, 《亚鲁王》由中华书局出版。目前, 如何增进当地民众对《亚鲁王》文化价值的认知, 怎样建构出有利于东郎群体传承这部史诗的有效机制和保护其传承的文化氛围等问题, 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探讨。《亚鲁王》的发现和保护说明深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非常必要。
对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理念, 要充分尊重被调查者及其作品的真实性。调查者不能轻视文盲艺人, 认为他们的说唱是民间的、老百姓的语言, 不如文人语言精炼、有品位, 因此便出现了根据自己的想法和观念去删除一些认为是史诗中重复或累赘的段落或诗节, 人为地改编原作。对如此删改, 钟敬文先生指出:“而这里恰恰正是口语思维区别于书面思维的重要特征, 正是歌手惯常使用的‘反复’或‘复沓’的记忆手段, 而‘冗余’、‘重复’正好表明这是口头文学的基本属性。”[3]9他认为:“口头性的深入探讨, 将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民众知识, 理解民众观念中的叙事艺术。”[3]9在田野调查中, 调查者要坚持本真性的原则, 尊重口头传统和民间艺术家的个性风格和艺术创作, 不加修饰、不加歪曲地真实记录, 避免因人为的删改和加工对民间文学造成扭曲和破坏。上个世纪初叶, 顾颉刚、刘半农收集民歌, 忠实记录方言, 不做任何文人的修饰加工, 给后人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民歌文本。这样的范例值得效仿。另外, 还应尊重调查对象的权益, 要考虑到他们的年龄、身体状况、情绪、禁忌等因素, 进行妥善周到的安排。对口传文学的采录, 应坚持在艺人生活、传艺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 只有在原有的文化空间或一定的仪式里, 面对家乡的民众, 艺人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 激情满怀, 演唱自如。在现场, 调查者不仅能真实全面地进行实地采录, 而且能够切身感受到口传文学的艺术感染力, 观察和了解到其对当地民众的影响力。
对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要向当地文化部门和老文化工作者了解当地民间文学的蕴藏情况与地域特点, 以及过去的搜集情况, 特别是要了解在同一文化圈中哪些乡镇、村落属于资源蕴藏较为丰厚者, 有哪些著名的传承人, 然后确定一些重点村镇和若干传承人 (讲述者、歌手) 。在掌握了全面情况的基础上, 再有选择地进行调查和采录。”[1]30在进行田野调查前, 不仅要确定调查线索和采访对象, 而且要拟定好可行的调查计划, 根据民间文学的特点, 调查与记录的内容应包括: (1) 项目生成与传承的历史、过程、演变情况; (2) 收录与项目相关的资料及文本 (异文本、手抄本、出版本等) 和形象文本、影像资料 (说唱表演的语言、音质、形体、表情及表演的场所、受众、氛围等录音录像资料、音像制品等) ; (3) 与项目相关的民俗事象、物质载体、历史传说等; (4) 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料、生存情况、传承谱系等; (5) 项目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申报书及审批文件等。采访中, 对于讲述者讲述中运用的方言、俗语、口头语、套话、韵语、称谓等, 要尽可能准确地予以记录。“记录下来的每一篇作品, 都要在文本的末尾署上下列几种背景材料:讲述者、演唱者、表演者的姓名及男女、民族、身份、年龄、文化程度、简历、传承 (家传或师传) 、居住地及联系地址等;采录者 (包括翻译者) 、随行者的身份、工作单位、文化程度、联系地址;采录地点 (包括具体环境, 如鼓楼、场院、马棚等) 、采录年月日。”[1]35这样的调查和采录才能做到真实全面。
调查工作中收集、采录到的大量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资料, 是非常珍贵的成果, 应当通过认真的整理研究、确认立档, 给予妥善科学的保存保护, 进而才能方便利用。口传文学生动地描述了民间社会的真实生活, 形象地反映了各族人民的理想、情感、愿望, 以及生产生活的智慧和经验, 它像“多棱宝石”般闪烁着不同的文化光彩, 因而具有多种功能和学术研究价值。但是, 口传文学具有较大的变异性, 随时代的发展或传承人的离世易受损益或流失, 所以, 将采录的文字、声音等资料经过认真整理和翻译, 将其文本化是十分必要的。比起口语来, 文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固定性, 便于保存、利用和传世, 还能更全面地了解遗产项目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演变, “如吴歌, 宋代以前有郭茂倩《乐府诗集》, 明代有冯梦龙的《挂枝儿》《山歌》, 民国间有顾颉刚等人的《吴歌》甲乙丙丁诸集, 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时代的吴歌语言上差别很大。
我们现在靠着这些文本, 可以考知这一口传文化遗产的演变。”[4]354要将口传资料文本化, 就应由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学者, 依据科学的翻译方法, 将少数民族口语资料准确精到地译为书面文本, 便于保存和广泛地宣传传播。这是一项难度大、要求高的工作, 需要高层次专家的介入, 并制定出相应的规则和方法。比如《亚鲁王》的翻译, 原先只按川滇黔苗文通行的8个声调书写符号来记音;而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李云兵介入后, 根据当地语音声调系统复杂的实况, 制定了一套声调书写符号。与川滇黔苗文相比, 增加了3个声调书写符号而使之成为11个, 这才较为准确地记录了《亚鲁王》史诗。[5]317调查的遗产成果经过整理后, 还应登记立档, 这是基础性保护的重要一环。因为, 开户立档, 能够“将其生命原质冷冻化, 有效地储存其生命之根, 为后人真切地了解、利用乃至复活提供可靠的原始依据”[6]38。建立完整的档案, 既是调查工作的延续, 也是其他保护工作的基础, 还有利于妥善保存资料, 防止损毁流失。
对调查资料在立档保护的同时, 应在系统梳理、研究的基础上, 汇集优秀成果编纂出版丛书、作品集或调查报告, 形成书籍与文献, 既有利于项目的传承保护, 又能扩大其社会影响, 这是调查之后重要的后续工作。近年来, 有不少民间文学类调查成果已结集出版, 如《陆瑞英故事歌谣集》 (2007) 、《谭振山故事精选》 (2007) 、《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 (2009) 、《武当山南神道民间叙事诗集》 (2009) 、《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 (2010) 、《口头传统新档案———民间故事的录音整理与记忆书写类比文本》 (2011) 、《亚鲁王》 (2012) 、《钱王传说集成》 (2012) , 等等。有的省市对本地区口传文学的重大项目已进行过多年抢救性调查和保护, 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如吉林省文化厅实施的满族说部抢救工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 该省就开始进行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 组织社科工作者奔赴吉林、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四川等满族聚居地区进行调查, 寻访说部传承人, 他们经过艰辛的努力, 了解了满族说部在各地流行情况, 并对一些传承人讲述的说部进行了录音。
后来由于一些原因, 使这项工作中断了。2001年8月, 吉林省文化厅重新启动了这项工程。2002年6月, 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抢救与保护满族说部这一项目, 于2003年8月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国家课题, 2004年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2006年5月, 满族说部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多年来, 众多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参与了这项工程, 搜集了500余盘已故传承人遗留的讲述说部的录音带, 寻根探源查访仍健在的说部传承人, 忠实地记录、整理, 经过数年努力, 于2007年12月、2009年4月, 先后分两批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 计28部, 1200多万字。该丛书出版后, 他们继续扩大线索、深入挖掘、审慎认定, 组织实施了第三批书目的抢救工作。又经过五年的努力, 已完成满族说部丛书第三批书稿计26部, 900余万字, 交付吉林人民出版社。至此, 抢救满族说部工程完满收官。[7]5-6这些由专家学者主导或参与完成的调查成果汇编或丛书, 为民间文学重要项目的传承保护、宣传传播、有效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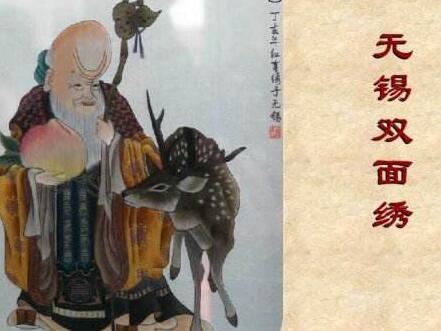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 我们还应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 以现代影像和数字化手法, 将各种民间文学活动及表演制成音像制品和多媒体制品, 并建立信息数据库。数字化存储, 既便于长期保存和利用, 又可以向广大民众宣传传播, 能广泛地弘扬优秀的民间文学艺术。2010年12月30日,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 已将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记录、采集的大量民间文学文字和图片资料进行了数字化处理。该数据库是我国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性资料库, 是我国口头文学资料最为系统的数据库。2011年, 文化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吴歌作为民间文学类的试点项目, 被列为该工程一期项目。2012年11月, 江苏省苏州市启动了吴歌项目数字化保护工程, 并已完成建设通过了验收, 为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存与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做法和经验。2012年4月,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启动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史诗百部工程”, 以仍在民间活态传承的史诗为项目对象, 记录100组艺人演述的史诗, 形成资料集、影音、数据库成果。[8]运用数字化技术 (如录音、录像) 并建立数据库, 是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的有效方式, 不仅能对采录的资料、作品等进行真实、全面的保存与保护, 而且能够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 为民众更好地传播、利用这些资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和数字博物馆, 要不断充实、丰富、完善。相关部门要加强科学管理, 应设熟悉业务、懂技术的专业人员, 负责数据库的建设和管理, 要责任落实、管理到位。
二、宣传教育:落实传承性保护
民间文学是口耳相传的艺术, 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 也就是说口传的民间文学作品是依附于歌师、传承人而活在民间的。所以, 民间文学保护的重点应落实在活态传承上而不是静态保存上。文化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1986名, 其中, 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有77名, 仅占总数的3.88%。有31个项目只有一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而且老龄化严重, 这说明民间文学生存濒危, 传承状况堪忧。如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玛纳斯》, 三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先后离世, 《玛纳斯》史诗面临着传承人断代的危机。要改变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状态, 需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传承机制的建设。
在抢救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 各级文化部门对代表性传承人承载的民间文学遗产重视采录和资料的收集, 形成了不少民间文学遗产成果, 如“集成”“汇编”“丛书”之类的书面文本, 以及依据现场录音、录像制作的影像作品、多媒体作品等, 但这些成果都是静态的, 仅靠这些是无法实现活态传承的。而代表性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才是实现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根本途径。所以, 抢救性保护的重点应是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传承人的传承。尤其是对那些年事已高尚能承担传承义务的代表性传承人, 应给予悉心的关照及做好各方面的保障, 使他们能够在有生之年培养出满意而合格的接班人, 实现薪火相传。这不仅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给予他们津贴、补贴等经济资助, 更需要落实法律的规约、政策的支持;不仅需要为他们提供带徒传艺的场所、展示技艺的平台, 更需要因人而异且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帮助, 如可以借鉴韩国《文化财保护法实施规则》中的规定,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配备专门的助教, 而且助教人选必须经过相关专家审查认定。配备得力的人员协助高龄传承人开展传习工作, 能够保障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有了新一代传承人, 才能保障民间文学中的濒危项目不会失传, 并使之活在民间、活在当代。
静态成果所形成的中国民间文学宝库, 是实现活态传承的基础和依据, 是需要后人学习、继承、发展的文学艺术传统。应当通过宣传传播、教育传承有效利用民间文学资源和成果, 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变“死保”为“活保”。要通过宣传教育, 落实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保护, 需要重视两方面的教育, 即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面向广大民众的教育, 通过向民众宣传普及民间文学知识、作品, 开展各种样态的民间叙事活动, 使民众了解、认知本地区自古传承至今的民间文学瑰宝, 使被弱化的民间文学活动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这方面有些地区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推广, 如浙江各地的文化工作者注重民间文学在当下民众中的活态传承, 采取了不少有效的做法。舟山市定海区将以前搜集整理的一大批定海民间故事重新又从文本回到口头, 专门邀请一位故事家用舟山方言来讲述这些故事。一批口头故事先后在舟山电视台播出, 并出版了《定海民间故事精选———方言音频版》, 每本书后都附有一个光盘, 运用文字和声音两种方式进行传播。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故事之乡”的余杭区一直致力于传统故事在当代的传承, 还特别强调现实题材民间故事的创作和传播。早在1991年, 塘栖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故事沙龙。这个沙龙一直坚持开展各种民间故事的传承活动, 成员有40多人。2002年, 他们又把故事搬到互联网上, 开办了国内第一家“故事派对网站”, 日访问量最高时达6万多次。他们还在网上开办故事创作网校, 免费培训28期, 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了一大批写故事的人才。近年来, 塘栖故事沙龙还在当地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举办每月两期的“美丽洲”故事会。故事会上, 既讲传统民间故事, 也讲当地作者创作的现实题材民间故事, 很受欢迎。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当地的民间故事传承逐渐出现复苏的态势。[2]417-418这也证明特定的环境、场合, 对于作为口头传统的民间文学的传承至关重要。这些环境和场合既包括固定的时间和空间, 如庙会、故事会、歌圩等, 也包括没有固定的时间和空间, 如劳动场合、节庆活动、人生礼仪中的讲唱。任何活态民间文学的传承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场所或场合, 倘若失去了讲唱活动约定俗成的语境和场合, 民间文学就会走向衰亡。基于这样的认识, 有的民俗学者提出, 最为理想的方法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恢复”民俗场;有些民俗场不可能再恢复, 但可以采用“移植”的方法, 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间文学演述民俗场, 如传统赛歌、对歌的形式可以引入民众生活及新的民俗活动中。[9]180-181的确, 如何恢复、激活或营造民间文学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文化空间、文化生态, 是一个值得重视并需要付诸保护实践的问题。然而, “无论是保持、恢复还是重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 关键都离不开创建和享用这些文化的民众。当这些文化事相真正回归民众, 在他们生产生活中扎下根来, 就成为稳定的文化生态, 使相关的民族文化财富得到切实保护了。”[10]475
民间文学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也是各级各类学校普及中华传统文学艺术及实施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但长期以来, 我国民间文化教育十分薄弱, 大学里曾一度停开了民间文学课, 全国各高校的民间文学教师几乎无一例外地改行去教中文专业的其他课程, 致使广大学子对民间文学作品和知识知之甚少。自新世纪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以来, 教育部门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中的传承和传播, 各地的中小学纷纷把本地区民间文学代表性作品引进教材、引入课堂, 进行民间文学的启蒙教育,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绍兴市秀水小学积极开展绍兴民间文学进校园活动, 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绍兴童谣引进教材, 编写出版了校本教材《绍兴民间文学 (儿童读本) 》 (上、中、下) 共三册, 以适合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要。同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绍兴童谣进校园活动, 该校专门组建了“若耶诵读社”传唱童谣, 并精心排练童谣表演。小社员们的童谣知识和表演技巧不断得到提高, 他们不仅经常在校内表演, 而且多次参加社区表演和专业展演活动, 广受好评。如今, 高等院校的一些院、系, 也陆续开设民间文学课或相关讲座。在普及民间文学知识中, 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青少年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的认知和认同。
学校教育也担负着培养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专业研究人才的重任。高等院校相关院、系应设民间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 为热爱民间文学且有才华的大学生提供深造的机会, 培养出一批能够胜任民间文学保护和研究工作的专门人才, 解决目前面临着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短缺的问题, 这是一项亟待加强的工作。实践证明, 大学师生参加民间文学的抢救工作, 可以加强科学性和科学研究工作。段宝林先生回忆道:“在20世纪60年代, 贵州省文化部门在田兵同志主持下, 发动文化、教育部门的专业文艺干部和师生进行调查收集, 出版了四五十本《贵州民间文学资料》, 钟敬文先生说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写出许多博士论文来。”继而, 他不无感慨地说:“如今, ‘民间文艺十套集成’有300卷之多, 每卷百万字左右, 比贵州的资料要多好多倍, 将会出多少博士论文和专著呢?可惜这种研究工作尚未引起重视, 教育部门和各地的社科院还没有组织力量去深入研究, 民间文学的博士点还是那么稀疏零落;文化部门还没有组织文艺院校、研究所的力量去深入研究, 以为只要把资料搞出来就行了。”[11]51这样的问题应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和着力解决。“同时, 要办好民间文学刊物, 发表民间文学家优秀的口头文学创作;应恢复或重建民间文艺出版社, 及时推出民间文学艺术研究的新成果。”[12]25
三、合理利用:坚持发展性保护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贯彻这一方针, 就需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才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对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做好基础性保护的同时, 应注重发展性保护。因为, 保护的目标是长远的, 不但要使我们抢救、认定、保存与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资源存留在当代, 而且还要在合理利用的基础上, 促其在现实社会中衍进发展, 使其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事实上, 凡能延续至今的任何一项活态口头传统、民间文学事象, 必定具有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新内容, 不然就会消亡或只能停留在文献、光盘中保存。这些活态传衍着的民间文学, 因为它“始终以口头形式的特点延续至今”, 易于“受到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威胁”, 因而“面临着消失的危险”。[13]3要改变这种濒危状态, 需要我们通过保护行动, 人为地为它们创造生存发展的条件, 修复文化生态环境, 促使口头传统、民间文学事象在保留自己的基因、特性的同时, 增强适应新时代、新环境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采取保护行动的理由。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资源的前提是合理, 合理即合乎理性。坚持合理利用, 不仅要树立起文化遗产合理开发利用的正确观念, 还要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机制, 并从多方面引导、规范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坚持合理性的方针。因为,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就像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发展, 给当地民众带来一定的实惠;另一方面, 若开发利用不当, 不仅会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资源, 而且会使原住民文化意识、精神感情受到贬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 政府提出“合理利用”的方针, 是有针对性的, 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中出现的问题及后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后果, 为了使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更理性、科学而确立的。目前, 在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中, 存在着不当利用、过度开发的问题, 如有的地区为了发展地方旅游产业, 招徕和吸引游客, 把本地流传的民歌、故事等随意改编、添枝加叶, 有的甚至添加进一些不健康的内容, 歪曲、滥用, 严重地损害了民间文学的特质。“在旅游文化开发中, 在不少地方出现了‘新编历史故事’‘新编风俗故事’‘新编山川故事’‘新编名人故事’, 不但没有给真正的旅游文化增光添彩, 反而造成了不少的混乱、问题。”[14]3这些不当利用、过度开发、盲目发展的问题, 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所以, 树立正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观, 充分认识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价值实现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把握其价值实现的内在规律, 是实现合理利用的基础。
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活在当代并造福于民,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为此, 坚持发展性保护,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题中应有之义。发展性保护是需要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共同努力方能实现的目标, 它需要做多方面工作。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要求, 通过“宣传、弘扬”使保护对象得以“传承和振兴”。在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 应利用现代传媒方式和手段, 加强宣传、传播与弘扬。历史上,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口头传播和纸质传播。但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 音像、影视、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手段, 为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传播与弘扬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更广阔的平台。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传播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涌现出了一些成功的做法。从2008年开始河北藁城市耿村拍摄1001集电视故事系列剧《古国一千零一夜》, 该系列剧是以《耿村故事一千零一夜》一书为蓝本, 用电视系列剧的方式对民间故事进行全新的演绎和传播。2013年, 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文化厅、山西广播电视台和万荣县委县政府联合出品, 山西卫视播出的28集贺岁剧《快乐的万家村》, 是以贺岁喜剧的形式讲述“万荣笑话”。2014年2月11日至13日,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连续3期直播的《中国谜语大会》, 首播和重播一共吸引了2.8亿多电视观众收看, 3场直播共有206万人同步参与实时猜谜, 此节目在民众中反响很大。之后, 在中国传统佳节元宵节到来之际, 《中国谜语大会》与电视观众和新媒体用户如期“约会”, 已连续举办了三年, 并已成为具有浓厚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氛围的全民猜谜盛宴。可见, 运用新媒体宣传、传播民间文学, 并允许作品根据时代变迁进行与时俱进的再创造, 这是活态保护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同时, 利用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艺术形式宣传、传播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保护方法。如黑龙江省将赫哲族伊玛堪说唱与望奎县皮影两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完美融合, 以伊玛堪说唱中的“莫日根阔力型”经典故事为基本素材, 创作出伊玛堪皮影戏《西温莫日根》, 已经巡演了30多场, 颇受各界民众的喜爱。[15]通过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相互结合, 且实现“珠联璧合”式的传播, 这种富有创新性的保护形式有效地促进了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 也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宝藏。由于民间文学是植根于民族土壤中、传承发展于民众中的生活文学, 它不仅内容包罗万象, 而且涉及到人类生产生活各个领域, 是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睿智的结晶, 因而具有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科学、经济、娱乐等多种价值。通过科学开发、合理利用这座宝藏, 可以繁荣当代文学艺术创作, 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使民间文学资源经过挖掘利用、转化创新, 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各种艺术, 使其以更鲜活的形式活在当代、融入生活。“民间文学作为一种口传文学, 已经在民间广为传播, 观众早已熟悉了相关人物及其故事情节, 其文化符号深入人心, 这是任何市场营销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像孙悟空、哪吒、花木兰、诸葛亮、梁山伯、祝英台、白素贞、许仙、包公等人物形象早就成了文化符号, 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观众心中。”[16]87所以, 利用民间文学资源创造的各类文艺作品、开发的动漫作品和旅游服务产品, 均能获得民众的持续认可和广泛接受。如利用脍炙人口的中国四大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等艺术作品, 广为流传。美国人利用我国民间文学资源拍摄的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 以及我国著名的动漫作品《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葫芦娃》《三个和尚》等, 都已大获成功。这说明, 挖掘好、利用好民间文学这座宝藏, 既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又能以其作为活水源头和艺术资源, 通过合理利用、转化创新, 开发创造出当代民众乐于接受的各种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 服务民众、造福当代。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Z].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2]顾希佳.非遗视野下的民间文学:以浙江为例[A].马文辉, 陈理主编.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4]刘承华主编.守承文化之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殊性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5]余未人.民间文学的文化生态及其对策[A].马文辉, 陈理主编.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6]贺学君.民间传说保护之理论思考[A].苏州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编.东吴文化遗产 (第二辑) [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7]谷长春.宏大的叙事口述的历史——写于满族说部抢救工程收官之际[A].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非遗保护与研究 (总第2辑) [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5.
[8]李珊珊.《中国百部史诗工程》编委会成立[N].中国文化报, 2014-11-06.
[9]郑土有.民俗场:民间文学类非遗活态保护的核心问题[A].马文辉, 陈理主编.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刘守华.论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A].王文章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集[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11]段宝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的几个紧迫问题[A].张仲谋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12]李荣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文集[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6.
[1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书编写指南 (中文本) [Z].
[14]丹珠昂奔.玉树文化研究 (序一) [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
[15]非遗剧目《西温莫日根》走进长春警营[N].吉林日报, 2016-07-22 (10) .
[16]汪广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意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1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