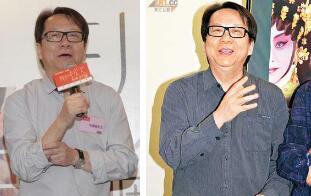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学术界对于香港“金牌编剧”杜国威的评价不一。“写情”是杜国威所擅长的, 然而戏剧并非“写情”就好, 戏剧的情感描写中必须积淀一定的社会人生思考才有其“情感本体”价值。正因如此, 杜国威成熟期那些在爱情、友情、亲情描写中蕴含着人生况味, 和感情世界中融入社会现实与家国情怀的剧作, 获得较好成就;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 他着重“边缘”感情予以商业化娱乐化展现的剧作则存在很多不足。杜国威追求雅俗共赏, 其创作推动香港话剧从小众文艺成为社会性的文化艺术, 这对于香港话剧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戏剧雅俗共赏固然可以通俗, 却应该力求“化俗为雅”, 争取“俗不伤雅”, 切忌“俗不可耐”。这是杜国威今后戏剧创作、也是香港戏剧今后发展应该着重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写情; 人生况味; 家国情怀; 边缘感情; 雅俗共赏;
ramatic Writing of Hong Kong Writer Du Guowei
Hu Xingliang
杜国威被媒体誉为当代香港的“金牌编剧”。然而学术界对于杜国威戏剧的评价分歧却颇大。有人称其为“杰出的剧作家” (1) ;有人则认为尽管杜国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剧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他更多是“通俗戏剧的大写家” (2) 。对于具体作品的评价也是这样。比如《Miss杜十娘》, 有人批评作者是“恋栈于掌声与票房, 挑一条易走的路, 由从俗、媚俗而至于粗俗、庸俗, 实在是一种‘迷失’!” (3) 有人则认为“杜国威所以要把一出严肃、沉重的爱情悲剧改编为嬉笑怒骂的喜剧, 除了讽喻丑恶、薄情的现实外, 还在向人们昭示那种自然、豁达, 闪烁着佛光禅理的‘爱情观’” (4) 。“金牌编剧”杜国威在香港戏剧舞台极具号召力, 那么,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其戏剧创作的成就, 其剧作在当代香港戏剧史上有何贡献、价值和意义?
综合来看, 学术界对于杜国威戏剧的研究存在三点认知偏差:一是总体评价过高, 对其戏剧创作的成就、贡献和不足缺乏实事求是的论述;二是以偏概全, 用他成熟期的成就和特点概括其全部创作;三是笼而统之, 对其戏剧“写情”的不同内涵和不同价值缺少深入分析。本文即是针对上述问题而进行的思考。
杜国威1979年开始业余戏剧创作, 1993年成为香港话剧团全职编剧, 将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 杜国威共创作了30多部话剧作品。早先, 经过《球》 (1979) 、《我系香港人》 (1985, 合编) 等剧的探索, 他在《虎度门》 (1982) 和《人间有情》 (1986) 两剧中, 确立了其戏剧搬演艺人生活和表现社会现实的两大走向。在其创作成熟阶段, 沿着《虎度门》走向, 他创作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1992) 、《剑雪浮生》 (1997) 、《寒江钓雪》 (2003) 等剧;沿着《人间有情》走向, 他创作了《遍地芳菲》 (1988) 、《聊斋新志》 (1989) 、《南海十三郎》 (1993) 等剧。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杜国威戏剧创作的黄金时期, 获得较好评价的《人间有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聊斋新志》《南海十三郎》都是这一时期推出的。90年代中后期以来, 杜国威未能突破自己而登上新的艺术境界, 更严重的, 是其戏剧描写从通俗走向庸俗、粗俗, 《城寨风情》 (1994) 、《Miss杜十娘》 (1996) 、《播音情人》 (1997) 、《梁祝》 (1998) 等剧明显出现滑坡。
杜国威的创作对于历史、时代、政治的把握比较“隔”, 擅长描写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生活和情感。他说自己“很喜欢写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5) 。学术界也是这样评价杜国威的。如香港学者指出“杜国威长于写情”, 认为“情”是其戏剧世界的精神面貌 (6) ;内地学者同样认为“人间有情, 也确立了杜国威一系列创作的基本主题” (7) 。然而, 只是笼统地指出杜国威戏剧“写情”———或者具体一些如写爱情、友情、亲情、家国情等———这一点是不够的, 因为同样是“写情”, 杜国威有些作品成功, 有些作品却失败, 可见戏剧并非“写情”就好, 戏剧的情感描写中必须积淀一定的社会人生才有其“情感本体”价值, 戏剧的感染力归根结底是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杜国威有些剧作 (如《人间有情》《聊斋新志》《南海十三郎》等) 在感情描写中融入社会现实和家国情怀, 有些剧作 (如《虎度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等) 在感情描写中蕴含着较多的人生况味, 有些剧作 (如《Miss杜十娘》《播音情人》等) 其感情描写则趋于庸俗和粗俗, 这些不同的思想内涵就决定了其戏剧“写情”的不同价值。
一、温馨怀旧:爱情、友情与人生况味
搬演艺人生活的《虎度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剑雪浮生》《寒江钓雪》, 都是写爱情和友情, 怀旧而温馨, 在杜国威戏剧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是杜国威特别熟悉的题材领域, 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弥漫于香港社会的“怀旧潮”在其戏剧中的体现。杜国威从小就喜爱粤剧和歌舞表演, 这些更多本土风味的艺术渗透在他的骨髓里, 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从80年代初开始, 香港社会进入“回归”历史转型期, 焦虑、期待、茫然等种种情绪在社会上弥漫开来, 一批怀旧题材的电影、戏剧、音乐应运而生, 怀旧成为普遍的民众心理和社会文化趋势。正是在这股“怀旧潮”中, 杜国威从小就熟悉的粤剧艺人和歌舞艺人的生活, 从其笔下走上舞台。《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 那是香港经济由萧条走向繁荣的兴盛时期, 剧中出现的丽花皇宫夜总会、天星码头以及《不了情》等流行歌曲, 承载着那个时代的香港记忆。同样, 任剑辉、白雪仙、唐涤生 (《剑雪浮生》) 、薛觉先 (《寒江钓雪》) 等粤剧前辈与老香港记忆相交汇, 故事讲述中, 那种浓浓的怀旧情感随着剧情发展而慢慢地渗出。如此怀旧可以引发香港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这些怀旧戏剧着重描写艺人的感情世界:爱情和友情, 温馨感人。杜国威对于艺人生活和感情的描写, 于1982年的《昨天孩子》中初见端倪, 尔后在《虎度门》中有较好拓展, 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剑雪浮生》中趋于成熟。这两部成熟期的怀旧戏剧, 前者主要写友情 (亦写爱情) , 后者着重写爱情 (亦写友情) , 但都是缅怀好人, 都写得温馨感人。作者说, 剧中“所有角色都是好人”, “因为我总觉得写一些有希望和美好的东西, 总比把生活里最痛苦的东西放上舞台为好……于是我便写了很多温情的东西” (8) 。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写抒情歌后姚小蝶, 20世纪90年代初自加拿大返回香港, 准备在即将拆除的丽花皇宫夜总会举办纪念演出。在这个当年她和露露、莲茜、凤萍歌唱生涯起步并遭遇爱情的地方, 姚小蝶心情激动、浮想联翩, 从而带出动荡岁月中, 她和沈家豪这对情人20多年相互守望的故事, 更是细腻地铺陈了四个歌女在艰辛的生活打拼中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姊妹深情。这些金兰姊妹的人生在这里也发生改变。凤萍掏心掏肺地爱着好赌的乐师Donny, 最后跟着Donny远走南洋, 在越南西贡一家夜总会被双双炸死。莲茜在歌舞厅看破红尘, 觉得“有钱没钱对我都是一样, 生老病死也不要紧”, 抽烟喝酒最后肝硬化而亡。只有露露善于抓住机会, 嫁夫生子家庭幸福圆满。姚小蝶自己呢?她与夜总会乐师沈家豪真心相爱, 但是男人的自尊使沈家豪不愿做当红歌星“姚小蝶的男人”, 因此对姚小蝶若即若离。然而“世情变, 人情在”, 露露和丈夫在20多年后为姚小蝶举办了这场纪念演出, 暗中安排沈家豪从美国返港在纪念演出舞台上与姚小蝶相会。演唱会上, 姚小蝶唱着当年沈家豪为她写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沈家豪吹着萨克斯风为她伴奏, “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剧终, 姚小蝶与沈家豪深情牵手、痴情相望。
杜国威写艺人生活明显受到传统粤剧的影响。他说, 年少时“看任剑辉、白雪仙交心的演出, 我神往、感动, 随着他们哀而哀, 乐而乐, 浑然在他们中间, 喃喃随唱” (9) 。传统粤剧大都是搬演男女爱情, 杜国威擅写最让他痴迷的粤剧前辈之间的爱情故事。20世纪50年代, 粤剧名伶任剑辉、白雪仙和大编剧唐涤生在香港组建“仙凤鸣”剧团, 创作演出了《牡丹亭惊梦》《帝女花》《紫钗记》《再世红梅记》等经典剧目, 有力地推动了粤剧艺术的发展。杜国威的《剑雪浮生》即是讲述这段奇缘。此剧表现了任剑辉、白雪仙、唐涤生对粤剧艺术的执著追求, 及其同舟共济、精妙合作的舞台创造, 更着意描写了他们———任剑辉与白雪仙、任剑辉与唐涤生、白雪仙与唐涤生———之间浓浓的爱情、友情以及介于友情和爱情之间的暧昧情感。现实中三人之间这种微妙的感情关系, 投射在穿插于剧情的“戏中戏”片段中, 形成戏里戏外相互映照的艺术景观;作者将他们的感情关系写得纯洁、温馨、感人。《寒江钓雪》也是叙述粤剧名伶的爱情, 写薛觉先与唐雪卿、江小妹、张德颐三个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
这些戏剧写的都是前辈艺人的爱情和友情, 其中也有不同。有的剧作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不只是写剧中人物的友情深厚、爱情守望, 它还展现了一群艺人的艰辛生活, 表现了这些艺人的人生酸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之所以取得较好成就, 就在于它透过这些艺人的生存抒写着一定的人生况味, 这种渗透着人生况味的感情才具有一定的内涵和深度。《虎度门》比较好也是因为这一点。然而必须指出, 杜国威的挖掘还不够深刻。即便是大获学界好评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虽对4个歌女的有情有义、对姚小蝶与沈家豪的情深意浓写得有血有肉, 但是, 对于那个年代社会底层的艺人、尤其是歌女被欺辱、被践踏的辛酸的人生, 少有真切的表现, 较少对于现实和社会的深入思考。
那些单纯写艺人的爱情或友情的戏剧就更显得单薄。杜国威懂得, 优秀伶人“一出虎度门, 便必须忘却本我, 浑然在扮演的人物之中, 喜怒哀乐重头雕琢, 在别人的故事里, 交自己的心!” (10) 他希望自己的剧作也能够“在别人的故事里, 交自己的心”。然而从实际情形来看, 他更多是“雕琢”故事以及故事中人物的喜怒哀乐, 而较少“交自己的心”———对社会人生的深切感悟与体验。人是丰富、复杂的, 人性是感性和理性、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渗透交融, 或是感性 (自然性) 中有理性 (社会性) , 或是理性 (社会性) 在感性 (自然性) 中凝聚和内化, 成为“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正因为如此, 似《剑雪浮生》这样近于“神性”的纯净感情描写, 就更多像是一个美丽的“成年童话”。人们难以从中感受到剧中人物与其所生存的时代、现实的深层联系, 难以看到人的生存和生命的真实情形, 甚至难以看到人物之间微妙的感情关系在其内心激起的深层心理波澜。其“写情”背后的历史感和人文内涵都比较缺乏, 更没有达到论者所谓“优美、典雅、诗意盎然” (11) 的境界。
然而问题不仅于此。杜国威有些剧作描写艺人的生活和感情还流露出一种小市民味, 缺少应有的现代意识。最典型的是《寒江钓雪》。此剧写粤剧名伶薛觉先与唐雪卿、江小妹、张德颐三个女人的感情。薛觉先年轻时潇洒不羁, 有很多女性痴爱他, 他也闹出很多风流韵事。剧中三个女人对薛觉先的爱是自由选择和追求, 作者将她们对于薛觉先的爱情写得曲折生动、纯情美好, 这些都无可非议。问题是薛觉先应该如何对待这三个女性, 特别是对唐雪卿和江小妹, 薛觉先应该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感情关系。剧中, 薛觉先为了江小妹, 曾先后两次怒掴唐雪卿。如果说第一次, 唐雪卿完全因为吃醋嫉妒而毫无理由地赶走纯洁少女江小妹, 薛觉先怒掴唐雪卿还情有可原;那么第二次, 是江小妹主动把她与薛觉先的儿子交给唐雪卿并离开薛觉先, 薛觉先却再次怒掴唐雪卿, 并且对江小妹说自己与唐雪卿所谓“恩爱夫妻”只是演戏给别人看, 这就很难值得同情, 并且与剧中所写唐雪卿正直的思想人格形成矛盾。作者擅长写情, 他是欲借“五哥 (引者注:指薛觉先) 和他三个至爱女人的微妙关系”, 去“探讨五哥的感情世界”, 以及“探讨‘爱’的精神” (12) 。然而像薛觉先这种旧社会名伶的情爱生活值得赞赏么?如此情爱生活能体现怎样的“感情世界”和“爱的精神”?如此情爱生活描写又将女性置于何种地位?男女之间的爱情、人格、权利的平等体现在哪里呢?
二、感情世界融入社会现实和家国情怀
后来回顾创作历程, 杜国威把1987—1991年视为其创作的“矛盾期”, 期间他“想改变自己的风格”。他说:“为什么会矛盾呢?因为我在想, 究竟自己应该跟从以前的风格, 继续写一些纯洁、温情的东西, 还是应该另觅一些新的东西来突破自己呢?” (13) 这次“矛盾”和“突破”最明显的改变, 就是杜国威在他所擅长的人物感情关系描写中, 渗透进了较多的社会现实和家国情怀。作者不再是一般地描写人与人之间的情和义, 而是进一步, 从人们的感情关系中去展开对时代、社会和现实的思考。所以, 只是笼统地评价“杜国威借助艺术想象, 形塑和睦的社群与温厚的人性, 精心营构一个伦理的乌托邦, 作为功利社会的对照。他不轻言批判, 也不提供反思, 历史的迷魅, 生存的困境, 统统消融在纯净化了的众生法相之中” (14) , 或笼统地说“人情美与人性美”形成杜国威“戏剧创作的特殊视角和主题倾向” (15) , 如果说它对于作者创作的早期阶段、以及那些描写艺人之间感情关系的作品还大体合适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有所突破) , 那么, 对于“矛盾期”之后努力“突破自己”的杜国威来说, 就不大准确。也正因为如此, 如果仍然着眼“写情”来评价杜国威“矛盾期”之后的创作, 例如, 认为《南海十三郎》着重是写“两段君子之交的师徒情谊”, 薛觉先、南海十三郎、唐涤生三个粤剧传奇人物的惺惺相惜, “这种传统中国的才情关系, 便成为全剧的中心思想” (16) , 就显然不能阐释该剧深刻的涵义。
杜国威创作的这一走向在1985年的《人间有情》中就显露迹象, 其透过亲情、爱情、人情带出历史风云、世事沧桑, 与男欢女爱、姊妹情深这般“纯洁、温情的东西”明显不同。沿着这个走向创作的《遍地芳菲》《聊斋新志》《南海十三郎》等更是如此。在这些作品中, “写情”仍然是杜国威戏剧动人之所在。《南海十三郎》中薛觉先与十三郎之间、十三郎与唐涤生之间那种爱才惜才的深厚感情, 《聊斋新志》中人与人 (孙潜与学生白如云、程独秀) 、人与狐 (孙潜与聪敏好学的狐妖) 之间真挚的师生情、人与鬼 (程独秀与死去的情人落霞) 之间缠绵悱恻的痴恋情, 以及《遍地芳菲》中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参加者, 他们之间父女、母子、兄弟、夫妻、朋友、同志的浓浓情感等等, 都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但是, 这些剧作更注重的不是这些感情描写, 而是在这些感情描写中所渗透的社会现实和家国情怀。而当作者笔下人们之间的感情与社会现实、民族国家发生关联时, 其创作就拓展、超越和深化了他已往所擅长的“写情”内涵。
这些戏剧更多是写人们在大时代中、在混乱世道中的生存和挣扎。作者把剧中人物之间的感情关系放到历史风云、时代潮流中去描写, 就是要在其感情世界中融入更多的时代、社会、家国的情怀。《人间有情》中,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 因为人们的生活和命运被时代大潮所裹挟, 如天佑被日军拷打致残, 美娇倾慕的小伙子参加革命牺牲等, 其“写情”就更多一些沧桑、沉重。《聊斋新志》中, 孙潜受到朝廷奸臣迫害而躲避庐山讲学, 借讲解《阿房宫赋》, 论述仁政、暴刑以“借喻当今朝政得失”。孙潜的人生命运及其与学生和狐妖的感情, 同样因为卷入“家事国事天下事”之中而显得严峻、深沉。《遍地芳菲》中, 来自农民、行伍、知识分子、华侨、洪门兄弟、甚至风尘女子的这群人, 他们与民族同甘苦共患难, 为了国家而舍弃亲情和爱情, 揭竿而起、英勇奋斗, 他们的感情世界中激荡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南海十三郎》亦是如此, 着意在现代中国历史风云中, 讲述粤剧大编剧南海十三郎的生存境遇和情感历程。
在大时代中、在混乱世道中生存和挣扎的这些剧中人物, 其形象、性格的特质是什么?主要不是所谓“温厚的人性”或“人情美”、“人性美”, 而是对自我、人格、正义的执著和坚守。《南海十三郎》也是搬演粤剧艺人生活, 然而, 它不再像作者其他艺人题材剧作一样主要是写爱情或友情;此剧着力呈现了“两段君子之交的师徒情谊”及其所体现的“传统中国的才情关系”, 更浓墨重彩地表现了艺人的风骨和精神。十三郎是一个不问政治也不信教的粤剧天才, 他有自己的艺术信仰和追求, “敢爱敢恨至敢做敢写”, “做戏即系做人, 要导人向善”。20世纪30年代, 十三郎的编剧、打曲对粤剧艺术发展贡献重大。40年代初香港沦陷, 十三郎来往于香港和内地, 既难以适应内地的社会政治, 也不能适应香港粗俗、庸俗的演剧风气, 他偏执地、痛苦地挣扎于其中, 坚定地守护着一个艺术家的傲骨。十三郎不合流俗, 特立独行, 即便是后来落魄潦倒, 也不愿趋时从俗, 坚守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艺术良心, 最后倒毙街头, 走完悲剧性的一生。《遍地芳菲》以“草”作为中国人的象征, 带出起义失败却“遍地芳菲”的戏剧意象。作者说:“中国人是草!刚毅顽强, 勇敢不屈, 面对劣境依然茁长, 展露青葱。” (17) 《聊斋新志》是新编历史故事, 奸臣魏忠贤要将东林党赶尽杀绝, 孙潜在国家危难面前大义凛然, 其正义追求和刚正人格令人倾羡。
由此, 这些戏剧就在人与人感情关系的描写中、在人物命运的揭示中, 体现出作者对于现实与人性丑陋的批判。《聊斋新志》借古喻今, 忧国忧民:“当国家出现问题、万民怨愤的时候, 如果只用刑法暴政镇压而不主张仁义, 那人民便会更加愤怒, 反抗到底, 视死如归, 一发不可收拾。”而在国家危难和现实黑暗面前, 剧中既有像白如云、程独秀这样追求正义、卫护老师的门生, 有为感恩老师而与朝廷锦衣卫搏斗的狐妖, 也有一些门生自私懦弱, 自顾自逃离, 甚至还有像何鹏这样出卖老师、侮辱师妹的阴险卑鄙的小人。十三郎 (《南海十三郎》) 才华横溢, 命运多舛, 早年恃才傲物, 后来落魄潦倒, 但仍然我行我素, 他在抗战时期对于那种“叫个女人上台扭扭叫劳军”之类演剧风气的尖锐嘲讽, 他在战后对诸如“ (猩猩) 跟住个村女珠胎暗结, 生咗个猩猩仔十八年后劈山救母”之类粤剧的严厉批评等等, 都坚守着“敢爱敢恨至敢做敢写”, “做戏即系做人, 要导人向善”的艺术信仰, 在世态炎凉、现实丑陋中坚守着自己的追求和人格。《遍地芳菲》对于社会黑暗, 对于镇压起义的反动势力, 同样进行了尖锐批判。因此, 认为杜国威戏剧“不轻言批判, 也不提供反思, 历史的迷魅, 生存的困境, 统统消融在纯净化了的众生法相之中”的观点, 是不切合实际的。
正是因为在感情世界中渗透了社会现实和家国情怀, 杜国威这个走向的作品, 尤其是《南海十三郎》, 代表着其戏剧创作的主要成就。当然, 这些剧作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人与人感情关系的描写, 怎样与社会现实和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它是这些创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南海十三郎》能够将二者融合, 在十三郎感情世界、人生命运的刻画中折射历史和时代的面貌, 而又有优秀的审美创造。相对来说, 《聊斋新志》写师生情、人狐情、人鬼情, 它的聊斋式故事占据更多篇幅, 也较感人, 但孙潜的家国情怀没有很好地融入剧情结构和形象刻画, 就影响到作品的情感深度和审美创造。二是感情关系、社会现实和家国情怀, 怎样与戏剧的娱乐倾向相结合?这个问题随着杜国威创作走向成熟而日益突出。《聊斋新志》中的人狐情、人鬼情描写, 有些情节和场面与全剧内涵少有关联, 只是意念式地对照说明世上有些人还不如狐和鬼, 比如程独秀与落霞的人鬼恋情, 比如变人未成、样貌丑陋却痴情专一的狐妖翠娇求爱等, 只是增加了舞台的热闹和逗趣。这种情形即便是《南海十三郎》中也存在。少年十三郎的恶作剧和叛逆, 其父江太史形象、举止的卡通式搞笑, 尤其是剧作前半部关于江太史12个妻妾及其斗嘴打闹的琐碎描写, 体现出作者讲故事、写世俗风情的才华, 然而渲染过多, 又与十三郎的人生命运少有内在联系, 就影响了戏剧的艺术完整性。
三、媚俗:“边缘”感情的商业化娱乐化展现
杜国威写南海十三郎可能也有自己的内心困惑:是迎合大众随波逐流, 还是坚守自我和艺术良心?应该说在杜国威前期戏剧中, 有些艺术理念是可见其追求的。十三郎推崇的“敢爱敢恨至敢做敢写”的剧作家本色, 十三郎坚持的“做戏即系做人, 要导人向善”的艺术信仰, 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看作是杜国威对于自己创作的期许。所以在成长期和成熟期, 他能够写出《人间有情》《聊斋新志》《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南海十三郎》等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 具体地说, 是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演出获得巨大商业效应, 杜国威等人组建“春天制作”商业剧团大力推动香港话剧市场化之后, 有一股更大的商业和娱乐的力量在撕扯杜国威, 使他把戏剧看作是“娱乐性行业”, 而丢开此前戏剧“故事”中的“情怀”和“灵魂” (18) 。此后创作的《城寨风情》《Miss杜十娘》《播音情人》《梁祝》等剧大都走向庸俗和粗俗。舆论界开始批评杜国威“媚俗”。尽管作者极力为自己辩解, 学界也有剧评人极力为其“护短”, 然而媚俗却是实情。这也是杜国威的戏剧在成熟期之后不能有更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杜国威为自己辩解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是创作“最像自己的一个时期”, 他在剧中“放纵自己的感情”, “每一个剧本都不是为人家而写的” (19) 。杜国威成长期的剧作确实工整规矩, 然而到成熟期, 尤其是写《南海十三郎》, 其编剧笔法潇洒自如, 其情感表达敢爱敢恨, 那么, 为什么这个“最像自己”的作品获得好评, 而他后来那些“最像自己”的剧作却遭遇批评呢?有剧评人为杜国威“护短”, 说:“他的剧作, 不论人物、情节和语言, 均有本土特色, 更有广大的观众, 有人因之而指摘他是‘媚俗’, 我看这是不公平的。” (20) 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式诡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最像自己”, 是否“放纵自己的感情”, 更不在于是否有“本土特色”和“广大的观众”;媚俗, 是为了迎合流行和时俗, 而离开严肃的题旨, 去着重渲染那些热闹、滑稽乃至庸俗、粗俗的东西。
于是, 在原本就趋于通俗的基础上, 杜国威戏剧在感情描写、主题内涵和艺术表现等方面都出现新的转向。
作者仍然擅长“写情”, 但是感情描写在慢慢变味。此前杜国威戏剧中那种人情味, 那些爱情、友情、亲情和家国情大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妓女、舞女、同性恋、情人等“边缘”感情。《Miss杜十娘》《梁祝》属于后现代解构式“故事新编”, 然而作者不是以现代眼光去重新阐释杜十娘、梁山伯、祝英台这些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 而是或者用同性恋作为卖点, 把梁山伯改为同性恋者, 写他与祝英台的情感纠葛;或者借搬演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 而着意展现妓院生活, 渲染妓女的卖弄风骚以及妓女和嫖客的打情骂俏, 甚至有妓女“初夜权”拍卖和“破瓜”惨叫等场景的细致描写, 全剧最后是“众男女全情投入, 酒色逐捉”, “纸醉灯迷, 风情无限, 尽显浮光。歌台舞榭狂欢”。《播音情人》描摹几对男女情人虚情假意的感情游戏, 其英文名为“That's Entertainment”, 就是追求“开开心心、轻松惹笑”。即便是《城寨风情》, 作者原先是想透过不同时代几对青年男女的感情故事, 去表现香港九龙城寨的百年历史变迁。姑且不论在时代风雨飘摇中变迁的九龙城寨, 忽略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和九龙城寨声名远播的“黄赌毒”等描写, 而着力于几对青年男女的感情故事能否支撑得起剧情架构;即以这些不同时代青年男女的感情表现来说, 为了追求好看、搞笑、热闹, 作者写了4组“乖弱男”与“豪放女”的老套恋爱故事。这里着重呈现的不是他们的感情, 而是由他们的感情故事所带来的看点、娱乐、乃至脱衣舞场的色情表演等等, 与作者此前戏剧的感情描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 这些剧作情节庸俗胡闹, 主题内涵稀薄乃至扭曲。先看两个故事新编作品。《梁祝》写梁山伯喜欢“男性”的祝英台, 当祝英台恢复女儿身, 却让他气绝身亡。全剧看点就是梁山伯的同性恋, 然而剧终却又回到传统故事的“跳坟”和“化蝶”, 这就让戏剧主题模糊不清, 剧情结构也与前面渲染梁山伯是同性恋而不爱祝英台的设定失衡。剧中哪有什么“超越世俗、超越性别的‘至诚之爱’” (21) ?《Miss杜十娘》相反, 上半场是演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传统故事, 如果戏在这里结束, 她还是为寻求爱情而执迷的杜十娘;但作者改变了情节发展, 让杜十娘跳海未死又回到妓院, 以自己的经历和教训, 要众妓女“记住!做鸡, 都要做一只有前途有希望嘅鸡”, “要受得起考验, 坚持到底!”这就彻底解构了原著中的杜十娘形象, 让主人公成为一个放荡妖媚的妓女。剧中多次合唱所传达的内容极其庸俗、粗俗, 所张扬的人生观、价值观极其陈腐堕落:“任年华如逝水花片刻开放, 任行为随败絮放荡, 同君你齐放任多开心, 唯是多金兼多银至动人”。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讽喻丑恶、薄情的现实外, 还在向人们昭示那种自然、豁达, 闪烁着佛光禅理的‘爱情观’”, 也没有什么“包含了许多人生与生活真相的感悟, 而又因为反讽的存在而闪烁出特殊的光芒” (22) , 这里只是一味展现丑恶而少批判甚至无批判。两出搬演现实的作品, 《城寨风情》开场写得较好, 既有历史也有爱情, 后来情节发展就主要变成爱情, 然而那些着重呈现看点、娱乐、乃至脱衣舞场色情表演的所谓爱情故事, 难以承载反映九龙城寨百年变迁的历史沧桑;着意开心、娱乐的《播音情人》, 全剧虚情假意、歌舞风骚, 少有人生、人性和人情。有剧评人指出:“剧场是人的艺术, 最终能否打动人 (观众) , 要看舞台上的人有没有血肉。演出风格可以写实写意超现实, 故事可连贯可撕裂, 时空可在眼前或天边, 但如果没有真实的人性人心人情在后面, 还是不能叫人笑叫人哭。” (23)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wenxuelunwen/3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