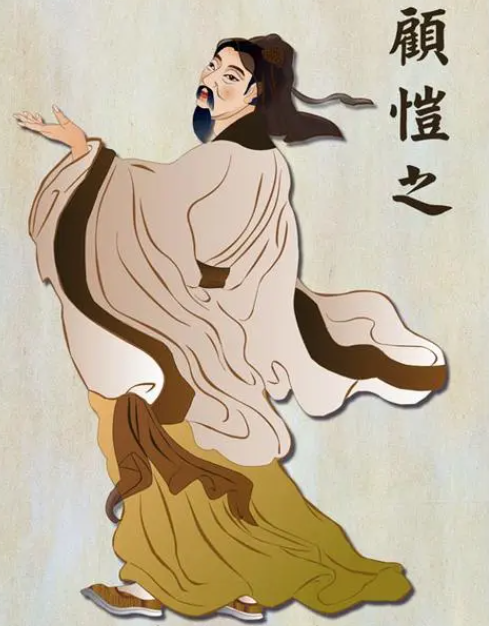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中国第一幅以表现人神情感为主题的画作,是依据三国时期曹植的诗赋《洛神赋》进行的改编创作,文绝与画绝的跨时代创作,称得上是文学绘画相结合的巅峰之作,在其中能感受到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文字与绘画的碰撞没有界定,没有固化,千人千意、万人万解。顾恺之《洛神赋图》对“形”的描绘、“神”的刻画、“情”的表现在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也有所体现,对后世及当代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影响。
一、《洛神赋图》创作的社会时代背景
《洛神赋图》的创作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尖锐的阶级矛盾、连绵不断的战争、四分五裂的政权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而魏晋玄学的兴起又使一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清谈家应时而生,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突破了秦汉时期“助教化,成人伦”的艺术教育作用,转而注重表达艺术家内心的情感,作品上升到更高的审美层次,《洛神赋图》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二、《洛神赋图》的创作文本《洛神赋》
(一)《洛神赋》创作背景及其内容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后期创作的辞赋。张新亚认为:“《洛神赋》是作者理想抱负的形象化身,作品表现的是作者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追求失败、理想破灭后悲愤凄苦的心情。对当时压抑人才、摧残理想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含蓄而又尖锐的控诉和谴责,表现出一定的抗争精神,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和魏晋时代远离现实、“崇道抑儒”的士人心理活动是一致的。从作品艺术角度而言,魏晋文人学士隐逸的处事态度形成的对质朴画面和画外意境与传神的追求,引出他们对书画审美的独特视角,即对淡泊出世美的追求。
(二)《洛神赋》的文学价值及其对《洛神赋图》的影响
《洛神赋》不仅是曹植辞赋中的杰出作品,同时也是魏晋时期抒情小赋的名作。人神之间的真挚爱情以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出来,《洛神赋》对后世艺术创作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书法家王献之与画家顾恺之均以此为题来进行创作,可见《洛神赋》的艺术魅力是历久弥新的。
同时,《洛神赋》为《洛神赋图》的成功创作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指导作用。第一,想象丰富。《洛神赋》整个故事发展历程井然有序,充满着想象,但这种联想并不奇特荒谬,反倒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第二,文采华美,讲究对仗、排偶、韵律。通篇下来一气呵成,具有连续性,为画作的创造提供了完整的故事发展背景。第三,刻画细致,与修辞手法的恰当同用使绘画摒弃了传统的绘画技巧,创造了新的画面表现形式。正是以上的这些特征加以艺术家自身的创造能力造就了《洛神赋图》这一传世佳作,并为以后艺术手法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洛神赋图》作品分析
《洛神赋图》原卷为设色绢本,东晋画家顾恺之以曹植诗赋《洛神赋》的故事发展为线索表现画面内容,人物故事情节分段表现,画面中自然山川多作为背景,带动画面的连续性,同时也衬托出人物性格。全卷分为五段,描绘洛神与曹植的纯真爱情,讲述他们如何相遇又分离,从邂逅、定情、殊途、分离、怅归方面将二人的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文学与绘画作为艺术的两大形式,一方面以语言的技巧性带给人们无限的想象,另一方面以绘画的直观性带给人们视觉的享受。
(一)《洛神赋图》中的线条艺术
在视觉表现上,顾恺之运用线条增添空间层次与关系。画面中,作为主角的洛神和曹植神态与衣纹变化丰富,线条柔韧温和,圆润平滑,洛神之美凸显其中,似“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而作为背景的山水神兽,则表现得刚健有力、粗犷硬朗,塑造出山峰与野怪的锋芒毕露、狰狞凶狠,这种具有强烈对比的线条体现出画面的力量感、节奏感和均衡感。线条艺术的虚实相生、刚柔并济,赋予《洛神赋图》独特的审美感受。绘者精湛的运笔技巧、主观表现,造就了“春蚕吐丝”般的高古游丝描。
(二)《洛神赋图》中的构图布局
《洛神赋图》在构图上运用了卷轴的表现形式,画面连续表现了完整的故事情节。《洛神赋图》将整个故事放在一个卷轴之中,用山石、树木、河水等景物作为背景,将画面分割成不同的情节,故事人物的出现随着诗赋发展顺序推进,称得上是一部魏晋时期的微电影。故事开篇以曹植为主体的一行人漫步阳林眺望洛川,忽见洛神。洛神感觉到了曹植的爱慕,互相许以信物,在天地间飘摇舒袖。待到分别时刻,风神停风,水神息波,女娲唱起了嘹亮的歌,洛神乘着六龙云车,从此人神殊途、天各一方。顾恺之在安排画面构图时,错落有致、张弛有度,山水、人物、奇禽异兽等客观物体的安排在有限的画面空间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和氛围感。
(三)《洛神赋图》中的设色安排
《洛神赋图》的画面多以勾勒填色为主。从人物画面来看,服饰表现技法多是平涂,色彩的不同体现人物的身份地位差异。描画洛神与曹植这两位主要人物时多用红、黄等鲜亮明丽色凸显;作为次要人物的侍从则用素色表现,使得画面人物主次分明。画面整体的空间感、层次感十分突出,黑白灰关系处理恰当,不仅使画面丰富,又增添了画面的美感,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代表了当时绘画设色的最高水平。
四、顾恺之《洛神赋图》人物画的审美价值
除画家身份外,顾恺之还是影响深远的早期绘画理论家,有三篇画论传世。在这些画论中他提出“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画论名句,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为后世中国传统绘画创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一)《洛神赋图》之“迁想妙得”
《魏晋胜流在画赞》中,顾恺之写道:“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提出“迁想妙得”的观点,将艺术家自己的构思情感放在最主要的地位,这是画家把握生活的一种艺术方式,是主体情感牵制客观事物的表现。画家在创作时需要把自己代入画中的人物和情节,想他们所想,感他们所感。类比于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艺术体验活动,要先有想,才能有得,并创造出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
在《洛神赋》中,曹植运用了大量篇幅形容洛神的美貌,在文字的传达下,顾恺之发挥自己的想象,以画笔塑造画面中洛神的形象。曹植说“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顾恺之便用极其柔软弯曲的线条描摹洛神的服饰,衣带缠绕包裹着曼妙的舞姿,没有任何一条线是笔直的,翩翩飞舞,摇摆蛟龙,轻盈而敏捷。顾恺之提出的这个想法不仅为他创作《洛神赋图》锦上添花,同时也为观者提供了人在画中游的绝佳体验。
(二)《洛神赋图》之“传神论”
“传神写照”的提出称得上是顾恺之在艺术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在《论画》中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他认为,一幅画无论是什么题材内容都需要曲折的反映画家本人的情感与想法,以形表现神,神是一件作品最中心的要点。绘画中,人物外形的美丑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描绘出人的性格、气质与精神,尤其是对眼睛的描绘。据记载,顾恺之经常在作画后不画眼睛,问其原因,他便回道:“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画面人物的神气所在。在《洛神赋图》中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洛神与曹植的“眼神戏”。画面中,作为次要人物的随从们,眼神都是程式化的呆滞木然,衬托了曹植见到洛神的欢喜与惊讶。仔细观察有一画面,随从们的眼神均是向下倾斜,目中无神,而曹植的眼神直视前方洛神方向,显示爱慕与期盼。洛神的神情也随着场景的交错变换表现不同的情感。顾恺之用眼神来诉说洛神、曹植的人神殊途,那种真切的情感跨越时空,让今天的我们也感同身受。
五、《洛神赋图》中体现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
中国传统艺术向来要求“以形写神”“以形传神”,这与顾恺之传神写照的绘画理念不谋而合。在《洛神赋图》中,顾恺之把握了绘画艺术的本质,即绘画是对人精神世界的体现,是对人内在美的体现。洛神与曹植之间的情感交流依靠眼睛和神情的传递,情感表现得极其丰富。《洛神赋图》中不求形似但极具装饰意味的山水形象,不仅没有失去自身特征,反而强化了画面中缥缈悠然的深邃意境。《洛神赋图》“画尽意在”的审美境界不断衍生,标志着中国早期的绘画逐渐摆脱了从属政教的地位,走向了审美自觉的境地。
中国传统艺术一贯强调文学艺术之美在于情与景、心与物、人与自然的交融合一,顾恺之将自身主观的生命情调融合于客观的自然景象和人物活动之中,创作了《洛神赋图》,并在尊重客观事物规律的基础上,融情于理,将情感与物象相结合,表达主观感受,以及山水人物的和谐共生。
六、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原本是“重教化,助人伦”的政治教化工具,但在顾恺之出现之后,艺术创作更加纯粹。他将绘画技法上升到了学术理论层面,提出“迁想妙得”“传神写照”。其创作的《洛神赋图》成为流传千古的爱情长卷,《洛神赋图》独特的艺术特点和艺术表现使其成为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洛神与曹植的一次次眼神交流中,顾恺之把人对美的追求发挥到极致。他将人生感悟和情感注入画作中,融合中国传统艺术的思想精髓,赋予中国绘画新的审美理念,引起观者的情感共鸣。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785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