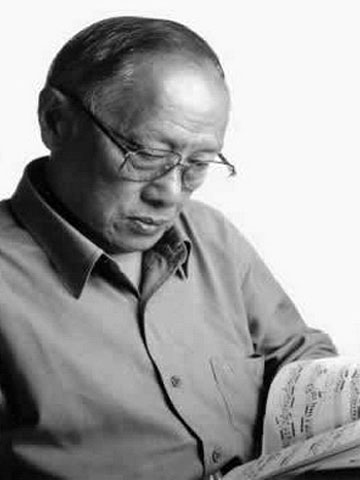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要:杜鸣心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他用中西音乐理论技巧相融合的手法来书写他自己的“音乐风格”,并且他的创作充分体现着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刻见解。本文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角度入手,结合杜鸣心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中的娘子军音乐形象的塑造以及中国音乐语言的充分运用,论述了杜鸣心音乐创作中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是文化学中的重要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由德国扬·阿斯曼提出,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构成了文化记忆的理论来源,阿斯曼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上将记忆分为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扬·阿斯曼从文化学的视角探讨记忆与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联,他将记忆划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个体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这三个维度对应在记忆理论中可以被理解为个体记忆、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的提出将记忆从个体范畴直接延伸到了文化范畴。“文化记忆包括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必不可少且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画、仪式等内容,其核心是所有成员分享的有关政治身份的传统,相关的人群借助它确定和确立自我形象,基于它,该集体的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属性和与众不同之处。”文化记忆强调的是社会和文化、意识与文化以及心理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记忆通过语言、文学、教育等途径而存在,进而文化记忆成为社会群体的共同认知,并最终融入民族性,文化记忆不同于社会记忆,因为文化记忆更加体现着人类过往在历史长河中的文明记忆。
“文化记忆”这一概念提出后,探讨文化记忆成为研究记忆与文化问题的重要视角和方法。音乐文本作为文化记忆重要的抒情媒介,同样存在着研究的必然性,据扬·阿德曼指出的文化记忆“受到主观经历、客观和科学的历史知识以及文化回忆三个因素的制约”以及文化记忆所要强调的三种互动关系可以认为,音乐创作中的文化记忆受到社会因素、情感因素和知识因素的影响。在当今全球化的视野下,强调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是当代音乐创作的“风向标”,杜鸣心是新时代中国音乐历史上非常重要以及不可或缺的作曲家之一,其创作中所体现的中国音乐风格正是他对于中国音乐“文化记忆”的体现。
一、记忆的纹理——红色娘子军的形象塑造
记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始终贯穿哈布瓦赫全部研究的核心论点,他提出个人的回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尽管拥有记忆的是人的个体,但这种记忆是深受集体影响而形成的。个体存在的只有感觉而不是回忆,回忆或者说记忆的根源是存在于人们所参与的集体当中的,所以记忆乃至文化记忆都脱离不开社会的影响。文化记忆所关注的是具有某些神圣因素的过去的一些焦点,文化记忆的社会维度体现在一个群体通过回忆过去,将起着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进行现时化而产生的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红色娘子军作为发生在绝对的过去的历史事件,以及已经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群体对于身份的认同。随着红色娘子军的形象在幸存者的回忆录以及电影与其他艺术形式作品中得到编排和塑造,有关这个社会以及时代的群体共同记忆便在图案和空间中得到了铸造。红色娘子军中大多数都是女性,并且来自农村,她们中有些来自农民赤卫队,作战勇敢,曾在琼崖苏区成功担任掩护任务。杜鸣心通过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重塑了一群英勇无畏的女战士形象。从内容上看,《红色娘子军》强调的是女性的解放意识,歌颂了党和国家。自钢琴组曲的改编版本问世以后,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它的时代意义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更迭而涣散。杜鸣心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改编自舞剧,作品中杜鸣心并没有将舞剧中冗长的主题运用在钢琴组曲的每个乐章中,而是在音乐主题的选用上和音乐形象的整体塑造上以及音乐的编配方面对舞剧《红色娘子军》进行参照。
(一)娘子军连歌原型的基本形式
杜鸣心巧妙地将“娘子军连歌主题”运用到了整部组曲中。娘子军连歌作为文化记忆中的媒介,具备着规范性与定型性的推动力,也就是具备着三个方面的作用:存储、调取、传达。这是对娘子军形象的存储、对群体记忆的调取,以及对娘子军连歌新形式和娘子军精神的传达,娘子军精神全面地融入了杜鸣心的创作中,维护与完善了听众对于红色娘子军精神的记忆。在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中,“娘子军连歌主题”在七个乐章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了五次,分别运用在第一乐章《娘子军操练》的引子和结尾、第三乐章《清华参军》的结尾处、第六乐章《常青就义》第二段、第七乐章《奋勇向前》结尾处。“娘子军连歌”主题贯穿在整部组曲中,使整个作品形成了统一的音乐主题与形象。“娘子军连歌主题”原型是一个简约型的主题发展类型,在应用这一主题时,杜鸣心对该主题的发展类型进行了重复,或将其改变成了完整型以及在完整型基础上进行变形的形式。
主题核心呈示中第一动机的“E、A”两音预示着娘子军形象的第一次出现,两音在音程关系上形成上四度下五度的关系,这两个音的出现也确定了整个娘子军连歌主题的整体基调,主题核心呈示中的第二个动机呈现音阶式的下行,最高音与最低音之间同样也是四五度的音程关系。在主题核心的展开中,杜鸣心将“E、A、B”三音进行展开,对娘子军形象进行了第一次调取与强化,最后以“E”音为中心进行音阶式的下行,结束了整个娘子军连歌的主题原型的叙述。整个娘子军连歌的原型叙述体现着杜鸣心的创作对于娘子军这一文化记忆形象的存储作用,而杜鸣心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展开将其作用于群体记忆,起到了调取群体记忆的作用。
(二)娘子军连歌主题的变形
“娘子军连歌”主题出现在《娘子军操练》的引子和结尾中时,是对娘子军操练时刻苦精神的描绘,而表达训练井然有序,同样也是对文化记忆的调取与传达。对文化记忆的调取作用主要体现在音乐主题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其还是简约型的叙述方式,只是延长了一倍的时值,加入了附点节奏,使整个主题听起来更具有进行曲风格,与标题《娘子军操练》形成呼应,传达了娘子军的革命精神。在《清华参军》结尾处时,杜鸣心将娘子军连歌主题发展为完整型的方式,完整地呈现了主题核心发展的四个阶段——呈示、巩固、展开与结束,这一段充分展现了文化记忆的调取和传达,较之前的主题发展来看,其加入了上五度模进,并且这一模进没有脱离核心音“E、A”两音,其中的四五度音程关系充分体现了杜鸣心旋律写作的巧思以及其创作的民族特征。在主旋律音不变的基础之上,其对织体与节奏进行了一些变形,在旋律的节奏中加了附点,琶音式的织体较之前柔美了许多,一改原来的进行曲风格。
在第六乐章《常青就义》中,舞剧的剧情主要描写的是男主人公洪常青坚定不移的革命气节,而“娘子军连歌主题”的运用则是表现常青对娘子军团的回忆,所以将“娘子军连歌主题”运用在中间的第二段中,起到了文化记忆的存储、调取与传达三个方面的作用。如果按照主题呈示、巩固、展开、结束四个发展阶段来看这一主题,可以发现该主题被重复了三遍以上,这三遍重复是对娘子军形象的再一次存储。在第二遍时,杜鸣心并没有将主题动机完全呈示和展开,而是调取了一小节,围绕主音“#F”展开。在第三遍时,再对主题向上四度模进进行重复,形成主题的巩固,之后并没有直接进入展开或结束阶段,而是加入了呈示乐思的低八度进行,并且同样以“#F”音为主音进行展开,展开和结束时都使用了模进的发展手法,对着这一主题进行了巩固。这样反复地呈示与展开一次次再现了娘子军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充分体现着对这一精神的存储与调取作用,虽然这一段不是直接对四个过程的陈述,但是从主题发展来看,“娘子军连歌主题”发展的三个阶段,都可以在下方重复的地方找到原型,并且整段的旋律都在“#F、B”两音的框架内,所以,后面第二遍第三遍的呈示都是对“娘子军连歌主题”的巩固,这一段同属于完整型的主题核心发展类型,接踵而至的模进片段与之形成了娘子军形象的联觉,让听众能更加感同身受,产生共鸣,这充分体现了杜鸣心音乐主题发展的智慧,起到了文化记忆的传达作用。
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奋勇向前》的结尾处,这是带有总结性的一个乐章,在作品的最后,杜鸣心引入娘子军连歌的主题来做最后的收束。在最后一次叙述中,作曲家再次对这一形象进行了存储以及传达,这一段的“娘子军连歌主题”发展方式与第六乐章《常青就义》中相同,但是加入了音阶、琶音式的过程中的连接,使主题更加跌宕起伏,总结了娘子军奋勇抗战的一路艰辛,通过音乐主题的变形发展,展现了作曲家对于技巧以及音乐主题的掌控。
在这一红色娘子军连歌的改编中,这些不同的阶段构成了真正的记忆行为,过去的文化制品在当下被杜鸣心激活,并通过记忆工作本身让记忆变得更加生动了起来。《红色娘子军》是一部红色经典作品,在提到红色音乐作品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时杜鸣心说道:“战火硝烟虽然远去,但那段历史永远不能被忘记。踏上新征程,我们要用好红色经典音乐这个宝贵的红色资源,让红色经典唱响时代主旋律”。杜鸣心改编的《红色娘子军》,运用钢琴这一乐器将篇幅短小的乐章汇聚成了一部钢琴组曲,弘扬并传播了红色精神,极具时代价值与意义。
二、从“仪式”到文本——音乐语言的变迁
“文化记忆在社会中的实现,是通过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经典文献)、意象系统(图像)或仪式系统(节日和礼仪),确立和巩固集体内每位个体成员的身份意识。”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为了维持世界运转,都必须在仪式和精神层面上付出努力,而这些努力最初不是寄托在书籍上,而是体现在仪式中。为了仪式的正确举行,人们必须熟知相关知识,这样的仪式称为“记忆的仪式”。这种仪式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文化依赖于记忆,所以这种“仪式”就是对其所指的文化的记忆,是文化的本源。但到了文字的发明开始,这些“仪式”逐渐过渡到了文本的阐述,文本作为记忆的媒介,同时作用于文化之上,而音乐也是从那时开始有了记录。在促成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重复、解释、回忆成为文化传承的手段,文化在这些过程中保持着其自身的持续性,也就是群体的身份认同。虽然在记忆载体中存在变迁,但文化却一直保持着自身的持续性。
作曲家杜鸣心曾多次到海南当地进行采风,为了写出带有浓厚黎族民歌音调的作品,他经常深入黎族人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没有乐谱记录的时代,我国的民歌通常是以口头形式来进行传播的,但文本以及记谱法的出现,实现了民歌记忆从“仪式”到“文本”的改变。在倡导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专家学者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资源进行了开发与保护,作曲家也将民歌的因素运用在了新时代的音乐作品创作中,使少数民族音乐走向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文化记忆也依靠这种可持续性得以长存。在杜鸣心的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中,《军民一家亲》的主题“万泉河水”是经过作曲家搜集海南民间音乐素材创作而成的,该作品是以海南黎族民歌《五指山歌》作为旋律基础来进行加工、改编和发展的,这首民歌极具地域性特点。
《军民一家亲》这首作品的调式为徵调式,是黎族音乐中大量存在且为海南黎族音乐特点的调式。整首作品运用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五度音程来写作,五指山歌采用F徵调式,军民一家亲采用E徵调式,从五指山歌到军民一家亲共经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始的两音动机,都呈现上五度下四度的音程特征,且都停留在了徵调式的主音。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大径相同,只不过最后的徵音提高八度。第三阶段杜鸣心在创作时运用了一处巧思,原曲《五指山歌》作为一首海南民族民歌,节拍上是我国民歌所独有的特点,即节拍随感情发生变化,但杜鸣心在创作中采用相同的拍子进行创作,在《五指山歌》向《军民一家亲》的过渡过程中,2/4拍中最后一音与3/4拍开始的音进行了置换,节拍时值缩短到2/4拍构成新的主题旋律,最后停留徵音,杜鸣心在此基础上引申出两小节停留在与《五指山歌》第三阶段中心音相同的商音,与《五指山歌》相联系。第四阶段原曲《五指山歌》围绕羽音进行展开,而《军民一家亲》同样围绕羽音展开,这一阶段与中国传统音乐中起承转合中的“转”相契合,从徵调式转到羽调式,《五指山歌》对第四阶段的旋律对调式进行了巩固,回到了徵调式,《军民一家亲》同样也是以徵调式结束,运用上下起伏的旋律渲染军民鱼水情。
“在阿斯曼看来,从鲜活记忆到档案再到正典(中译本作“卡农”),是重新框架化和重新语境化的过程”,而记忆的持续依赖于社会关系和框架的持续,框架强调的是选择的重要性,杜鸣心选择海南黎族民歌这一民歌框架,在其框架基础之上进行重构,能够使得与这一音乐文本相对应的记忆得以延续。“重新语境化,就是某种社会实践在另一个社会语境中发生的变迁,强调的是互文性——新语境影响社会实践的内容和意义”。杜鸣心将这一作品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运用在他的钢琴组曲中,这一曲调在时代的变迁下,得到了黎族人民的传唱,进而成了黎族民歌的经典。杜鸣心一直以来都热衷于写作人民群众喜爱的、能听懂的音乐,这首作品不仅在音乐文本上言简意赅,也表达了一种军民鱼水之情,这种感情同样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爱戴和信赖,也揭示了军民关系之间的淳朴本质。
三、中国语境下文化记忆中的文化认同
阿斯曼的研究以埃及、以色列和希腊为例对文化记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作为历史悠久的国度,中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断裂的经历,是唯一文明持续至今的国家,这使得它的文化记忆研究具有极为难得的样本意义。中国语境下的文化记忆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均具有不可多得的延续性、丰富性与多样性”。中国音乐的发展从上古时期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到今天的新时代,无不体现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延续性的特点。我国每个民族的音乐都具有不同的艺术特色与特点,这体现着中国音乐乃至中国文化的丰富与多样,而这样的文化记忆都与集体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息息相关。
认同与意识相关,这关乎个人与集体两个方面。自我的形成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这一论述强调整体对于部分的优先权,而个体又是集体的组成部分和载体,这强调了部分对于整体的优先权。而在文化记忆的形成过程中,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杨·阿斯曼将个人认同又区分为“个体的”认同和“个人的”认同,“个体的认同”关乎个人的“主要参数”,与自我存在等意识相关,而“个人的”认同则是一定的社会结构分配给个人的角色、性格等,也就是社会对个体的
认可以及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集体认同则是一种形象的构建,指社会中的成员与这个形象进行的身份认同,集体认同与个体认同的区别在于集体认同没有一个明显可见的身体作为基础载体。
杜鸣心的创作体现着文化认同的特征。在这部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中,可以直观感受到作曲家杜鸣心对于这部组曲所倾入的情感与真诚,还能感受到他对于中国音乐文化的发扬与继承。杜鸣心的“个体的”认同来自他成长的家庭,杜鸣心深受中国传统音乐影响,创作的作品都富有中国音乐风格。后来,杜鸣心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入选到苏联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进行学习,在此期间,他在苏联学习了许多欧洲传统的音乐作曲技法,这些也存入了他的“个人的”认同之中。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是杜鸣心钢琴表现力充分发挥的结果,更是作曲家对于民族音乐的审美感受的充分流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现实性和浪漫性等特点,杜鸣心先生在将其改编成钢琴组曲时,继承了舞剧的中心思想,也继承了舞剧音乐的创作特点,这种文化记忆深深刻在了杜鸣心的骨子里。
四、结语
杜鸣心的音乐创作以乐器作品为主,其第一首钢琴作品《练习曲》写于1955年,至今已经有将近70年的历史,虽然杜鸣心先生已到耄耋之年,但他从未停止过艺术创作,他的作品经久不衰,带给了后人愉悦的审美感受。他说:“《延座讲话》告诉我们: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的艺术不能只表达个人的情感,不能故作清高、过于功利,艺术要与人民沟通。我们创作每一首乐曲,都要力争能为人民所喜爱,从我们的作品中得到美的享受。”他的音乐充分体现着他对艺术的极高追求,他的作品强化了观众对于中国音乐的文化认同感,这是研究文化记忆以及将杜鸣心与文化记忆直接相连的原因所在。
在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中充斥着杜鸣心对于中国音乐“文化记忆”的思考,从红色娘子军形象的塑造,到红色娘子军连歌在整部组曲中基于表达情景的变型,再到组曲中的经典段落“万泉河水”对海南民族山歌《五指山歌》的改编运用,都体现着他在“技术层面呈现出基于中国文化形态和精神的技术特征,进而充分彰显了中国音乐的特性,体现中国智慧,显露中国文化,凸显中国文化身份”。正如杜鸣心自己所说,他的作品就是在朴实无华中流露出其个人的真实情感,这也正是杜鸣心先生的音乐作品能够打动观众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J].外国语文,2017(02):36-40.
[2]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16(06):18-26.[3]陶成涛.文化乡愁:文化记忆的情感维度[J].中州学刊,2015(07):157-162.
[4]郭新,郎雅慧.器乐曲旋律写作溯源及独特风格的技术构成——杜鸣心近期课程教学中个人阐述撷英[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04):24-46.
[5]曹雅丽.杜鸣心:让红色经典唱响时代主旋律[J].中国纪检监察,2022(13):61-63.[6]张露露.“文化记忆”视域中的古代仪式与文本——柯马丁的《诗经》研究的方法与争议[J].浙江学刊,2022(06):173-181.
[7][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J].,金寿福,黄晓晨译,史学理论研究,2015(03):49.
[8]赖国栋.在历史和现实中穿行——读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J].史学理论研究,2016(01):152-156.[9]连连.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J].江海学刊,2012(04):177-181+239.
[10]傅显舟.杜鸣心其人其作及研究[J].人民音乐,2008(07):18-23.
[11]郑艳.现代作曲技术中的中国文化标识——音响设计、节奏数控、结构布局的探索与创造[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20(02):6-19.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585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