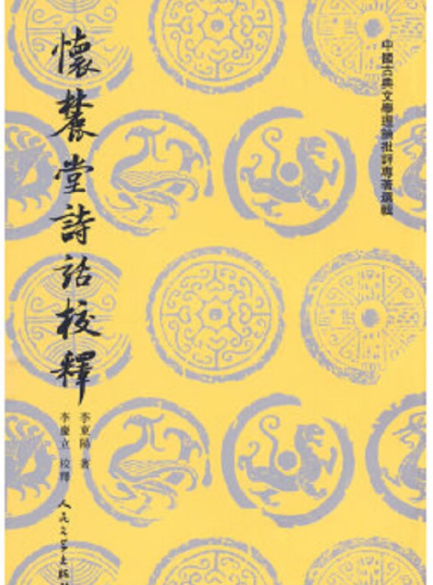摘要:《怀麓堂诗话》作为中国古代具有复古倾向的文艺批评论著,以盛唐为正宗,学习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比兴诗论,反对“比之浅薄”“兴之萎靡”的错误思想倾向,认为“比兴之间,先取兴者”,提倡运用“以兴导比,以质刻物”的写作方法,以抒发天真兴致为最终目的。同时也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一定程度实现了后代对前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比兴界定的发展,在比上“不可太切”对“切类”的超越,在兴上对不同关照对象的超越。文章将以《文心雕龙》为参照,探讨李东阳对前代在比兴诗学方面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怀麓堂诗话,李东阳,比兴关系,复古诗学
一、李东阳的比兴诗论
在比兴关系上,李东阳认为:“古诗辞贵简远,贵质而不俚。”[1]他将兴象至于诗歌创作的第一位,而兴的生成,则应在远处、淡处找寻。此处并非着意排斥日常琐物和浓烈情词,而是他认为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在《怀麓堂诗话》中,他举了一系列诗人诗句为这一观点作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柳宗元的《渔翁》一诗,全诗如下:“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议论的焦点集中于诗的结尾二句:“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苏东坡以为“虽不必亦可”,即东坡以为前四句已是情词俱佳,结尾二句大可不必。而李东阳则认为,“若如东坡所言,削去结尾二句,则与晚唐何异。”[1]
李东阳和苏东坡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诗论冲突,很能代表向复古派过渡的明代诗坛与宋诗、晚唐诗比兴理念的冲突,而这一矛盾中心,就落在李东阳、晚唐诗人和宋代苏东坡一派诗人对于比兴手法的不同见解上。
想要厘清其中根源,我们可以从李东阳口中的反面例证——晚唐入手。复古派中另一位诗人胡应麟在《诗薮》中对唐人李频的《乐游原春望》表达惋惜:“中四句居然盛唐,而起结晚唐面目尽露,余甚惜之。”原诗如下:“五陵佳气晚氛氲,霸业雄图势自分。秦地山河连楚塞,汉家宫殿入青云。未央树色春中见,长乐钟声月下闻。无那杨华起愁思,满天飘落雪纷纷。”我们可以看到,李东阳和胡应麟对上述两诗的称道之处都在于其面目似盛唐,而惋惜之处都在于其晚唐风貌的流露。综合两诗特点,笔者以为,李东阳等明人对于晚唐诗风的不满主要集中于两点:1.意向抓取的浅近繁缛,即比之浅薄。2.情思气象的幽微衰颓,即兴之萎靡。
(一)比之浅薄
从第一点意象抓取来看,杨慎对晚唐诗的评价很具代表性:“大历而下,如许浑辈,皆空吟不学……此等空空,知万卷为何物哉!然犹是形月露而状风云,咏山水而写花木。”简而言之,复古派认为晚唐的另一特点是对外物的过度重视和描写,只一心地形月露而状风云,咏山水而写花木,流连沉醉于浅近俗套的雪月风花,却空吟不学,缺少求诸内的情感和气象。
在柳宗元的《渔翁》中,前四句分列了“渔翁”“西岩”“清湘”“楚竹”“烟”“日”“山水”等一系列具有时间连贯性的秀丽物像,将诗的主体渔翁至于浑然一体的天光水色之中,尤其是“欸乃一声”和“山水绿”更使耳中所闻之声与目中所见之景发生了奇特的依存关系,刻画出极具时间感的空间画面效果,可谓极尽了比拟造物之功力。但这颇具渲染力的描绘画面笔法,在李东阳看来,不及尾联的天际悠悠,云荡渺渺。
李频的《乐游原春望》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尾联在景物的抓取上,选择的是表达愁思的代表性物像——杨华似雪,可谓见其物而知其情,在秦地汉宫、未央树色、长乐钟声等意象之后,骤然流于落花飘雪,未免陷于窠臼。
需要注意的是,李东阳等人对于晚唐诗的批评并非就是在否定比拟意象之于诗歌的重要作用,相反,他们对比兴给予同等的重视,不可分割,认为:“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指责模仿宋诗者“黜意象,雕精神,废风格”,一味说理而不描绘物像,便会沦于宋诗的道学疏卤。他们反对的,是囿于雕琢堆砌比的外物,而粗浅于兴发的表达,不能融情于景、情景交融。
这一点在李东阳对两句诗的不同态度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对“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一句,李东阳认为:“论者以为至妙。予不能辩,但恨其意象太著耳。”宋人石延年的这一句,意在用花鸟树的生动意象,表现自然界的和谐畅美,素为论者所称道,但李东阳却不认同,因为“其意象太著”,即意象太过明白显现,尽露则无味了。李东阳这里仅以一“著”字言其欠佳处,若要具体言说,还需从其他论家认为其之所以至秒处入手。近人陈衍的《宋诗精华录》中说,这两句好在“能于‘绿杨宜作两家春’外辟出境界”。“绿杨宜作两家春”一句,是白居易移情于物,将友情寄于绿杨之上,想象着若与友人为邻,树将以浓荫覆蔽两家,春色满园。陈衍认为,石延年此句在移情于物之上另辟蹊径,写出物物情意交融,以有情之眼观无情之物,遂觉万物皆有深情。笔者以为,李东阳认为此句欠佳处与陈衍认为此句至秒处,恰都在物物之情上。陈衍赞其能将人情移于物意,以情眼观之,禽鸟亦软语缠绵,花树也交缠生香。可李东阳却认为此句太过急切显露地将乐意、对语、生香、交花等情语赋予景语,不待读者从“比”中体悟“兴”,而是将其呈在表面,直露而流于浅俗。这正是复古派对于宋诗的鄙弃之处。而同样是意象表现上,李东阳则倾心于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二句,此二句不著一字情语,只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几个意象进行列锦铺陈,似乎无意于营造兴寄,却将早春的沉寂凄清,羁旅的愁思孤冷,自然而然地浸透入全句之中,使得诗歌的意境达到了恰如其分的朦胧感和陌生感。因此李东阳赞其“意象具足”。在“意象太著”和“意象具足”之间,我们能够很明晰地辨识李东阳乃至复古派为何扬唐抑宋,以及他们对于意象刻画(即“比”)的追求。
(二)兴之萎靡
从第二点情思气象来看,柳宗元的《渔翁》一诗,李东阳认为若无尾联,则与晚唐无异。这一论调固然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也有其缘由。与“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两句中,分别取意于“回看长江天际流”“云无心以出岫”的开阔飘逸相比,前几联囿于江岸渔人从夜晚到破晓的活动,取境于山水间的闲适秀丽,未免显得境界小了。因此不同于世人多称道颈联的精妙,李东阳则褒扬尾联之气象阔大,意境悠远,有盛唐之气,甚至不惜将前几联打入晚唐之流。从这一特殊作品引发的由宋到明的文学探讨中,我们得以一窥宋、明诗坛在文论上的剧变。
上述的问题在对李频的《乐游原春望》一诗的讨论上表现得更为显著,李频此人,虽处晚唐,却时有俊句,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言其“诗虽晚唐,却多壮句”。但他终究无法摆脱时代大环境的影响。此诗中间四句素为人所称道,以对长安宏阔气象的描写,抒发慷慨豪迈之情,而胡应麟所谓“起结晚唐面目尽露”,是与中间的清旷壮阔之气相比,收尾两句不可避免地落入对灰暗政治前途和衰颓国运的哀叹悲愁之中。面对眼前富丽、巍峨的秦地汉宫,不可避免地会使人忆起过去的盛世恢宏,可感慨之后,又无法抑制地滑入感伤主义的时代情结中,所谓末世哀音,不外是那骤起飞扬的杨华,漫空飘洒如暮雪纷纷。
综上,以晚唐为切入点,再回到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的论调,我们就能更为明晰地辨识他的比兴观点。首先,诗贵意,在比与兴之间,他认为兴寄是整首诗的执牛耳者,所谓“贵情思而轻事实”。物像的比喻刻画,不胜其烦地反复描写,纵能得万物之精髓,在李东阳看来亦不如寄托于简远朴淡的高远情致。进而论述兴寄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宁疏笔勾勒直下天际的洪流、飘逸山头的流云、苍茫树色中的宫阙、苍白月色下的钟声,也不细绘精写眼前的绿水渔翁、落花尘雾。因为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2]
上述观点的提出,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深深根植中国悠久的比兴传统中,下文将选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比兴关系的认识作为传统诗学的代表,对照分析《怀麓堂诗话》对其思想的继承。
二、刘勰的比兴诗论
刘勰在《诠赋》篇提出的“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论、《物色》篇中的“心随物宛转”和“物与心徘徊”《隐秀》中的对隐秀二者的判断:“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以及《比兴》篇中对比兴手法的系统性概述。[3]这四者表现了刘勰的比兴主张,接下来我们将对比李东阳的文论理念进行逐个分析。
(一)《诠赋》篇:比兴之间,先取兴者
在《诠赋》中,刘勰认为:“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即内在的才情要由外物而触发,因此文义必须明洁典雅;外在的景物要由内在的才情而反映,所以辞采必须艳巧绚丽。[4]总的来看,刘勰认为好的诗文既追求辞采的绚丽,又力图义理的典雅,彼此相得益彰。按照刘勰的理论,二者兼得,固然是好文章,可世间鱼与熊掌兼得者又有几人。因此后世文人,纵希求尽善尽美,实则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偏废一方:如晚唐与元代诗人的重物像之辞工,而流意旨于衰颓,宋人的重义理而“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陷诗文于枯索。
以李东阳为代表的复古派同时反对这两种倾向,所谓“宋人专用意而废词,若枯蘖槁梧,虽根干屈盘,而绝无畅茂之象。元人专务华而离实,若落花坠蕊,虽红紫嫣熳,而大都衰谢之风。”他们提出要注重诗的“色泽神韵”,重“情”、重“兴象”,再次高扬诗的独立地位,注重诗之本色,不能如宋人一般作诗如作文,以至将文的议论事理混入诗中,冲淡了诗本身具有的抒情特征,正如何景明所言:“夫诗之道尚情而有爱,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感情者,诗之道也,慈惠出焉;经德纬事者,文之道也,礼义出焉。”李东阳也有类似的论述:“诗与文不同体,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韩退之以文为诗,固未然。”也不能如晚唐与元人一般,混淆诗与词的界限,过于雕琢辞藻,放纵私情,少丈夫语。总而言之,既不能像文,亦不能似词,即所谓:“诗太拙则近於文,太巧则近於词。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因此,复古派诗人基于文学史视角,确立了以盛唐为宗的诗歌创作理念:“苏黄矫晚唐而为杜,得其变而不得其正,故生涩崚嵴而乖大雅。杨范矫宋而为唐,舍其格而逐其词,故绮缛闺阃而远丈夫。”但明代复古派诗人在提出诗论后,是否真正在实际创作中成功贯彻了呢?尚待考量。
(二)《物色》篇:以兴导比,以质刻物
然而,纵抓住了诗的情意,无人能够凭空抒发,我们依然不得不依托于比之外物,更不必说许多的内心所感本就是由五感在外界的所视所闻而启发的。正如李东阳所言:“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於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如何能够在借助意象的同时避免其喧宾夺主呢?刘勰和李东阳也给出了相似的方法,一是以兴的高远雅淡以导比,二是刻画比物时注意用词的简洁质朴。刘勰在《物色》中言道:“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认为大凡吟咏诗歌,其志必须幽远高深,以此去体察景物的美妙,并比附文辞,才算大功告成。[4]这正与李东阳的“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相合。刘勰还认为:“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即风物景色虽然千变万化,但作家的遣词造句,却应务求简要,使诗味盎然,如清风之吹拂;文情朗畅,若皓月之初升。他还赞叹诗经的创作者们,“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以极少的笔墨去总括繁多的形象,而诗人的情感和风物的面貌,却都能略无遗漏。这正与李东阳所说的“古诗辞贵简远”相通。[5]
(三)《隐秀》篇:天真兴致
但若如上文所论,作诗用词重在简要淡远,岂非李商隐、西昆一体,皆非好诗?岂非文辞质朴简练者,皆得好句?诗的辞句究竟如何写才不致浮丽雕琢?在这一点上,刘勰和李东阳一致认为:应当发乎自然。刘勰在《隐秀》篇提出:“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即有的作者把文句的晦塞生硬当作精深,但这只是文句的艰深难懂,并不是文义的委婉隐曲。又有的作者用雕琢刻削的手法来撷取纤巧的文辞,但这只是堆砌的华美,并不是自然的秀逸挺拔。所以文成自然、妙合天机的作品,就好像花草树木,自然显耀出它的奇葩异彩;但若润饰词句而刻意来博取华美,就好比在丝绸上渲染朱红碧绿的色彩,虽然颜色深浓而繁缛鲜艳,但终属做作。这与李东阳的“贵质而不俚”“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不谋而合,追求简与淡绝非沦于俚俗,而是在坚守诗的文学性特质的基础上,本乎自然,发于自然,所谓“天真兴致”。
三、结论
“比兴”自古以来便是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重大命题,比兴关系所蕴含的言有寄托、风神韵味、含蓄隽永的经典审美意趣是中国丰富灿烂的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言及比兴:“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人生于自然天地之间,托身于庙堂江湖之内,所兴所感中,最幽微、隐约、难以用简单语词概括者,便从比兴中寻求寄寓,将诗人含蓄又炽烈的情感蕴藏在深远辽阔的象征中,形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效果。因此,比兴可谓是一代代书写者人性魅力和文化品格的生动投射。正因其极为重要的文学地位,也造就了其复杂难解的理论特征,自古以来的创作者和鉴赏家就这一命题不断思考、探索、完善,在契合的同时又有超越,从而一次次地为文坛正本清源、振叶寻根,为人类与世界的共振寻求新的突破,攀登至情与自然彼此融汇的新高峰。[6]
参考文献:
[1]李东阳.怀麓堂诗话[M].北京:汇聚文源,2015.
[2]邱昕悦.《怀麓堂诗话》文体理论研究[D].湖南:中南大学,2022.
[3]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刘勰.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5]以比较的视野看刘勰的复古文学思想[J].江西社会科学,2004(7):179-186.
[6]刘勰“比兴”修辞论之探析——以《文心雕龙·比兴》篇为中心[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4(05):55-61.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828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