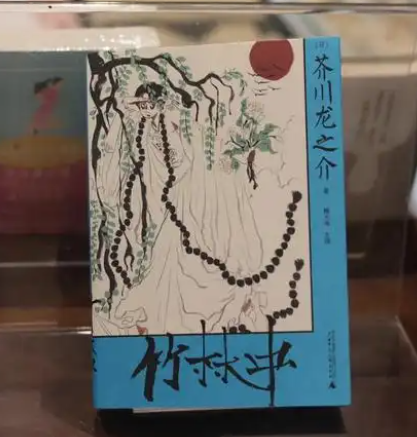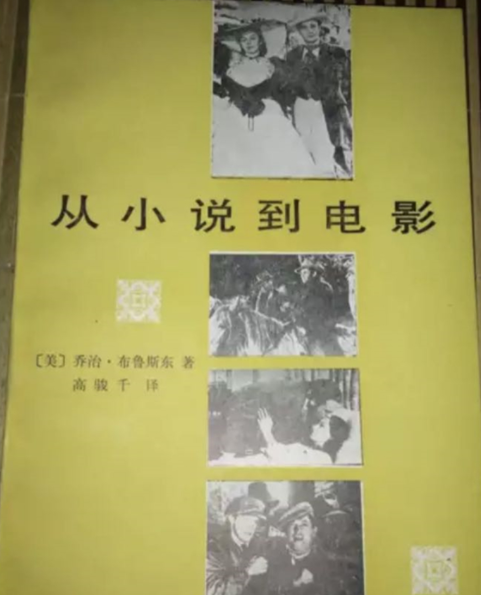文学原著与电影改编的关系时至今日在文学界仍然有人抱有这样的成见:电影是戏剧和摄影联姻的“私生子”,往高处说不过是一种庸俗的商业化媒体。改编后的电影经常被拿来与文学原著比较,结果可想而知——“风马牛不及”常常成为其标签,评论家和观众也大都大失所望。以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文学原著与黑泽明改编后的《罗生门》电影为例,从文学原著的樱花精神、电影改编的可能性、双方的相辅相成与“创造性背叛”四方面进行考察,从而论证文学原著与电影改编的“桃李关系”,以期为改变文学界的成见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文学原著与电影改编的介绍
芥川龙之介创作于1921年的《竹林中》以樵夫在竹林中发现死去的武士尸体为开端,随着案件调查的展开,多名相关人物登场提供证词:发现尸体的樵夫、妻子真砂与其母亲、行游僧、强盗多襄丸与被受害者亡灵附身的巫师。几位当事人向审判长讲述了从自己的利益考量,不同版本的案发经过,但各方各执一词、矛盾重重,事情的真相也变得模糊不清,如同一个不可破解的悬案摆在读者面前。1950年,由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原著:《竹林中》)上映,文学原著与电影改编的关系也逐渐受到文学界的关注。
在文学原著《竹林中》中,推官的审讯是情节展开的脉络,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首先,樵夫讲述了自己像往常一样在上山砍柴的途中,于山后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男性无名尸体,尸体周围的草被踩得乱七八糟,伴随尸体留下的还有绳子和梳子。行脚僧则讲述了晌午时分,自己与一名骑马的女子同去关山,见到那男子佩刀且带着弓箭,却没想到他最终会被杀害。捕快也讲述了自己赴命去抓捕大盗多襄丸的情景,大盗多襄丸既带了刀,也带了弓箭,这正与被害人死亡时的情况吻合,同时大盗多襄丸过去又有犯罪前科,因此可以合理断定一定是多襄丸杀了男人。老妪也道出受害者正是其女婿,为狭国府的武士,性情温和,从不招惹祸端,且夫妇两人洁身自好。现不仅女婿被杀害,女儿也不知所踪,最可恨的还是多襄丸这个狗强盗。
接着,也来到了故事情节的高潮,大盗多襄丸承认自己杀了男子,但没有杀女子。他见到女人的美貌后便萌生了一定要把女人弄到手的念头,便借口寻宝将男子骗去杉树地下,并绑了起来。女子见到丈夫时,提出“自己死,或丈夫死,两者死一个”的说法后,多襄丸才不得不答应女子的请求杀了男人。此后,场景又转到了清水寺,女人忏悔道,自己被大盗多襄丸糟蹋后,丈夫却对她冷漠憎恶,这使得她无地自容,才不得已拿起刀朝丈夫胸口刺去;且自己也决定寻死但未遂。最后,来到了小说的结局。男人的亡灵借巫师说道,妻子被强盗的花言巧语迷得失去理智,甚至教唆强盗将其杀害,自己不堪其辱,最终拿起匕首刺向自己的胸膛。这时,有人蹑手蹑脚地来到自己身边,悄悄拔出自己胸口的匕首,顿时口中血*喷涌,永远沉入了幽冥的世界。
电影《罗生门》相比文学原著,内容有所删减,如女人岳母的供词被删减,但电影特有的叙事手法与转场方式也让人物形象更丰满,人物特点也变得更突出。同时,无论是电影开头破败城门营造出的肃杀恐怖气氛,还是大雨前后的罗生门,或者是巫师施法下狂风刮起、亡灵附身等独有的环境渲染,都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文学原著与电影改编的关系
电影改编以文学原著为基础,延续了日本人对“樱花精神”①的执着,弥补了作品结尾存在的缺陷。文学原著《竹林中》的叙述过程,以当事人的辩解开始,又以其辩解结束,无论是发现尸体的樵夫、妻子真砂与其母亲、被受害者亡灵附身的巫师、强盗多襄丸或者是行游僧,每个人在案件的审问过程中,无不袒露人性的错综复杂,贪婪、懦弱与自私也无时无刻贯穿其中。这样扑朔迷离的结局在普通观众当中或文学界都不时受到批评,没有结局的文学也被认为是使它呈现不瘟不火状态的原因。
在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电影中,人性的险恶虽表现得大同小异,但在电影的结尾镜头再次回到罗生门前,樵夫大声怒斥乞丐夺走婴儿的衣服,乞丐指责樵夫偷走匕首与僧人质疑樵夫抱走婴儿的目的时,樵夫表示家中生活困难,有其他六名孩子需要抚养。同时,在樵夫做出决定、乞丐愤恨选择离开之时,荒凉阴森的城门前的雨也意外地停了。
这看似不经意间的短暂结尾,却如点睛之笔打破了沉寂阴暗的基调,使人性的美好重新绽放,凸显导演在思痛时代对梦华的期盼,这也如同日本的国花樱花一般,在颓败沉寂的冬日里,打破凄凉之景,给予他人对美的重现与再塑造,深刻影响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与审美观念。
文学原著为电影改编提供范例,助力电影探索自我的更多可能性。在原著《竹林中》的情节展现中,怀疑主义与利己主义互相交织,每个人都在为维护自身的形象与利益展开激烈的争辩,这为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优秀的素材,但美中不足的是,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个人辩解似乎将原本简短的小说进行再分割,使充满谎言与罪恶的书中世界黯然失色。
在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电影展现过程中,以象征地狱与人间分界点的罗生门为开端,乞丐、樵夫与僧人回忆与交谈当日情况,不断推动了跌宕起伏的情节的发展。暴雨下的罗生门与雨停天晴的罗生门、公堂上由哭转笑的受侮辱妻子、英勇无畏的日本武士②与落荒而逃的背影等,以文学原著的原始角色为基本,在电影渲染的视觉文化氛围下,达到全方位刻画人物形象的效果,也使得情节推进更加条理化。
1951年,由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斩获了第1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圣马克金狮奖——最佳影片与第2届日本电影蓝丝带奖——最佳剧本;同时,电影的问世也推动了小说影响力的扩大化,进一步走进大众的视野。
文学原著与电影改编的“藕断丝连”,蕴含在方方面面,促使双方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无论是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还是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无不建立在确保忠实性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或再创作。文学原著《竹林中》的情节,以各方供词为线索展开,每个人在讲述事实的同时,又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人性的险恶与凶险在此刻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中,罗生门下倾盆大雨,乞丐、樵夫与僧人围绕人性展开激烈的争辩,人性的善恶也在罗生门下有不同的展现方式。无论是忏悔的僧人、抢夺匕首与决定抚养婴儿的樵夫,还是为生存抢夺无反击之力婴儿身上衣服的乞丐,站在人间与地狱的分界点上,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最后的选择。如此阴暗、潮湿、凋零、残酷败落的罗生门景象下,是芥川龙之介内心的写照,是他无法诉说的苦闷,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内心的迷茫与不安。
双方对人性毫不掩饰的刻画,一方面肯定着人性的冷酷和残忍,另一方面透露出对人性本质的怀疑和对“要道德、良知还是要生存、活命”这样伦理的拷问,无不突显出人性的本能良知对“善”的呼唤。
文学原著与电影改编的“桃李关系”,亦是创造性背叛。“创造性背叛”原本是文学翻译领域常用的术语。之所以用在此处,因为文学原著与电影改编原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学载体,将文学转化成电影,本身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所以说,导演对文学原著的理解与把握,直接决定改编后的电影会以何种方式最终呈现。
导演如果想表达何种感情或思想,必然需要以文学原著为基础,然后选取合适的情节加以放大或细化,这便是“创造性背叛”的开始。就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而言,破败的城门可以认为是导演欲表达某种思想的目标。在电影开端,大雨如洪水般涌来的城门下,一众人相聚于此,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议论起自己的所闻所见,议论之时有舒缓,更多的却是激烈的争吵。而在电影的结尾,当乞丐选择夺走婴儿的衣服去换钱、穷困潦倒的樵夫在家中已有多名孩子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抚养婴儿的时候,每个人最终都在人性的抉择下做出了决定的时候,原本的倾盆大雨也停止了。这样的情景是以原著为基础的再延伸,也强化了对人性本质的拷问与呼唤。
同时,导演无论如何进行改编,其基本情节脉络与文章是吻合的,这也是“创造性背叛”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并不把改编后的电影作为文学原著的另一版本,而是称为“改编”的重要原因。无论是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文学原著还是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电影改编,离不开的是各位证人或受害者亲属对自己所见所闻的讲述,也更离不开受害者“本人”对自己的证言。但是,在基本的情节脉络下,其传达的感情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又有所差异,且带给读者的观感亦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文学原著与电影改编之间的“创造性背叛”可以与“桃李关系”划上等号。文学原著为电影提供了故事框架,电影也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文学原著的背景设定,这也是导演灵感的直接来源。改编的电影不仅可以让读者思考电影传达的思想与感情,还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让读者重新思考文学原著,从而在作者创作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创作”。
日本文学原著与电影改编共同构成了这段“桃李关系”。文学原著是桃李之树,改编后的电影则是桃李结出的果实。文学原著为电影改编提供富足的营养,滋润其茁壮成长,从而结出饱满的果实。来年,当电影改编的果实撒播在大地上,春暖花开之际,其由读者“第二次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会冒出新芽,比过去的任何时刻都显得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活力。日本文学原著与电影改编,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靠,从而推动彼此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①樱花精神: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一,认为人生如樱花一般,只求华美一瞬,短暂亦无妨。
②日本武士:身手矫健灵活,忠诚勇猛,常佩长刀与短刀,眼中饱含令人畏惧的杀气。一旦武士被俘虏,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与不叛变决心,第一时间会选择切腹自尽。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799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