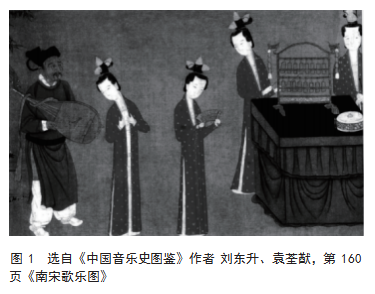摘要:在宋代,音乐机构在宫廷的音乐活动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些机构种类繁多,包括太常寺、大乐署、鼓吹署、教坊、钧容直、云韶部、东西班以及大晟府等等。这些音乐机构对于宋代宫廷音乐还有宋代民间音乐的整体发展都产生了意义深长的影响。因此,研究宋代的宫廷音乐机构,对于认识宋代的音乐文化及其本质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将目光集中在宋代教坊音乐机构的探究上。
关键词:宋教坊,音乐机构,教坊乐制
引言
建立于唐代的教坊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中一个重要的宫廷俗乐管理机构,此机构经历了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沧桑变迁,曾经在唐代时期达到了鼎盛。宋朝虽不似唐朝一般拥有巨大财力的支持,但宋朝宫廷里设置的音乐机构同样有很多,且承担着音乐的运行、管理。教坊就是其中一个,而且宋教坊在宋代音乐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宋代延续了诸多属于唐代音乐机构的传统,设立了教坊。由北宋建立,经过南宋时期的变迁,教坊也慢慢地淡出了音乐历史的舞台中心,逐渐式微。宋代成为教坊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
一、宋教坊源起
宋代的教坊作为宫廷中极为重要的音乐机构来说,其主要承担的工作就是管理宋代燕乐的创作和表演。其对于宋代音乐来讲,这个存在于宫廷中的音乐机构不仅仅是推动了宫廷中的燕乐发展,它也极大地影响到了宋代民间瓦肆勾栏的发展。
谈到宋代教坊的源起,就要回到公元960年。后周时期的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并自立门户,建立起了北宋王朝,标志着一个崭新历史时期的开始。依据文献记载,在北宋建国后的二年的正月一日,大臣们便已经在朝贺的仪式中开始采用教坊乐。由此我们就能够判断出,北宋教坊的历史可以追溯北宋到建国之初的第一年。宋太宗赵匡胤在建国初期就重新建立了教坊。在建国后的20多年里,北宋持续发展壮大,教坊逐步汇集了由于战乱流散各地的乐工,使各地杰出的乐工乐人齐聚于此。
宋代教坊在多个方面都沿袭了唐代教坊的体制,但在教坊的从属关系方面,唐代是由皇家宫廷负责管理的,而宋代教坊在创立初期则是由宣徽院负责管理,到了北宋中期,宣徽院被废除,宋教坊改为太常寺管理,直至靖康二年,汴梁被攻陷,教坊的乐器乐书全部散失,北宋教坊随之告终。
北宋倾覆南宋开始,南宋时期教坊成立的时间已经无法考证,但历史记载清楚地显示,处于南宋时期的教坊曾经历过多次裁撤与建立。其被废止的主要原因是南宋建立之时,政治机构尚不稳定,所以在南宋建炎初年,教坊被废除。绍兴十四年时,教坊重新设立,但其维持的时间并不算持久,在绍兴三十一年之时,金人再次大举入侵攻打,由此,南宋的教坊也就被彻底废止了。南宋时期的教坊在绍兴晚期被废弃,但到了孝宗的乾道和淳熙时期,教坊的职责被教乐所取代,原先属于教坊中的乐工乐人全部被解散,一部分教坊的乐工被派往德寿宫任职(德寿宫是宋高宗退位修养的地方),还有一部分的教坊乐工分配到了地方之上,到临安府衙前乐中充当乐工。
自绍兴末取消教坊之后,教坊事务被归属于教乐所管理,表明南宋政府不再养活专门从事教坊演出的固定乐工,教乐所已完全控制了原本由教坊负责的一些功能。在教乐所的时代,尽管没有教坊这样的机构存在,但教坊的声誉仍然不减,宋代的小说和笔记经常提及。教乐司是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之一,在当时也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但由于历史原因没有被重视。教乐所的存在一直延续到南宋的末期。
在乐工的设置方面,教乐所中的乐工主要由市人、杂攒组成,两者皆为街坊艺人类似的身份。乐人成分具有临时召集和雇佣制的特点,也就是所谓的“和雇”。
康瑞军老师针对和雇制度,发表过一篇文章,《和雇制度及其在宋代宫廷音乐中的应用》[1],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和雇制度的缘起、和雇乐人的构成以及和雇制度的影响等等。南宋的教乐所大致与南宋的政治权力相始终,设立于绍兴三十一年,前后存在约一百余年,在南宋宫廷音乐活动中,无论是教坊还是教乐所,由于当时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它们凭借与民间音乐关系更为密切的优势,全面超越了当时的太常寺。
南宋时期的教坊命运多舛,经历过设立、裁撤、再设立最后彻底废除多次变化。于绍兴年间的教坊再度废撤以后,转由教乐所取代了教坊的职能,其中的原因是在宋朝整体大环境缩减的背景下,各个音乐机构都受到了缩减,教坊作为宫廷中重要的音乐机构,也未得到幸免。后来设置的教乐所相比教坊来说更为精简,用乐以及乐工方面都受到简省,不过即使教坊机构实体已经消亡,但是其名号是存在的。
宋以后,元世祖中统二年设置教坊司,到了元十七年,改教坊司为提点教坊司,隶属宣徽院,后来隶属礼部。明朝的明太宗朱元璋在平定江陵(现在的江苏)南京的第二年,便建立了教坊司,隶属于礼部,掌管宴乐大会,至清代,顺治元年,设立教坊司,雍正时期将教坊司更名为和乐署,依然是主要掌管宫廷宴享的音乐。
综上,南宋之后的教坊整体呈现出临时性和减省性的特点,原因主要因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宋朝的统治者更加倾向于精简机构设置,以便于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时局。另一个原因是自宋代开始,民间的音乐活动蓬勃兴起,这给宫廷的音乐活动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影响下,南宋的宫廷音乐逐渐演变为一种与民间紧密结合的新型音乐形式,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南宋时代宫廷和民间音乐文化的广泛传播。
二、教坊乐制的来源
有关宋代教坊乐制溯源之问题,赵为民老师的《试论蜀地音乐对宋初教坊乐之影响》以及张国强老师的《宋代教坊乐制研究》两文中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赵为民老师的文章指出蜀地音乐在宋初教坊乐制的形成过程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2]。
在张国强老师的文章中,则在前文的基础之上,对宋代教坊乐制的来源概括为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主要是继承唐制和受到蜀地的影响。首先,宋代之前的五代时期虽然长期受到战乱的影响,当时的宫廷音乐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由于五代时期十分注重对于礼乐制度的恢复,曾倡议过“复兴雅乐”之议等活动,后周末期时,随着窦俨编写的《大周正乐》的面世,雅乐的制度也逐步取得了恢复。因此,北宋在建国后,实际上继承了后周的雅乐传统,而宋初的宫廷雅乐正是后周雅乐的代表。虽如此,但宋初的教坊乐制所遵循的并不是后周雅乐,其为承唐制,据考证,《陈旸乐书》中记载有关于宋初教坊乐制确立的文字记录,在其中就曾明确指出其乐制来源于唐[3]。
宋初教坊乐制不循后周而承唐制,在张国强老师的文章中所认为: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北宋建立之初,大约有过二十年的时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北宋教坊也随之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乐工。然而,在唐代末期和五代时期,长时间的战争导致了乐工的大量流失,尽管宋代初期建立了教坊,但这些教坊的制度仍然不够完善,所以北宋王朝在发展壮大期间,为了进一步完善制度,均将由于战乱而四处流散的五代乐工纳入了宋教坊。笔者认为此说法逻辑清晰,符合史料记载。再谈,观察宋初教坊中乐工的来源,蜀地的乐工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因此蜀地对于北宋教坊乐制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参考。
在安史之乱时,长安被占领,唐玄宗逃到了蜀地,而后唐僖宗也逃到了蜀地,由此给蜀地带来了大批的文人、乐工等等,对蜀地音乐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使得蜀地成了最有条件保留唐代宫廷乐制的地方。宋初时期大批蜀地乐工进入了教坊,从而使得宋初教坊得到了扩充,而在日后宋教坊逐渐形成乐制体系的时候,蜀地乐工在宋代教坊中人数众多,理所当然成为骨干力量,且这些乐工技术水平又高,故而占有特殊地位[4]。由此可以得出,宋代教坊乐制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其继承唐制,其次就是蜀地确实对宋初教坊乐制产生了极为特殊的重要影响。
三、教坊与其他宫廷音乐机构的关系
(一)与均容直的关系
钧容直是宋代军事机构所辖的音乐机构之一,均容直隶属于中央禁军属下的音乐团体。在太平兴国三年公元年从军营之中选拔出了擅长音乐的士兵组建而成。初名叫做“引龙直”,后来取“钧天”之义,改名称为钧容直。均容直于绍兴三十年间解散,历时一百六十八年之久。
关于宋教坊与钧容直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北宋教坊四部乐中含有龟兹乐,而钧容直中也增设了龟兹部,且规模与宋教坊龟兹部相同,所用乐器也相同,这直接体现了宋教坊对钧容直的影响。二是因为《宋史》中有记载,两者经常在许多场合之中进行共同演奏,所以两者可以说是一种很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5]。当教坊和钧容直一起进行演奏时,他们的音乐风格并不和谐,导致教坊的乐曲取代了钧容直原本要演奏的大曲。因此,之后钧容直演奏的许多乐曲与教坊的演奏风格有许多相似之处。
(二)与大晟府之间的关系
北宋音乐史上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音乐事件,在当时,朝臣之间曾出现过多次乐议活动,这同样是北宋雅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事件,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一定的影响。而大晟府就是北宋乐议的成果[6]。宋代的统治者十分强调三纲五常、等级制度,乐制。原来是由太常寺掌管礼乐,到了宋代,宫廷就将礼和乐两者区分开来,进一步设立了专门管理雅乐的大晟府,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乐机构。大晟府主要掌管各种典礼所用乐,其大都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祭祀仪式,朝会,册封太子皇后等等。
宋徽宗时期设置了大晟府,其重要缘由是因为陈扬进献的乐书二百卷,其中提到神宗、哲宗朝“尚用教坊杂乐,未讲先王雅颂之制,二变四清,杂然并举”,陈扬认为这种做法“非先王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之意也,可不厘正之,以和臣邻化天下邪”宋徽宗接受了陈扬提出的建议,开始对宫廷乐舞进行一些复古式的改革。改革后的乐舞称为“新乐”,并设置大晟府掌管新乐。于是大晟府不仅与太常寺共同分掌礼乐,还管辖着教坊。对教坊所使用的乐器、所奏的乐曲及宫调数目都进行了调整。宣和七年十二月,由于金人入侵,朝廷下令整顿机构,废除各种部门。于是,机构中的大部分乐工乐人都被解散。在北宋政权被灭亡后,大晟府中的乐器也几乎全部散失。
四、教坊乐制探究
四部乐是北宋教坊的重要乐制之一,据《宋史》记载,宋代教坊循唐制,有四部乐,但其并未明确指出教坊四部乐的名称,仅列举了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三部的名称,所以宋教坊四部乐中另一部的名称受到许多学者的考证。日本学者岸边成雄认为宋代教坊四部乐之一应当还有“云韶部”。他认为“据说太常四部乐当初系乐器展览而非四部伎,将乐器分成四类,而在太乐署内设庭展出,供公卿观览。”这句话的含义是,太常四部乐制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乐器的分类方式。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岸边成雄的学者所持的看法,仅仅是一种具有推测性质的观点,他并未提供足够有力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看法。但支持这一岸边称雄观点的学者并不是少数,其观点对众多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小盾先生同样认为“太常四部乐是一种对太常寺所掌乐器进行分类的制度,流行于唐宋两代[7]。”不过王小盾老师认为四部乐名称应为“龟兹部、鼓架部、胡部、鼓吹部”。
在张国强老师的《宋代教坊乐制研究》对以上几种观点进行了论述:
首先,他认为由于四部乐名称的考述缺乏史料的明细记载,所以目前我们尚不能对四部乐性质,其名称是什么给出明确定论。依据史料《玉海》所引述的玄宗《实录》中记载,提到太常四部乐,其最初出现是在唐玄宗时期宴请吐蕃使者的宴会上,据此可以推测出四部乐并非岸边称雄所认为的是一种乐器分类法,其是用于宴会享乐的,似乎不能将太常四部乐理解为乐器分类法,因为它与唐代的多部乐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如此一来,王小盾老师以及日本学者岸边称雄对于四部乐为乐器分类法的说法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再看岸边称雄所说的四部乐之一为云韶部的说法:云韶部建立于宋代初期,属于宫廷音乐机构,最初叫做箫韶部,从教坊之中学习音乐。云韶部的职务就是在宫内或者亲王府内供乐[8]。大多数持云韶部属于宋教坊四部乐之一观点的学者,比如岸边称雄,他所论述的依据就是因为云韶部一度学习于教坊中,并且于宋代初期建立,所以认可这种说法,至于为何云韶部未曾与其他三部记载于一处,原因在于北宋时期的一场“元丰改制”,受到了音乐机构改革的影响。因此黎国韬老师还提出,在机构改革前,云韶部隶属于教坊管理,在改革之后才隶属于宫廷管理。张国强老师以上这些论据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据其考证,宋教坊四部乐的设立要早于云韶部,早了至少10年,所以云韶部不能归入教坊四部乐之中。并且后来宋教坊机构承唐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本质上是一个负责管理和培训音乐家的音乐机构,而且在教坊里学习的不仅仅是云韶部,同时作者还提出云韶部虽于教坊之中学习,但是其乐工是南汉的宫廷中获取的内臣,与一般教坊乐工的身份不同,再者,考证了《玉海》和《宋史》中的资料后又出云韶部自成立之初就一直由内廷管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云韶部并不属于教坊四部乐之一。
再看王小盾老师所说的鼓吹部,笔者认为,王小盾老师鼓吹部说法的观点可能并不妥当,因为宋代的鼓吹主要用于祭祀,法礼等等的正式场合,由专门的鼓吹署机构管理,隶属于太常寺掌管,而宋教坊显然是俗乐机构,两者性质、应用场合都有所出入。所以这种说法尚值得商榷。杨荫浏先生在谈到宋代教坊的内部组织时推测认为,其应是分为大曲部、法曲部、龟兹部,和鼓笛部四部。张国强老师认为杨先生的推测是有道理的:其论述为:陈旸《乐书》卷一百八十八:“教坊部”条云圣朝循用唐制,分教坊为四部……,非如唐分部奏曲也。其中“非如唐分部奏曲也”这句话不仅仅代表了唐朝所实行的是“分部奉曲”,并且还直接显示出了宋代教坊四部合一之前的性质与唐朝是一样的,都是“分部奉曲”,属于乐的性质。由此可以推测出宋教坊之所以要分为四部,其主要是承继了唐代的制度,都实行了“分部奉曲”,《宋史·乐志》所载“所奏凡十八调四十大曲”的那一部,为宋教坊四部之一部,无疑问教坊另外三部所奏分别为法曲部奏大曲二,龟兹部奏大曲二,鼓笛部未详载所奏曲目及曲数。可见,固然各部所奏大曲在风格上可能有所区别,但均以演奏大曲作为其分部之依据,只是所奏大曲之数目不同。如此一来,则可以明确宋代教坊四部乃和唐代多部乐与二部伎一样,都是“分部奉曲”的[9]。
结语
宋代的宫廷里有许多音乐机构,教坊属于宋代众多音乐机构之一,它的职能主要是进行宴乐的表演和创作。本文论述了宋教坊的源起,其在北宋建国初年即已建立。至南宋时期命运多舛,多次裁撤,整体呈现出简约的特点。针对教坊乐制的来源,笔者在认同前辈学者观点基础之上总结为,宋代教坊乐制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其继承唐制,其次就是蜀地确实对宋初教坊乐制产生了极为特殊的重要影响。宋代众多音乐机构中,与教坊关系最为密切的有二,分别是大晟府和禁军乐队均容直。最后,关于宋教坊四部乐之一是什么的问题众说纷纭,结合前人研究成果,首先否定了其作为乐器分类法名称的性质,再者,四部乐之一为云韶部以及鼓吹部均不妥帖,而杨荫浏先生推测为大曲部的观点经张国强老师史料的论证最具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康瑞军.和雇制度及其在宋代宫廷音乐中的作用[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7,(02):79-88+5.
[2]赵为民.试论蜀地音乐对宋初教坊乐之影响[J].音乐研究,1992,(01):6.
[3]赵维平.宋教坊的形成、内容及与唐教坊的关系考[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02):108-113+5.
[4]卫亚浩.北宋教坊的灭亡[J].唐都学刊,2011,(05):102-105.
[5]陈卉.北宋教坊的政治功能及其属性[J].音乐天地,2023,(06):4-12.
[6]宋康,刘茜.论教坊对宋代音乐文学的影响[J].音乐探索,2020,(02);80-84.
[7]刘媛媛.宋代宫廷音乐机构研究[D].武汉音乐学院,2007.
[8]徐蕊.略论宋代教坊[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4,(S1):7-9.
[9]张国强.宋代教坊乐制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4.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799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