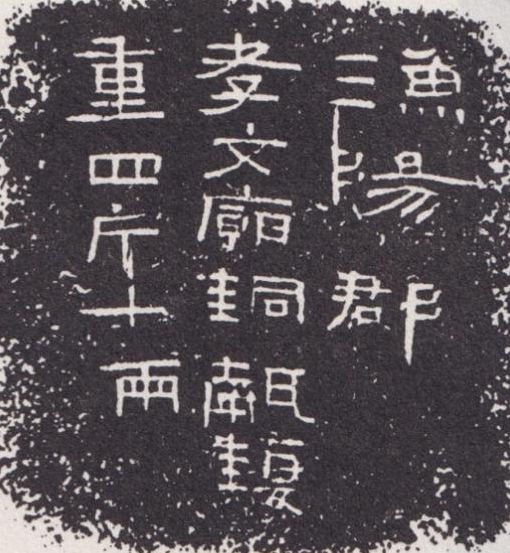汉武帝晚期被视为汉朝向守文转向的重要时期,在汉武帝晚期及霍光执政时期,儒家思想地位大幅提高,儒生群体成为重要政治群体。但武帝之后长期的理政思想依然保持了重视历史经验与实践操作性的黄老与法家学说特点。包括皇帝与百姓都仅仅将儒家理论视为解释性的话语体系,并不重视儒家理论的具体实践意义,但伴随儒家理论这一社会文化对社会个体的行动影响加深,事实上使得帝王在进行政治决策时更多地要考虑儒家理论,汉武帝后的理政思想存在着一个儒家化发展的显著特征。
武帝时期是两汉思想与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田余庆在《论轮台诏》中将汉武帝晚期视为汉朝向守文转变的重要转折期①;徐复观也认为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在保持儒家理论仁义的内核下对儒学内容的重新解读与发展,是两汉思想与政治转向的重要标志②。武帝晚期以及霍光执政时期,是儒学思想开始成为思想主流,儒家群体成为重要政治群体的重要时期,这是符合历史印象的,但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汉朝的政治治理思想并未带有鲜明的儒家化特点,即使是出于汉朝转向守文的霍光执政时期,其政治行为也依然是和武帝前期极为相似的,赵鼎新将这一现象总结为外儒内法,他认为儒家思想在汉朝只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而内在的政治理论依然是法家的而非儒家的;要验证这一观点,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何儒家理论可以解释法家的政治理论这一问题。余英*将汉代儒学的发展解释为“儒学的法家化”,认为在汉代,儒家的核心观点从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变为了法家的“尊君卑臣”论,这一解释为为何儒家理论可以解释法家的政治理论提供了答案。但事实上,汉朝儒家对于皇帝依然保持了一个限制的态度,董仲舒即有“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论断,而之后昭帝时,眭弘就上奏说:“汉帝宜谁人,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宣帝时,盖宽饶上奏称:“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即使汉朝的儒家思想仅仅作为意识形态来产生功用,但在具体的理政行动上也必然是具体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进行了修改与变化来符合儒家学说的观点,而非儒家思想法家化来契合具体的政治实践理论。
要理解为何在儒家思想占据了思想主流,儒家群体成为重要政治群体的双重前提下,儒家思想依然只能作为意识形态,而不能成为具体指导政治实践理论的原因,需要再次从武帝晚期及霍光执政时期儒生地位的提升与儒学独尊的现象出发,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还可得出汉朝执政理念的特点及其与后世的联系。
儒生地位的提升与儒学独尊
李开元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中分析了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与汉初政治间的关系,事实上,以丞相职位为例,一直到汉景帝的丞相申屠嘉之前的历任丞相,基本都是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而这种风气实际上也延续到汉武帝时期,其中丞相包括周亚夫、刘屈氂等人都是与军功受益阶层紧密相关的。除去汉高祖刘邦可以凭借手段与威势轻易掌控军功受益阶层外,之后的惠、文、景帝的多项举措,明显是直接受到军功受益阶层制约的,虽然文景时期皇帝与军功受益阶层已经进行了多次摩擦,但皇帝并未试图打破皇帝与军功受益阶层相对平衡的格局,而到汉景帝后由于开国功臣的相继离世,军功受益阶层出现了一个小断层,随后武帝朝军功卓越的是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与汉武帝关系紧密的青年将领,他们与传统的军功受益阶层联系不大,而汉武帝通过扶持他们,进一步削弱了军功受益阶层。
相较于东汉,西汉时期丞相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且官职长期固定为一个。在汉武帝之前,丞相任相时间长,多出身于权贵之家(包括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也多在任上寿终正寝或进行平调;在武帝及武帝以后,丞相任期短,更新快,被罢免以及诛杀频繁,寒门丞相占比也大幅增加。这种对比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武帝在有意打压军功受益阶层。汉武帝既利用卫青、霍去病屡创军功,打压了传统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权力与影响力,又通过连续的罢免、赐死丞相削弱相权,进而打压其背后的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而在以卫青为核心的新军功受益阶层实力日益壮大时,汉武帝扶持了李广利,对这个新军功受益阶层进行了分化打压,同时依然通过对相权的削弱打压新军功受益阶层。直到武帝晚年,由于巫蛊之祸,中央官员受到了大清洗,官员出现了大量真空,而汉武帝采用了大量提拔儒生寒门的方式来填充这一真空。
相应的,在思想领域上,汉武帝通过诏贤良文学策选中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天人三策》一策回答何为大道之要,一策回答如何施行王者之道,一策阐明《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其中关于大一统的描述,被许多学者认为带有文化专制主义的性质,而汉武帝对天人三策的认可,就被理解为皇帝对儒家文化专制主义的认可,因此自易白沙始,许多学者将董仲舒的思想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根据对董仲舒《天人三策》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董仲舒强调罢黜百家针对的是推广官方教育,如班固《汉书》中说:“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而其中关于“邪辟之说灭息”的说法,则是董仲舒对推广自身策略的美好展望,而非文化专制的具体行动。而汉武帝对董仲舒《天人三策》的赞赏,也并不是对独尊儒术的认可,而是对儒学理论解释作用的满意,而之后的大兴官学则和任用魏其、田蚡一样,其目的在于推广儒家理论,但也并非是试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将儒家思想地位的提高与儒生阶层的壮大统一起来考量,以丞相为例,可以发现,汉武帝时期的丞相往往兼顾了儒生与寒门的双重身份,而参考其他三公九卿的职位,可以发现,武帝朝高级官员的一大重要特征可能并非是其儒生身份,而是其寒门身份,像公孙弘、张汤、桑弘羊等人,理念各不相同,却基本同归于寒门而被汉武帝任用。由此可以推测,儒术在政权治理理论上的地位提升不是学术上的胜利,而是皇权争夺相权的结果;而儒生集团的迅速壮大,也只是汉武帝对于儒家学说解释作用的偏好导致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在具备儒家思想地位独大和儒生群体壮大两大条件下,汉武帝之后的时期并未完全转向守文的风气,而是依然保持了重视历史经验与实践的政治理念。
可以明显看到,汉武帝晚期是西汉时期的重要转折时期,汉初皇帝面对的权臣、匈奴、地方三大问题在武帝时期基本得到解决。除去外敌问题依然存在外,汉武帝之后皇帝面对的主要问题变为了外戚与宦官,也就是汉初的军功受益阶层对皇帝的威胁基本已经得到了解决,外戚与宦官的权势滔天,本质上依然是依托于皇权的,因此这种问题的变换是皇权扩张的结果,问题的核心由皇权与相权、皇帝与军功受益阶层间的矛盾变为皇权交接时两代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使得历代皇帝在度过交接的阵痛后在任上往往能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不受挑战。而在武帝朝转向的重要节点,儒家的思想理念实质上并未起到重要作用,而被皇帝与权臣都视为实现目的的工具,像之后的外戚王莽就借助汉朝儒家的理念来推进他的篡权道路。要探究儒家理论对治理理论在武帝及之后为何影响较小,就必须探索武帝为何偏好儒家学说这一原因。
实权与合法性:皇权的两大需求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初黄老道家的思想家大多数为跟随刘邦征战天下的功臣,如萧何、曹参等,而黄老道家在实政的主张偏向依据历史经验来进行务实的政治实践,在这种视野下,秦朝时法家的一系列对君主掌权合理性的论证就极易被批驳。苛政被视为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而君王要求权力集中的行为也被视为苛政将兴的前奏,因此在汉初黄老道家的理论中,并不存在对于帝王集权的正统性论证。由于主张黄老之学的思想家又大多数属于功臣集团,因此汉初的黄老道家理政思路主要就围绕着提高功臣集团的权力来展开,其中汉高祖刘邦本身率领功臣集团统一天下,所以在刘邦在位时期,皇帝权力依然十分强大。汉高祖刘邦尝试废除太子,改立赵王刘如意时,群臣只能劝诫刘邦。而到了汉文帝刘恒时,宰相申屠嘉为了严肃朝廷礼仪制度,多次试图斩杀汉文帝宠臣邓通,这种不同体现了汉初帝王缺乏权力合法性的学理支持,在黄老思想的历史经验理论指导下,帝王不能在即位后便享有实际的权力,而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来掌握权力,而在这种过渡时期,功臣集团的老臣则凭借自身的威望与实力实际掌握了中央政府的核心权力。
黄老之学要求帝王清净无为以及以法度为依的理念,实质上维护了汉初功臣集团的利益诉求,论证了功臣集团掌权的合理性,这种理论在汉高祖时期受到高祖与功臣集团的一致认可,因为刘邦的权威和实力足以驾驭群臣,这套理论实际并未对他的权力造成约束,而在文帝、景帝时期,皇帝的利益与功臣集团的利益分野逐渐明显,黄老之学的理论则实质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伴随着申屠嘉的逝世,之后继位的丞相如陶青、刘舍等虽属功臣集团,但实际能力与影响力均不如之前的丞相,在此背景下,汉武帝继位后便尝试打破丞相出于列侯的传统,提拔了寒门丞相。但皇帝既要打击功臣集团以加强自身权力,又要依靠功臣集团维护自身统治,因此汉武帝选拔丞相以及百官的新标准依然要让原来的功臣集团拥有上升渠道。出于分化功臣集团、加强皇权的目的,汉武帝提拔了一些儒家的学子,这个数量在朝臣占比中并不大,并且汉武帝同样也提拔了张汤、王舒臣等法家学子,但汉武帝表现出的对儒家理论的喜好,直接影响到了臣民对儒家学说的态度。许多寒门子弟以及一些在功臣集团里不突出的子弟,选择了学习儒家理论以求得到皇帝的任用,这就使得实质上儒学理论的深厚与否取代了军功功绩作为皇帝任用官员的新标准,而由于汉武帝同时仍然关注军事,大力提拔取得军功的臣子,而功臣集团也能够通过学习儒家理论适应新的选官标准,因此汉武帝在君臣权力之间所施展的这套“推恩令”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汉武帝前期的官员结构明显带有由以功臣集团为主到向以儒臣集团为主过度的特点。
由于儒家理论受到世人重视的关键在于汉武帝对儒家理论的重视,因此儒家学者也根据汉武帝的偏好以及理政的实际需要,对儒家理论做出了新的梳理,突出了儒家对于帝王权利合法性的学理论证这一重点。董仲舒建构了“天人同类”“同类相动”“天人感应”的天人关系学说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的三统学说,将天视为汉代帝王的权力来源,又指出汉代与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为“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的继承关系,认为汉代之政兼顾“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的三大特点,这就为帝王集权以及汉朝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儒家的学理支持。董仲舒关于汉代合法性的论证理论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董仲舒所主张的类似恢复井田制度的主张并未被汉武帝施用,汉代的具体理政思路,依然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指导的务实,重视实效的特点。
如果汉代历史平稳地运行发展,也许汉武帝时期功臣后代与寒门儒臣并存于朝堂之上的格局还会持续相当之久,直到功臣集团的影响力逐渐式微,朝野接受以儒家学识为任官的新标准为止。然而在征和二年,汉王朝爆发了一场名为巫蛊之祸的政治事件,卫太子刘据为江充等人陷害而导致刘据以及支持刘据的臣子被杀害,而之后汉武帝发觉事情真相,又诛杀了谋立昌邑王的丞相刘屈氂,而与刘屈氂共谋的李广利发觉事情败露后也投降匈奴。巫蛊之祸与随后的武帝平反实际上对整个朝堂做了一个大清洗,大量的军功贵族后裔由于政治事件而被杀害,使得朝廷官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缺口。值得一谈的是,当时支持卫太子刘据的臣子许多都为儒臣,并且多为谷梁一派的儒家学子,《汉书》中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与汉武帝及其所支持公羊学派的拓边、武功主张不一样,谷梁派的学者宣扬仁政、教化,主张“文教”,但除去儒臣外,支持卫太子的重要力量为卫氏外戚集团。而在汉武帝平反期间所打击的支持昌邑王的刘屈氂、李广利,则代表了李氏集团,因此巫蛊之祸以及随后的武帝平反,打击了老一代被卫青、霍去病提拔的军功集团与新一代为李广利所提拔的军功集团。巫蛊之祸及随后的平反打击了两代军功集团,实质上几乎将汉初功臣集团的后裔一网打尽,这客观上使得支持相权的功臣集团话语权大幅缩小,而由于功臣集团的断层,汉武帝不得不更多地任用寒门出身的官员,而寒门士子任官的重要标准即为汉武帝所确立的儒家学识,寒门通过学习儒家理念得以任官,迅速地填补了臣子的中空,同时迅速形成了新的儒臣集团。
当然,由于汉武帝自身的功业与影响力,新兴的儒臣集团依然不足以抗衡与制约皇权,但汉武帝警惕“暴秦之政”,担心自身的穷兵黩武会招致如日中天的汉王朝如秦朝一样轰然崩塌。在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了轮台的“哀痛之诏”,宣布了其政策方向的转折。汉武帝此时主张禁暴苛、止擅赋、力本农,而儒家的一系列理论支持该主张,儒学在此时才真正成为官方主流思想。但武帝所主张的禁暴苛、力本农的政策实际上同样也可以用黄老道家的理论进行解释,因此,儒家在汉武帝以及之后的宣、元帝时期大行其道,并非官方完全以儒家的理论来指导政事,而是在基于历史经验的具体政治实践上,借用了一些儒学理论来为政策提供学理支持。
下轮台诏后两年,汉武帝去世。在之后的转折关键期汉昭帝时期,中央政府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实际划分为以霍光支持的贤良文学与以桑弘羊为首的兴利之臣两派,而经过盐铁会议与霍光诛上官桀、桑弘羊两大事件后,传统史学家认为这是霍光继承了汉武帝轮台诏的指导思想,推动了汉朝治国理路的转型,也使得儒家理论开始深刻影响政治实践。这一判断是合理的,霍光虽然支持贤良文学,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并不完全重合,相反,在霍光实际掌握了权力之后,他的许多政策实际采用了桑弘羊等兴利一派的主张。这实际上折射了汉朝的政治现实,虽然朝臣中儒臣占比大幅度上升,但这些儒臣往往只是将儒学理论和政治的实际经验相联系,他们的政治主张并不一一恪守孔孟儒家理论,他们政治主张的主体是历史经验指导下的务实理论和儒家仁德礼理论的折中,因此汉朝虽然被认为是儒生帝国的兴起时代,但此时汉代的政治治理思想依然是结合历史经验以及各家学说综合的产物,而非单一用儒家理论来进行指导。
儒家为维护皇帝权力以及为国家推行各项政策都提供了儒家学理的合法性论证,因此随着功臣集团实力的衰退,汉武帝尝试以儒家学识取代功业来作为选官任官的新标准,而这一举措也得到了功臣集团的接受,但随着巫蛊之祸这一特殊事件的出现,功臣集团后裔被大量诛杀,这加速了寒门儒生参与朝政的进程。而为了迅速填补巫蛊之祸后的空缺职位,汉武帝提拔了许多寒门儒生,但由于当时儒生非经由固定的标准与制度获得臣子之位,而是被皇帝赏识提拔而得臣位,因此并不恪守自身所学的儒家仁义理论,而是将儒学当作晋升的敲门砖,在具体执政时,他们仍然继承了以史为鉴的经验指导的传统。此后汉代的理政者,往往都有着深厚的儒学素养,但他们的理政思路,则不局限于孔孟的理念。
正如帕森斯所描述的规范秩序一样,社会个体对社会有着一致性理解,通过个体的自我内化,这种规范秩序实际上得以形成。当社会个体按照秩序规范所规定的规则行动时,社会中稳定的事实秩序就产生了。而作为解释话语的儒家体系事实上影响到了整个国家,无数个体不自觉地开始遵从其中的理论,因此在汉武帝后,儒家的治理理论也在事实上开始由表及里、由虚而实地具体影响政治实践了。
由文饰、文教到文法:理政思想儒家化的发展
正如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指出的,董仲舒所谓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理论,所指的重点是在官办教育、学校制度上。董仲舒的主张与秦始皇焚书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董仲舒并未禁止百家之学在社会上的推广与传播。虽然儒家的理论在汉朝帝王的重视下得以推广,但其余各家的思想并未完全被禁止与摒弃,同时,儒家思想的一家独大地位是由汉朝帝王推广而形成的,这就使得推广开来的儒家思想实质上是经过了汉朝帝王筛选的。
由于汉朝儒家并非以学理而是以权力得以占据思想界的独尊地位,因此汉朝的政治理念依然秉持着汉初以功业为依据的治理方式。在实际的政治理念中,儒家的思想与理念只是被部分使用,总体来看汉代的政治理念依然持“以霸王道杂之”的特点,这种特点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更为明显,像曹操、诸葛亮等人直接宣传和使用申韩之术来进行政治治理。汉朝的治理思想中儒家理念更多起到一个解释与说明的作用,即带有明显的“文饰”特点。同时,为了加强儒家理论的威信,武帝以及之后的帝王纷纷推进了儒家经典教育,这也客观上支持了儒家重视文教的观点,因此,武帝以后的政治理念,虽然在表面上与儒家的理论相契合,但实质上仍是以实践与历史经验为依据的。
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武帝曰:‘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虽然,武帝之能及此也,故昭帝、霍光承之,可以布宽大之政,而无改道之嫌。”在理政思想上,儒家学者确实对自身理论进行了一些修正,用以配合当时的政治需求,而之后的汉政依然体现了“以霸王道杂之”的特点。但正如帕森斯分析的,单位行动深受目的、手段、条件和指导性原则的影响,在具体的行动过程中,个人对于确定目标以及选择达成目标的方法具有自由性,但个人也会不自觉地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在社会文化影响下,行动者会形成一套符合社会文化的道德性规范,并不自觉地利用它来指导具体行动。儒家宽仁之道渐渐深入人心,虽然这种理念在早期更多地被帝王当成提供合法性理据的工具,被门阀贵族视为维系家族的根基,被寒门视为鱼跃龙门的工具,但随着时间的深化以及时代儒学家的思考与发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自觉地使用儒家的理念来指导自身的行动。国家统治者同样如此,后世的赵宋帝王出于对立国根基不稳固的审慎,对文教系统持一个温和宽容的态度,对礼乐、典章、律法等规范也持敬重依靠的态度。因此,相较于汉唐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忽视成文规范的“嚣陵噬搏”风气,赵宋帝王给予了规范化的制度和律法以更大的尊重,儒家的治理理念在宋朝实现了由虚到实的突破性发展。在宋之前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的治理理念实质上吸收了原属于法家的一系列治理手段,形成了文法性质的治理理论,具体表现为兼顾宽猛之治,将原属于法家“严刑苛法”的理论手段加以儒家化发展,归入猛治之中,正因如此,可以发现宋朝“绳墨”“文法”等词出现得相当频繁,儒家理念成为国家治理理念的结果,影响的并不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卓有成效的一些法家的措施,而是帝王、权贵出于个人私欲的一种肆无忌惮的行为。儒家理论对于纲常伦理的重视,在实际上制约了帝王权贵的出格行为。
如赵鼎新所言,汉朝在建国初期采用的治国理念是黄老思想,但黄老思想更多的是一种治理术,重视历史经验的黄老思想可以为具体统治提供措施,却不能为整个国家治理理论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此汉武帝在诏贤良文学策中提道:“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试图寻找一种官方话语解释理论,而董仲舒的儒学理论在这种情况下被选中,并且在后期这种“官方儒学”经过了多次的改造以及圣典化,最终形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理论中,重视历史经验的黄老学说,以及有着详细方法论的法家学说的观点,依然受到极大重视。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这些方法往往是以儒家理论得以解释和说明的,由此,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开始具有“儒法帝国”的特征。但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晚年是汉朝风向转向过度的一个时期,之后的汉王朝虽然可以称为“外儒内法”,但实际上这个“内法”与法家严刑苛法的理论已然不一致,为了契合解释它的儒家学说,汉朝具体的国家治理理念在实质上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儒家化处理,并且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与影响,事实上有更多的人接受并且不再仅仅将儒家理论当作一个工具,譬如在东汉末年已有儒学礼法之士对于当时流行的清流士大夫风气进行批判,又在三国时期,司马家族的司马孚在曹芳去世时“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总而言之,汉武帝之后中国“儒法帝国”的重要特点即为国家治理理念越来越符合儒家理念,毕竟当政治实践的结果能够利用儒家理论来进行解释时,这就意味着其实践理论是可以被儒学体系吸收借鉴的,并且通过吸收借鉴这种实践理论,使得儒家治理理论不再像春秋战国时期一般脱离实际、难以施行,相反具有了极强的现实实践意义。
汉武帝后,寒门儒家在官员(宰相)中的占比提升是功臣集团实力缩小、皇帝权力扩大的结果,反过来又继续压缩了功臣集团的实力,中朝权力提升的本质不是皇帝通过制度变革来加强皇权,而是皇权与相权此消彼长下的自然结果。儒家文化影响了汉朝的治理理论,但并非是春秋儒家的一套理念在政治上得到施用,而是儒家的理念影响了汉朝历代帝王所秉持的实践性政治理念,正如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所探讨的,自武帝朝后,在政治实践中的个体开始兼顾儒生与文吏的双重身份,最终形成了合流,秉持儒家理念的文吏成为了官僚阶层的最主要力量③。
在汉武帝时期以及随后的霍光主政时期,儒家思想在事实上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思想,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而寒门儒生集团也填补了巫蛊之祸中大批去世的军功世家的空缺,成为了汉朝重要的政治群体。但儒家思想在国家治理理论中更多是作为解释性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相应的寒门儒生集团,他们的核心特点也是寒门,儒家理论在当时只是他们晋升的工具,在他们掌权之后,具体的政治实践理念还是跟随统治者的意图而定,并非真正地使用儒家理论来指导政治实践,譬如霍光在盐铁会议后杀死桑弘羊,之后却在实质上依然继承了桑弘羊的一些理政措施,而儒生官员也在实践中得以贯彻。由此可知,武帝晚期以及霍光执政时期,虽然汉朝完成了向守文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非就是以儒家理念来进行指导执政,而是将一些措施适当地进行处理与调整,使其可以利用儒家理念加以解释。儒家理论的这种工具性在君臣间都达成了共识。
但随着这种解释性理论逐渐成为一种影响个体思想的社会文化,许多个体开始不再将儒家理论仅仅当作一个解释性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自觉地尝试利用儒家的理论来指导国家的治理,实际上儒家的政治理念已经影响到了具体的行动者。武帝之后的统治者,已经开始不再严格区分儒家的理论描述是一种证明合法性的话语体系还是一种真实的值得遵循的政治理念。而随着汉末至五代多次的动荡纷乱,许多统治者的实际政治行为和证明政治行动的合法性理论——儒家理念,充分背离,使得人们开始反思一味注重实际经验的理政思路的缺点。到了宋朝,由于开国君主倡导“召和气”与“立纪纲”并举,儒家治理理念开始由文饰、文教向文法方向转变。最终,儒家理政理论成功实现了由虚到实的转变。
注释:
①田余庆认为:“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也就是汉武帝死前二年。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的‘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②徐复观指出:“(董仲舒)的这一意图,与大一统专制政治的趋于成熟,有密切关系。他一方面是在思想、观念上,肯定此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想给此体制以新的内容,新的理想……他赞成禅让和征诛两种政权转移的方式,即是他依然守住‘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
③阎步克认为:“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官僚之间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分化;甚至,在中华帝国创建之始,恰恰就是由那些颇为纯粹的职业官僚构成行政骨干的,学者文人在其时反而颇遭排斥——这就是秦帝国的情况……世入汉代,文吏群体就开始逐渐让位于儒生官僚——兼为学者、官僚的‘士大夫’了。”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797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