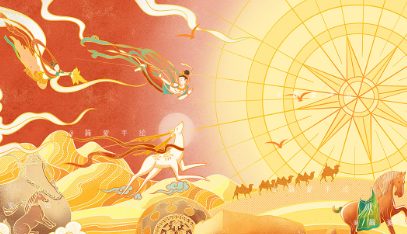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历史上的拓跋鲜卑民族所经历的南迁之路 ,在政治经济上既是草原游牧形态与 中原农耕形态不断 融合的发展之路 , 又是鲜卑汉化不断加深的文化 变迁之路 。 而伴随着拓跋鲜卑 民族的政权转移 ,其残 留的 历史遗迹却也是鲜卑 民族汉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物质文化体现 。本文主要研 究丝绸之路背景下的拓跋鲜卑音 乐“ 汉化”, 不是简单的草原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单向转变 , 而是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 、西域各 民族历史音 乐文化的交织统一 ,具有多向性 ,该时期的音乐考古、 图像材料中都印证着此观点。
【关键词】 丝绸之路,鲜卑汉化,古代音乐文化
季羡林先生曾强调 , 文化一旦产生 , 就必定要发生 交流 。交流是双 向 的 , 交流的双方都获益 。而拓跋鲜卑 民族南迁路径中的文化交流迹象就深刻反映 了此观 点。 从诸多考古材料中可以窥探到拓跋鲜卑民族对于自身文 化倾向的不断调整 , 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及其西域 、 中 原地域文化之间彼此交织统一且最终形成的汉化过程。 而鲜卑人生活价值与行为方式转变下的文化选择倾向也 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音乐彼此交融 、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特征。
一、“盛乐时代” 下的多元音乐文化碰撞
1 世 纪初 , 鲜卑民族自大兴 安岭东北地区进入到 “ 匈奴故地 ”, 而拓跋作为檀石槐鲜卑的远亲 , 南下至雁 门 、云中二郡塞之地的西邻 , 已逐渐具备与西域 、 中亚 地区互通有无 , 交流联系的客观条件 。可 以想象 , 当时的鲜卑民族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依托 ,不断发展壮大 , 日益加强了与西域地区和中原地区音乐文化的联系。
公元 258 年 ,拓跋力微率其部从长川迁于定襄盛乐, 从此逐步开启了拓跋鲜卑从游牧生活向农耕定居生活 的 方式转变 。盛乐时代下的拓跋鲜卑音乐更多凸显着本 民 族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习俗 。其 固有文化 虽与西域地 区、 中原地区文化存在着交流的轨迹 ,但其游牧民族的主体性特征依然存在着。
( 一)汉代壁画中鲜卑文化因素
东汉后期的鲜卑民族在和林格尔地区就存在着文化 交流融合迹象 。1971 年出土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 1 号的东汉壁画墓中 9 幅建鼓百戏 图 , 其生动展现 了 当 时的北方地区游牧民族乌桓 、鲜卑与中原汉族音乐文化 之 间 的交流 。绘于中室东壁的宁城建鼓百戏图 , 自南 门 入 院 中 , 旁侧设有一建鼓 。其百戏 图 的东 、西两侧 的屋 中坐有宾客 ,似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人物形象进入 院 中 。墓主人端坐堂上 。堂下院内有双人倒立 、对舞 、弄丸等百戏乐舞形式 。旁有乐队与之呼应 。游牧 民族人物形象对着墓主人行拜礼 , 周围环立着兵士吏属 。 由此可 见 , 东汉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乌桓 、鲜卑在与中央政权 交往互 市 中 , 存在着接受中原音乐文化浸染的文化环 境 。其墓葬图像中代表汉族音乐文化的吹箫 、埙 , 执桴 击鼓的演奏场面 , 以及西域音乐文化中跳丸 、飞剑 、舞 轮 、戴杆等百戏技艺 ,对于北方草原民族的音乐文化生活有着一定的感染与冲击。
壁画中形象地描绘了墓主人接见乌桓首领 的宏大场 面 ,他们髡头赭衣①。 《后汉书·鲜卑传》 中载“鲜卑者, 亦东胡之支也 , 别依鲜卑 山 , 故 因号焉 。其言语 习俗与 乌桓 同 。唯婚姻先髡头 , 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 , 饮 宴毕 ,然后配合 ”②。髡发这种具有鲜卑民族代表性的发 饰形象在汉族墓葬中出现 , 印证着早在东汉时期鲜卑 民 族就存在着与中央政权交流融合的历史例证 。而在草原 与绿洲丝绸之路文化的双重路径传播影响下 , 其交流融 合的是以西域音乐文化中的杂技百戏 , 与箫 、埙等乐器 为代表的汉族音乐文化 , 同 “ 葬则歌舞相送 ” 的鲜卑原 始歌舞艺术形式三者交织统一 。可 以想象 ,源于鲜卑 民 族生产生活 、情感抒发的鲜卑原始歌舞在东汉就已经开 始与中原与西域音乐文化进行着交流碰撞 , 为 日后其文化倾向的转变奠定基础。
(二) 北魏早期墓葬中文化交融
北魏政权的建立有向东晋夸示自身正统地位的意图 ,在其早期墓葬壁画等物质材料中也能看到北魏统治者在不断接受汉族传统文化过程中 ,对 自身正统地位 的 塑造与建设 。而这样的塑造与建设是鲜卑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 ,更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汇聚过程。
1993 年出土于呼和浩特三道营乡鸡鸣驿村 的一座北 魏贵族墓葬 , 其墓室墙壁上绘有杂技图壁画 。在 内容上 描述了身着红衣白袍与红彩长袍的墓主人夫妇 , 端坐殿 上正在观看 百戏乐舞的场景 。 台 下 5 名或蹲或立的舞 女 , 头扎双髻 、身穿短衣与曳地长裙进行舞蹈 。画面左 侧绘有头戴尖顶黑帽的 5 名杂耍伎人 ,橦倒伎人身着 白 衣 ,跪于地上 ,撑一长杆 , 杆顶撑一男子 , 另有一男子 在杆中部作攀援状 , 左右两侧站有双手张开作保护状 的 艺人 , 后一人手里抛着五个小球 。宫殿台阶以下空地上 一匹黑色鞍马 , 其对面停放着一辆牛车 。整体画面在文 化表象上确是不同民族区域之间文化汇聚 的具体体现。 作为音乐发展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百戏 内容 , 是西 域文化的典型代表 。而台下绘的黑色鞍马是北方游牧 民 族中的文化象征 , 其与以代表着汉族农耕文化的双轮双 辕牛车这个继西汉以来的在魏晋时期逐步成为高贵身份 象征的出行工具③ , 在北魏早期的墓葬壁画中共同构成一幅多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美丽画卷。
“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 … ”④ 盛乐时代下拓跋鲜卑民族所秉承萨满仪式下的原始歌 舞 , 自南迁至我国北方的蒙古高原匈奴故地后始终存在着与中原汉族文化彼此交流的条件 , 加之草原丝绸之路下西域与中亚地区音乐文化的传入 , 都对鲜卑民族在盛 乐地区的原始歌舞文化产生影响 , 其物质材料中展现出 的多 民族 、多区域的文化表征是不同地域文化接触中不断涵化的结果。
二、戎华兼采的“ 平城时代” 音乐
“ 秋七月 ,迁都平城 , 始营宫室 , 建宗庙 , 立社稷 ” “ 典官制 , 立 爵 品 , 定律 吕 , 协音乐 ”, 音乐在政治 中 的 功用被北魏的统治阶级愈加重视 , 为迁都后音乐文化的 繁荣发展提供空间 。 《魏书》 中 言: “太延五年(439 年) 四月, ‘鄯善、龟兹、疏勒、焉耆诸国遣使朝献’。 五 月 ‘ 遮逸国献汗血马 ’。” 大量西域音乐文化伴随着 “ 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 ” 的迁移 , 以及北魏与西域 国家交往的更趋频繁 , 使其西域与中原汉族文化和鲜卑 本民族文化在平城地区汇聚交织 ,共同构成平城时代下多元一体的音乐文化。
( 一)石刻艺术下的簸逻迴乐器
随着拓跋鲜卑民族南迁步伐的日益加快 , 拓跋鲜卑 人在宗教信仰上也从最初的多神崇拜 、载歌载舞的萨满 教向中原汉族的信仰佛教渐进趋同 。而自文成帝起开始 修建的云冈石窟艺术作为承载着多元音乐文化的物质载 体 , 生动展现了拓跋鲜卑民族在平城时期音乐文化之间 的融合发展 , 其雕刻的音乐图像也见证了北魏宫廷音乐与拓跋鲜卑民族不断汉化的历史进程。
第 8 窟 中主室北壁上层列龛中刻有八乐人 ,持排箫、 竖笛、横笛、琵琶、竖箜篌、角等。其中 ,角乐器的出现是北方草原鲜卑民族特质音乐文化的生动反映 。《新唐书》 有言: “金吾所掌有大角 , 即魏之簸逻 回 , 工人谓 之角手 , 以备鼓吹。” ⑤可见 ,在北魏时出现的大角被称 作簸逻迴 , 被用于鼓吹乐中 。而《乐书》 中关于胡角 的 解释: “ 胡角本应胡笳之声 , 通长 鸣 、 中 鸣 , 凡有三 部 …… 亦马上严警用之也 。其大者 , 谓之簸逻迴 , 胡人 用之 , 本所以惊中国马 , 非中华所宜用也。” ⑥可见 , 角 之用途为放牧狩猎的拟声工具 ,在内地角乐器未传入之 前 , 未 闻其声 , 所以才会使内地的马匹听之受惊 , 可 以 想象其声音宏大悠远的特征 , 符合北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
而 “ 后魏之世 , 有《簸逻 回歌》, 其曲多可汗之辞, 皆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不可晓解,盖大角曲也”⑦。 作为代表着北魏鲜卑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簸逻迴歌 , 以其 可汗之辞北虏之音为特色 , 与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音乐 文化 中 的排箫 、筚篥 、横笛一 同汇聚于云冈石窟 的石刻 壁画 中 , 彰显着北魏音乐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 的时代特 征。当下 ,角作为北方草原民族的特色乐器 , 常与铜鼓、 皮鼓合奏 , 也见应用于广西瑶族 、贵州彝族等地集会、 丧事 、宗教法事等民间风俗活动中 。而大 同地 区雁北笙 管乐中存在的龙头号 , 以其类似牛角的弯曲形制和具有 龙头状的凸型 图饰 , 被看作游牧民族角乐器的历史孑遗 , 继续存在于平城地区。
云冈石窟中所展现的手持乐器伎乐石刻是展现北魏 时期不同民族音乐文化交融发展的物质材料 。对 比 《隋 书·音乐志》 中所记录的龟兹乐 、西凉乐等其他乐部乐 器内容的使用情况 ,将石窟中所展现的乐队组合形式看 作是早期传入初期阶段下最为原始的乐队组合形式也未尝不可。
“ 龟兹者 , 起自吕光灭龟兹 …… 后魏平 中原 , 复获 之”“世祖击破赫连昌 ,获古雅乐 ,及平凉州 ,得其伶人、 器服 , 并择而存之 。后通西域 , 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 署。” ⑧北魏以一系列兼并战争的形式 ,徙工匠三万余户 进入平城 , 使其各民族音乐文化汇聚于此 。对于诸如像 “ 其乐具有钟磬 , 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 , 而杂 以羌胡之 声也 ” 的西凉乐等 , 都择而存之 。对于汇聚于平城之下 的各方音乐文化渲染以鲜卑色彩 。这也是多元音乐文化 交融之下 , 鲜卑民族 “ 乐其所生 , 礼不忘本 ”文化选择倾向的真实反映。
(二) 平城墓葬中的多元音乐文化汇聚
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艺术中更多展现 了北魏 中期 的 世俗音乐生活 。其墓葬中出土的壁画 、乐俑 、石雕等都 展现了不同文化因素融合与发展 。北魏文化选择倾向是 伴随着政治中心向中原的转移不断调整的 ,平城地 区墓 葬出土的物质材料彰显着鲜卑民族汉化进程 , 同时 , 也印证着北魏时期不同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繁荣景象。
2020 年在大同平城区发现的七里村北魏墓群 , 其 中 被命名为 M29 的北魏壁画墓中的多幅世俗生活内容体现 了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 、西北民族音乐文 化日趋融合的迹象 。墓室北壁西部残存的部分壁画中绘 有 四名 乐伎 , 自西向东分别手持琴 、长箫 、 琵 琶 或 阮 咸 。头戴着具有浓厚鲜卑民族风格的凹顶垂裙皂帽 。其 服饰以黑红相间交领宽袖长袍与淡红色交领宽袖长袍相 间而坐 , 奏以不同的乐器 , 这样的场景在大同云波里 的 墓葬壁画也可见到 , 可以想象在视觉与听觉上所展现 的 秩序井然 , 极具动感 、对比强烈的感官效果背后 , 或许 体现着鲜卑民族在平城时代下所具备的严格礼制规定,以及程式性的审美取向。
参照《大同七里村北魏墓 M29 壁画墓》 中关于乐伎 手持琵琶或阮咸的说法 ,本文认为可以将其认定为阮咸。 “今清乐奏琵琶 ,俗谓之‘秦汉子’, 圆体修颈而小 ,疑是 弦鼗之遗制。傅玄云: 体圆柄直 ,柱有十二 …… 阮咸 , 亦 秦琵琶也 , 而项长过于今制 , 列十有三柱 。武太后 时, 蜀人蒯朗于古墓中得之 , 晋《竹林七贤 图》 阮咸所弹与 此类 , 因谓之阮咸 ”⑨。 图中弹拨类乐器圆体直柄 ,手持 拨子 , 与云 冈石窟第 6 窟中正室东壁上层伎乐人手持乐器实属相似。
西壁绘以杂技乐舞场景 , 队首一人作 “ 缘橦 ”杂技 状 , 额前顶立一黑色长杆 , 二童伎攀杆于中部和高部, 作单腿撑杆和顶立动作 。后跟有 “ 跳丸掷剑 ”者 以及 中 间 2 人自右向左依次演奏乐器细腰鼓和箜篌 。最后 1 位 乐伎身着淡红色束腰长裙 , 裙摆 白色 , 右手持琵琶状乐 器 , 左手似弹拨 。 百戏作为西域音乐文化的典型代表, 沿袭汉魏旧制进入到北魏宫廷与世俗的音乐生活中 , 与 其他代表着汉族音乐文化的乐器组合在一起 ,共 同繁盛于鲜卑民族统治的“毡帐 ”之下。
(三) 百戏伎乐在平城时代的繁荣
百戏伎乐作为代表着西域文化的音乐 内容 , 在北魏 平城时期的石窟造像 , 以及墓葬壁画乐俑内容中频繁 出 现 。其百戏中缘橦伎乐更是作为这一时期一种特殊 的文 化现象在北魏的音乐文化中大放异彩 。笔者对大 同地 区 出土 的 图像 、乐俑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发现 ,在沙岭北魏 壁画墓 、智家堡北魏墓 、七里村北魏墓 、雁北师 院 M2、 梁拨胡墓 , 以及云冈石窟第 38 窟中均存有缘橦伎乐等百戏内容 , 与其乐器组合共同交织于壁画图像之中。
“ 橦 ”在《说文》 中其解释为 , “橦 , 帐极也 ”, 即为 古代旗杆 。 缘攀 以 为戏 , 是对其艺术形态的基本描述 。而明代方以智在其 《通雅》 中讲到 的 “ 立竿三丈, 缘其顶 , 舒臂按竿 , 通体空立者 ; 移时也 , 受竿以腹, 而项 、手 、足张 , 轮转 ; 移时也 , 衔竿 , 身平横空 , 如 地之伏 , 手不握 , 足无垂也 ; 背竿髁夹之 , 则合其掌, 拜起于空者 ,数也 ,盖倒身忽下 ,如飞鸟堕”, 这些对其 表演场面的细致描绘 , 也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缘橦伎乐人 的高超技艺 。而这样高超技艺与之丰富的乐器组合两相 配合下形成的热烈景观自然成为北魏宫廷民间竞相追捧的艺术形式。
乐舞百戏题材作为西域文化中的代表 , 在平城时期 的音乐图像内容中尤为繁盛 ,在其北魏的墓葬壁画 、石 刻、石窟造像中都能寻觅它的踪迹。 《魏书·乐志》 中有载: “六年冬 ,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 ,造五兵 …… 缘 橦 、跳丸 、五案 以备百戏。” ⑩究其原 因 , 就在于北魏时 期自道武帝以来 , 其音乐制度上面临着 “ 旧工更尽 , 声 曲多亡 ” 的局面 , 草原民族的固有音乐文化也难以全面 支撑北魏的礼乐制度建设 , 于此将百戏内容补充于北魏 的 乐制体系 中 , 极大地促进了它在宫廷与民间中的发 展 。而图像中所描绘的百戏内容也真实反映了当时平城时期各阶层对于百戏这种西域文化的喜爱。
墓葬壁画和石窟图像中有出现 “ 凡有百戏 , 必有缘 橦伎 ”现 象 , 笔者认 为 , 是缘于墓主人对于缘橦伎向 往 。作为当时现实社会中竞相追捧的享乐形式 ,将其刻 画于墓葬的壁画之中 , 象征着主人在其彼岸世界依旧可 以继续享乐 , 充分显示了缘橦伎在当时北魏鲜卑人心目 中 的地位 。而橦倒伎作为缘橦伎在佛经中的别称 , 在 《妙法莲华经会义》 中有载: “乾闼婆此云嗅香 , 以香为 食 , 亦云香阴 ,其身出香。此是天帝释俗乐神也。乐者, 幢倒伎也 , 乐音者 ,鼓节弦管也 ;美者 , 幢倒中胜品者,美音者 , 弦管中胜者也。” 可见 ,缘橦伎乐作为世间最为美好 的事物 , 与音乐中至美至盛的鼓节弦管之音相配 合 ,共同雕琢于墓葬与石窟壁画中 , 体现 了生者对于亡 者 的美好祝愿 , 祈愿亡者进入彼岸世界后依旧可以继续享乐。
缘橦伎乐作为百戏中的代表 ,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传 入 , 不断与其他区域音乐文化碰撞融合 ,共 同交织 出平 城时期多元一体的音乐文化格局 。而缘橦伎作为北魏时 期风靡一 时的艺术载体 , 伴随着历史发展 的不 断演变, 至今仍有 “ 闹 阁 ”这样 9 个大人头顶 9 个小孩 的 民 间艺 术形式存在 , 作为缘橦伎乐的历史孑遗存留于平城地 区 中 。 同 时 , 代表着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角抵百戏 内容, 与西域文化中常见忍冬纹共同雕琢于云中故城佛教建筑的 童子瓦当之上 ,反映了佛教文化下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汇 聚融合过程。而角抵百戏这样的艺术形式 ,在明朝以后已 在我国绝迹 ,仍保留至今的日本相扑 ,可以看作是它在丝绸之路东段音乐文化传播下的一种历史衍生形式。
三、“洛阳时代” 下的多元音乐
《魏书》 卷十九 中载: “国家兴 自北土 , 徙居平城, 虽富有四海 , 文轨未一 , 此间用武之地 , 非可文治 , 移 风易俗 ,信为甚难。” 可见 ,要想实现其稳定中原地区统 治的政治理想 , 国都平城已不再满足孝文帝推行 “ 太和 改制 ”所应具备的条件 , 再次的南迁之路势在必行 。太 和十七年(493 年), 拓跋鲜卑迁都洛阳 ,开启了北魏晚期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洛阳时代下的北魏政权是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 的关 键期 , 伴随着 “ 禁胡服 , 断北语 , 立汉姓 ” 的一系列措 施后 ,在音乐上体现的是对于复古中原正统礼乐的不断探索 。礼乐上的重新建构更多凸显的是其符号性特征,其目的在于争夺南北朝文化的正统地位 。观察该时期 的 地上 、地下音乐质料 , 北魏统治阶层的文化选择倾 向清 晰可见 , 其汉化过程同样也是不同区域文化共同交融塑造而成的。
洛阳地 区众多的墓葬内容中 ,其出土的奏乐俑主要集 中于元邵墓、染华墓、杨机墓中。北魏武泰元年(528 年) 元邵墓出土的鼓 吹 乐 组合 中 , 存在伎 乐俑 、骑 马鼓 吹 俑 、击腰鼓俑 多件 。伎乐俑盘髻于顶 , 衣领呈左衽状, 其 中 , 吹箫与抚瑟俑乐器图像完整 。抚瑟俑 , 跽坐 , 身 饰红彩 , 乐器置于双膝之上 。排箫俑 , 头挽高髻 , 衣领 呈左衽状 , 跽坐吹箫 。还有击筒俑 , 双臂高展 , 击左侧 竖置于腿的圆筒响器 。而腰鼓俑 , 头戴风帽 , 身穿左衽 短衫 , 系鼓于腰 。骑马鼓吹俑 , 头顶风帽 , 宽袖左衽, 左持鼙鼓 , 右手呈击鼓状 。该墓葬出土的乐俑手持乐器 形象生动反映了北魏晚期的音乐文化 , 既承继了中原汉 族文化传统 , 又存留着其他地域的音乐文化 , 彼此之 间进行着交融与汇聚的历史过程。
从陶俑整体的组合来看 , 最前部 以镇墓兽为首 , 其 后是武士俑 , 中间部分主要以骑从俑和牛车为主体的鼓 吹乐组合形式 , 后部是手持排箫与瑟的乐俑 、仆俑等相 结合的燕乐组合形式 。整体上是鼓吹乐与燕乐的二元式 结构 , 是西域音乐文化与汉族音乐文化的两相组合 , 反映了墓主人出行与宴飨之礼。
北魏杨机墓出土于洛阳市西南 15 千米的宜阳县丰李 镇马 窑村三道 岭 , 墓中随葬坐乐俑八件 , 均 头 戴平 巾 帻 , 衣领呈左衽状 , 所用乐器中尚存琵琶和节鼓 。其节 鼓整体样态呈螺旋状 , 与南亚地区流行的塔卜拉鼓形制 相似 , 可看作是丝绸之路影响下外来乐器的本土化体 现 。其余乐伎的手持乐器已经佚失 , 根据演奏姿势 , 周 杨 曾在他 的《礼乐文化视角下北魏王朝 的华夏化—— 以 墓葬中具有音乐内容的文物为中心》 中推测其乐器主要是横笛 、排箫 、笙 、觱篥 、 曲项琵琶与竖箜篌 。而洛 阳时代出土乐俑中乐器组合下大角 、吹叶等鲜卑民族乐器 的消失 ,代以汉族传统的排箫 、瑟 、鼙鼓 , 生动反 映 了 洛阳时代下北魏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而左衽这种代表 着草 原 民族文化衣领样式的残留 , 也 暗示着 “ 太和 改 制 ”下的鲜卑汉化某种程度上的不彻底性 。观其洛 阳时 代下的乐器组合形式 , 反映了鲜卑汉化过程中杂糅西域特色的自觉文化选择。
四、结语
立足现有的考古材料 ,对其历史文献进行分析 , 以 北魏政权不断南迁作为历史线索 , 纵观鲜卑音乐的汉化 路径 , 可 以基本得 出: 其一 , 北魏音乐经历了从原始乐 舞— 戎华兼采— 复古崇礼 、剔俗 留雅 的汉化历史递进过 程 。其整体上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是本民族音乐文化不 断与西域文化和汉族音乐文化三者碰撞交融共同构成 的 。其二 , 洛阳时代下墓葬文化中所显现的鲜卑 因素充 分体现了太和改制后鲜卑汉化的不彻底性 , 从历史唯物 主义 的角度 出发 , 两方文化之间发生碰撞 , 其弱势一方 的文化也不会消失得踪迹全无 , 势必会在其历史发展 的 各个阶段下留有痕迹 , 这样的观点也在诸多资料中得到印证。
纵观北魏的发展历史 , 拓跋鲜卑人 民从原始的游牧 民族一步步走 向政治权力的中心 , 是不断吸收外来文 化 、学习中原汉族文化的过程 。北魏政权统一北方 , 走 向强盛 , 是其统治者以其博大的胸怀 ,对外来文化 “ 兼 收并蓄 ,礼不忘本”。 最终走向分裂 , 也是因为在学习的 过程 中 ,对自身本民族的文化不断改造 , 丢失 自我 , 最 终引起社会矛盾 , 而走 向衰败 。历史 的经验告诉人们,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与碰撞 , 必然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 粕的过程 ,但如果只是一味地奉行“拿来主义”, 而丢失掉自身的本民族文化 ,其结果也是不长久的。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746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