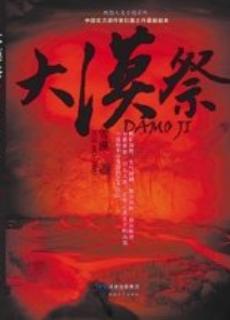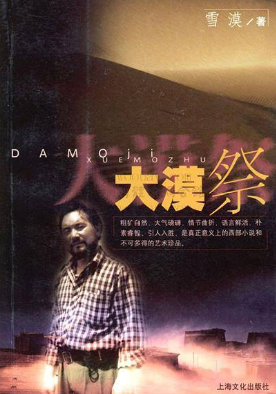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大漠祭》是描述甘肃农民生活的乡土小说。作者雪漠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和修辞手法,语言华丽而极富地方 特色。其英译本由葛浩文夫妇于 2018 年完成出版。基于文学文体学视角, 以葛浩文夫妇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比分析, 本文发现译作在词汇和修辞的层面上对于原作的主题意义、美学效果、文体特征都能较好地再现和传递,也验证了文学文体学 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大漠祭》,文学翻译,文学文体学
《大漠祭》作者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描写西 北乡土生活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出版以来, 雪漠广受关注。《大 漠祭》曾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其英译本 Desert Rites 由葛浩文夫妇完成, 于 2018 年 9 月出版。 作为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葛浩文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推 向世界的重要推手,翻译了萧红、苏童、王朔等人的作品。2012 年,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译者的葛浩文声名鹊起。因此, 《大漠祭》英译本的推出也再次吸引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从不 同角度探讨分析其英译本。
一、文学文体学与文学翻译
申丹认为“文学文体学特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 美学价值为目的的文体学派。它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 注重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 学效果”, “文学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可操作性比较强, 容易掌握, 适合引入翻译学科”[1] 。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一书中 指出,纯语言学的文学翻译研究需要文学文体学方法的补救,这 样既有语言学的分析,又能更透彻地分析作者或译者遣词造句的 美学功能。[2] 文学翻译须让目的语读者感受到原作之美,译文 的遣词造句需要产生对等或者类似的美学效果,因此文学文体学方法也适用于译文文本分析。《大漠祭》充满着“犷悍的民风, 奔放的原始生命力,新奇的地方文化形式”[3] 。小说作者使用了 大量的乡土语言,方言、叠词、比喻、排比、警句层出不穷,新 奇而真实地反映出当地人民的生活状态。此外,作者的人物、景 物描写、修辞句式使用都赋予作品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活的人物 形象。小说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的传递都是建立在作者和译者一 字一句的基础上。笔者从词汇和修辞层面选取例证, 对比分析《大 漠祭》原文和葛浩文英译本,从文学文体学视角出发,探讨葛浩 文对原文文体特征、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的再现和传递。
二、《大漠祭》英译本词汇的翻译
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叠词、俗语、俚语, 是小说的一大特色, 对非方言区的母语读者都会造成理解的障碍。外国译者要传递此 类文体特征,更加考验其功力。
(一)叠词的翻译
叠词,又称“复字”或“重言”。使用叠词,重复了其中 的一个或多个音节,突出了音韵节奏之美,增强了描述的表现力 和感染力。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乡土味叠词,多样而新奇,如“晃势晃势”“侉侉势势”“灵丝丝”“瘆怪怪”等。
例 1:她仿佛不是个实体,而是一团气,一团虚虚幻幻清清 凌凌的气。 [4]
译文: She did not feel solid to him, more like surreal, ephemeral, crisp,clear air. [5]
此句中,作者采用了两个 AABB 式的叠词连用,描写的是主 人公灵官对嫂子莹儿暗生出的情愫,一种内心起了波澜,而又 不敢接受的矛盾感。译文中,“surreal”“ephemeral”表达出 短暂虚幻的不真实感; “crisp”“clear”传递出清楚、真实又 脆弱的倾慕感。四词连用,达意且有一定押韵,可以说译者的 语言保留了部分原作的语言特点,很好地表达了原文主人公的 内心情感。
例 2:姑姑说狼外婆要喝血哩,咕噜咕噜的,像喝山芋米拌 面一样;还吃指头呢,跟吃大豆一模一样,咯嘣咯嘣的。 [4]
译文:Auntie had said that the grandma-wolf drank human blood, gulping it down like slurping potato millet. It also ate human fingers, crunching away like chewing broad beans.[5]
拟声叠词的运用是本书的另一特色,是最生动的动作描写 手法。中英文在深层结构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此类文体特征的 不可译性。译者的创造性,可以在意义和美学效果上弥补这个 不足。例 2 中两个 ABAB 叠词分别描绘了喝和吃的两个动作,而 译文选择的词汇“gulping... down”“slurping”“crunching away”“chewing”将这个两个动作的声音及发生状态描绘得传 神而到位。美中不足的是无法再现拟声叠词的童声童趣。
(二)其他方言词汇的翻译
中国方言众多,各个地区遣词造句各有差异。《大漠祭》 中大量的甘肃凉州方言土语词汇是作品的的魅力之一。用原生态 的文字最真实地反映出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他们的生活, “就像一 壶没有添加任何辅料的陈年老酒, 其醇香自然流出, 不事雕琢”[6]。
例 3:那个挨刀货死要面子,我一和他妈吵架,他就打我, 没轻没重的。 [4]
译文:That no-good husband of mine cared too much about losing face, so he hit me whenever I fought with his mother, and he could be brutal too.[5]
书中对人的称呼变化丰富。“老妖”“老货”“驴撵的”“孙 蛋”等人物之间的称呼反映出浓浓的乡土习俗和村民好恶。与家 畜、身体器官及污秽物相关的,有贬低意涵的称呼,都成了乡民 间嬉笑怒骂的习惯用语。文中的“挨刀货”也是如此, 译文“that no-good husband of mine”是对原文意义的精确解读和准确传递, 少了股狠劲,但也巧妙地传递出女人对丈夫深深的哀怨。
例 4:你细,细了多少年,也没见细下个财把把儿? [4]
译文:You’ve skimped all your life, and for what?I don’t see you getting rich because of it.[5]
小说中的动词使用也极具地方特色,如“务息”(照看、训练), “咋呼”(尖叫) ,“生发”(张罗)等。例 4 句子的动词用了“细”字表现出老父亲极其节约, 舍不得花钱, 甚至苛待自己的形象。
译文“skimp”一词也含有“不足”“克扣”“无法满足正常需要” 之意。可见,译者的语言选择准确地传递出了原文所要表达的 深意。
三、《大漠祭》英译本中修辞的翻译
《大漠祭》中语言极富西北乡土特色和文学美感。作者熟 练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呈现出苍凉粗犷的西北乡村风光,有血 有肉的各色人物和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活动。
(一)比喻
例 5:黄昏的太阳像个大血球,挑在远方的山尖,赐给灵官 一个血淋淋的脊背。 [4]
译文:The evening sun, like a large bloody orb, perched gingerly on the tip of a distant mountain, providing a bleeding backdrop for him.[5]
书中对太阳的着墨颇多。每一次太阳的描写都映衬出故事 的发展和主人公的心境变化。例 5 中,作者采用了明喻的修辞手 法,将太阳比作大血球,暗示故事的悲惨结局。译文中,本体、 喻体、喻词直译,保留了原文修辞之美,而在细微处则体现了葛 浩文对原文主题意义的精准把握。“挑在山尖”译作“perched gingerly”,“gingerly”意为“小心谨慎地”与“tip”相互呼 应。“血淋淋的脊背”则是夕阳照射下的一种背景画面,并非真 正地流血,“backdrop”一词将画面意义很好地传递出来。
(二)拟人
例 6:那个暴戾了大半个天的日头显得精力不济透出惨白的[4]
译文:The sun that had ruthlessly ruled the sky most of the day was now losing its strength, as a paleness seeped in.[5]
小说中干旱贫穷的西北乡村,太阳更多是代表苦难,而不 是光明和希望。作者寓情于景,将太阳拟人化,带来生动的画面 感,也铺垫了故事和人物的结局。译者的译文也保留这种修辞之 美和主题意义。“ruthless ruled the sky”形象地描绘了乡民 对暴戾太阳的感受。
(三)排比与反复
排比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的短语或句子连 用的修辞手法;反复则是同一个词组或句子一再出现。这些修辞 手法既能表现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形式和音律之美,又能增强情 感的表达,强化表达效果。
例 7:走刀路,走绳路,走药路,容易的很。 [4]
译文:We can use a knife, take a rope, or swallow poison,all easy remedies.[5]
例 8:重重重。天在挤,地在压。 [4]
译文:Dense, heavy, weighty. The ground pressed up and the shy pushed down.[5]
例 7 是排比的结构, 汉语三个带“走”的三字结构连用, 增加表达的气势和厚度。在译文中保留同样的美学效果几乎 不可能达成,例 7 的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排比结构,三 个动词词组的使用准确传递了意义,但美学功能和表达效果 有一定的削弱,出现了“假象等值”。申丹指出这种“假象 等值”是看似大致相同,但文学意义和价值相去甚远,是小 说翻译主要问题所在。 [2] 例 8 中出现了反复和对偶并用的手 法。三个“重”字连用,渲染出环境的压迫感。译文并未简 单重复,用三个不同的英语单词阐释同样的“重”字,看似 “假象等值”,但其中的意涵却更深入和立体, 描述的环境、 主题更深刻,相比于简单重复,美学效果并不差,可见译者 的用心和功力。
(四)谐音双关
汉语的同音、近音字词众多,谐音双关使用频率也高。利 用词的同音,使得表达具有隐含意义,既委婉也富有情趣,因此 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汉英语言形式差异巨大,谐音形式的保留 难度极大。
例 9:茄子花、萝卜花,见了谁是谁的话(花)。 [4]
译文: She’s always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or someone to anyone she runs into.[5]
例 10:他妈却说好梦好梦,夜梦双棺,官上加官。公鸡不 鸣母鸡鸣,家中出个好举人。 [4]
译文:But his mother said it was clearly a good dream. Two coffins sounds like two coffers; then hen takes over when the rooster does not crow, and the family fame and fortune will surely grow.[5]
上述两例“花”“话”谐音, “棺”“官”同音。译文无法 完全保留同等效果的谐音双关。译者在意义忠实的基础上,尽可 能地做到了语音修辞美的传递。“something”“someone”“anyone” 押韵, “coffin”和“coffer”“fame”和“fortune”也能做到押韵。 这样的语言选择实现了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的最大平衡。
结语
《大漠祭》中乡民的对话,充满着乡土特色语言。雪漠采 用极富特色的词汇、俗语、谚语,运用丰富的修辞手法,描绘 出 20 世纪 90 年代甘肃凉州腾格里沙漠边缘一个乡村的生活变 迁。成功的译者,不仅要传递出主题意义,也应保留原作的美 学效果和文体特征。从文学文体学的视角分析,葛浩文译本的 语言选择很好地实现了主题意义、美学功能、文体特征的平衡 和传递,这对于今后中国现当代作品的外译有一定的启发和指 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申丹 . 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 [J]. 中国翻译 , 2002.23(01):10-14.
[2] 申丹 . 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 马梅萍 . 关于西北乡土的一种书写———简论雪漠的系列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9(02):78-81.
[4] 雪漠 . 大漠祭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7.
[5] 雪漠 . 大漠祭 [M].Howard Goldblatt,Sylvia Li-chun Lin 译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8.
[6]王素音.《大漠祭》中蕴含的地域文化[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6.30(04):14-17+27.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741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