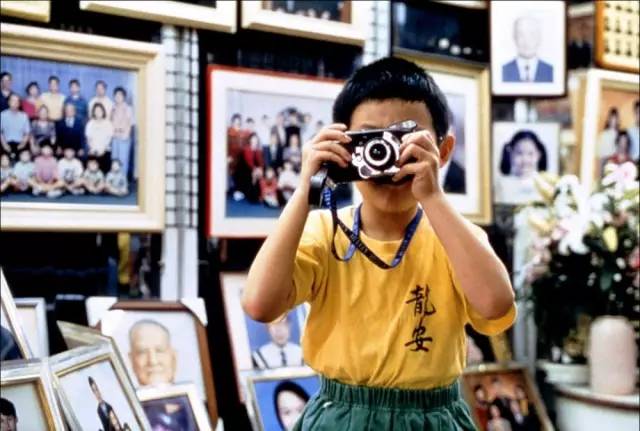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要:近年来,中国电影处于高速跃迁“大时代”,辽宁电影的创作也因此掀起了一场“辽影浪潮”新景象,这是辽宁电影发展中难能可贵的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地域书写为切入点,以此发现电影塑造对辽宁形象发现、表达、深化的种种路径,进而归纳电影塑造、传播辽宁形象的艺术规律和美育启发。
2011年,张猛执导的《钢的琴》一经上映便引发了广泛好评,也掀起了电影创作的一股“辽影浪潮”。地理景观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在实践活动中的产物,与每一个当地人的生活习性、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地理景观的形成表现了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地理景观得以保存和巩固。”对于辽宁电影而言,其特有的文化地理景观,即实现了地域文化的表达,又以“共情”的情感机制将辽宁形象展现给全国的电影观众,实现了艺术上的超越与升华。辽宁电影植根于群众,从独特的“地域”视角出发,在群众、英雄、家国之间书写了辽宁人独有的内心情感与生存境遇,实现了其特有的时代表达。

21世纪以来,辽宁电影的创作数量剧增,呈现出一派繁华之势,但与创作的热浪相恃,有关辽宁电影的研究尚停留在初级阶段,多数学者仍将辽宁电影放置于东北电影的框架之中加以讨论。对于东北电影,张芳瑜曾将其定义为:“东北电影是指以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作主体为核心,根植于东北三省独特的地域环境,创作的反映东北人民的生存状态,具有浓郁东北文化精神的影片。这种文化精神表现为开放包容、多元融合的移民文化精神;粗犷强悍、不息的“铁人”文化精神;自由诙谐、乐观淳朴的喜剧文化精神,以及狭隘保守、懒散懈怠的村社文化精神,揭示出东北电影概念深刻的本质与丰富的内涵”。诚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东北电影的整体界定涵盖了辽宁电影的一些特征。但针对21世纪以来的辽宁电影而言,这种宏观阐述并不能全面地揭示辽宁电影的“新”形象。笔者认为,对于辽宁地域电影概念的研究,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分别是“宏观”体系下的辽宁电影和微观体系下的辽宁电影。著名学者贾磊磊认为:“东北电影不是一个单一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个由空间地域、历史时间、创作主体、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电影概念。”因此,笔者认为宏观下的辽宁电影,应是以辽宁地区的个人、集体和制片厂为创作核心,以辽宁独特的地域环境作为空间文化景观,以群众、英雄、家国为主要表现手段,揭示辽宁地域独有的文化特色、思想观念等的作品,如《雷锋在1959》《钢铁意志》《长津湖》。这类影片将辽宁作为家国形象的一部分,侧重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以此来实现主流价值观的传递;微观下的辽宁电影,是以全国各地的个人、集体、制片厂为创作核心,以辽宁作为故事发生地,展现辽宁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文化精神,如《我和我的家乡之神笔马亮》《东北告别天团》《李诺的梦想》等,这类影片多以多元化的电影创作来实现市场突围,进而形成创作的良性循环。从整体来看,辽宁电影强烈的地域文化,表征着对其研究的迫切需要,因此,只有将辽宁电影从“东北电影”的研究体系下剥离开来,学界方能更好地从“辽影”概念基础上继续电影的研究之路,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一、历史中间人的无言困境
卡西尔将人看作“符号的动物”,认为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人们之所以能对这个世界有独特的认知,是因为符号是人们认知世界的有力工具,通过对符号意义的解读,揭示事物的普遍性原理,人们方能从中找到对知识、文化的意蕴表达。影片《钢的琴》开头长达40秒的镜头内,陈桂林与小菊各自背后的建筑交相辉映,将二人的社会地位与处境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陈桂林平静的话语和背后落魄的工厂含蓄地表达出底层人物的无奈,这种无奈正是20世纪90年代末辽宁工人无法言说之“痛”,这种“对比式”符号表达一方面交代了故事背景,另一方面奠定了影片整体的风格样式,为观众提供了“理性”的认知体验,即对落寞、变革与现实的文化认同。片中的“葬礼”作为视觉符号,纪念的不仅是逝去的老者,还有时代变革下工厂底层人民无言的困境。这种含蓄的现实,在《耳朵大有福》亦有体现,反复地出现写着“周杰伦”的一元纸币,花了出去又找了回来:精准呈现出小人物困顿生活的无尽心酸。此外,《幸福时光》中的老赵用白纸为盲女编织的“未来之梦”,更深层次地刻画出国家现代化变革速度与底层人民认知情况之间的差异。
然而,现实的困境与主题的升华并不背离。《钢的琴》中最重要的符号是陈桂林为挽留女儿而联合众多工友所打造的钢琴。这台钢琴承载着的不仅是跳跃的音符,更包含了以陈桂林为代表的下岗工人对曾经辉煌的工业时代的复杂情感:对于陈桂林来说,钢琴承载着他作为一名父亲最后的尊严;对于汪工来说,钢琴承载着他一辈子的工人阶级情怀;对季哥来说,钢琴承载的是江湖留存的最后一丝兄弟情……令人深思的是,作为21世纪以来辽宁电影中的典范,这类直抵生活真实的作品却往往被冠以“喜剧”之名,其中的人物也因独有的悲喜成为标志性的喜剧而存在,比如:《钢的琴》中的陈桂林;《耳朵大有福》中的王大耳朵;《幸福时光》中的老赵。在类型层面中,这些人物作为辽宁电影深植于全国观众内心的“底层形象”,更成为辽宁电影创作者们以喜剧手段展现悲剧的本质,实现“悲”内“喜”外类型化转变的不二法宝。因而,即使是喜剧片,辽宁的地域电影创作中也呈现出一股强烈的反叛意识,电影的创作者以“悲”作为影片内核,却用“喜”来传递社会的主流价值。这种悲喜的对话与共荣恰好契合了辽宁地域电影日渐强盛的文化表征。
“当一种文化的存在使人们意识到危机时,这种危机会反映到人的情感中,并使人们的文化感情受到强化。”无论是《钢的琴》当中陈桂林面临的离婚风波,还是《耳朵大有福》王大耳朵面临的“再”就业狂潮,他们都在为生活奔波着、矛盾着,追寻着人生的出路。遗憾的是,导演也未能在镜头中替他们找到答案,只能作为历史的中间人,将这些无言的困境深入呈现于电影中,这便构成了辽宁电影在叙事层面的情感逻辑,也是打动观众的最佳途径。
二、群众与英雄的形象书写
(一)平民与英雄的互为转化
自马宁提出“新主流电影”概念以来,各地区基于自身的文化地理景观,创作出了质量较高、口碑较好的影片。随着近年来“新主流”“主旋律”概念的不断生发,辽宁电影亦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赋魅”展现其价值,那便是平民与英雄。在辽宁主流电影中,英雄与群众不是对立的关系,一方也不是另一方的陪衬,英雄是群众的突出代表,群众就是英雄,英雄与群众互相指涉、共生共荣。在这一规则下,英雄与群众互相依靠,种种的共生与互化,书写了辽宁地域本土的“人民传奇”。如以抚顺“雷锋”故事改编,由宁海强指导的《雷锋在1959》;以鞍山郭明义为原型,陈国星指导的影片《郭明义》;以辽中县潘作良故事为原型,宋江波指导的影片《潘作良》等,这些英雄人物形象根植于辽宁群众心中。英雄的伟大之处在于平凡,无论是雷锋、郭明义,还是潘作良,他们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影片《雷锋在1959》中,雷锋在面对党的号召时,毅然决然选择离开家乡来到弓长岭。对于平民出身的雷锋来说,他本可以选择平凡的一生,但他仍用沸腾着的热血践行着对党的诺言。在《潘作良》中,原本农民出身的潘作良从种地人的身份转变为人民英雄,面对县城内上访群众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疑难杂症”,他挺身而出,把辽中县这一上访大县变成著名的“零上访县”。可见,英雄的种种成就,离不开与平民之间身份的平等关系,正是基于这样水乳交融的平等身份,英雄高大的形象方能逐渐走下神坛,与平民身份互为转换,更好地传达导演的艺术主张。
在上文所述的三部影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便是影片始终贯穿着人民的主体地位,强调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的存在才能衬托英雄的伟大。如《潘作良》这部影片中,潘作良始终坚定“群众的利益没小事,百姓的利益比天大。”雷锋日记也有这样的一段话: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一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先进才能移山填海。英雄在完成向群众的转向过程中,也实现了个人理想,这种平民与英雄互为转换的表达方式也为辽宁地域电影的未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战斗英雄的群像塑造与个体表达
2021年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共同执导的影片《长津湖》打开了辽宁电影通向世界的大门,史诗级的战争场面、经典的人物形象代表着我国主旋律电影的最高成就,学者张斌曾说:《长津湖》为中国战争片的类型拓展与美学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作为发生在辽宁丹东鸭绿江边境的地道“辽宁地域电影”,《长津湖》的明星阵容可谓空前豪华,吴京、易洋千玺、胡军等明星加盟,塑造了抗美援朝时期英勇的中国志愿军英雄群像。
自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桥》以来,我国便将中国战争类型片作为塑造“战斗英雄”群像的最佳载体。《上甘岭》(1956)中的女卫生员王兰从家中最胆小的孩子,成长为艰苦斗争、不畏牺牲的女英雄。正是对英雄群像的塑造,将英雄的光辉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英雄的个人形象塑造方面,《长津湖》则相较以往的战争片也有了较大改写。影片不仅表达了解放军战士英勇的一面,还在片中充分展现了他们平凡的一面,“等打完仗,你跟我家一起住,再给你娶个媳妇,生几个孩子,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是无亲无故的雷公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最乐于想象的未来。然而,雷公作为一个老兵,为保护战友,独自驾车冲向敌人。影片则借助他在牺牲前用颤抖的声音哼唱的民谣小调将其立体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有坚守有畏惧的普通人。毕竟,再强大的英雄,在面对死亡时亦会本能地表现出恐惧,但他即便恐惧仍然义无反顾地冲上去,这才是影片通过个性化的英雄想要传递的思想观念。正如影片中七连的神枪手谈子为所说:“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同样,《长津湖》不仅成就了伍万里这一角色,也升华了“爱国”这一主题。
三、艺术与商业的双重突破
自1987年主旋律电影概念被提出以来,我国的电影逐渐由“教育电影”转变为“观赏电影”,20世纪90年代上映的《焦裕碌》《孔繁森》等影片,在叙事上有着较强的“整体化”倾向,常常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以个人事迹为线索,将故事穿插于整部电影之中,通过个人传记式的叙事手法吸引观众,达成其教育目的。随着学者马宁于1999年提出“新主流电影”概念后,我国的主流电影市场便不断发生变革。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殊载体,电影业态不断优化,并聚焦于大众现实展开叙事,以“片段化”的叙事策略彰显中国人民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辽宁电影凭借着东北独有的“乡土气息”,通过对家国情怀这一共同主题的表述,让观众在欢乐中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
(一)创作的多元
2013年“辽宁文艺论坛”探讨了辽宁电影的发展问题,认为辽宁应当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创作激励机制和市场调控机制,组织并鼓励更多的电影人积极投身创作,搭建平台,创造机会,使他们的才华得以施展,形成一股合力,进而推动辽宁电影事业加速进步。以2013年为节点,时至今日,辽宁电影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特征,类型上丰富多样,在保证电影可观赏性的同时,又延续着“影戏”的主流传统,将教化与意识形态融入其中。《我和我的家乡》聚焦于社会民生话题,通过“乡村医保”“旅游扶贫”“乡村支教”“生态治理”“干部扶贫”等一系列社会热点话题,讲述了五个各有特色的故事。以《我和我的家乡之神笔马亮》为例,导演用电影艺术的手段实现了“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宏大主题,采用“片段化”的叙事策略,让观众体会到中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成就。在弘扬了爱党、爱国、爱家的积极思想和人文关照这一前提下,又以多元化的类型风格保证了电影能给观众带来良好的体验,为未来我国主旋律电影实现市场突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除《我和我的家乡之神笔马亮》以外,辽宁喜剧电影成就让人刮目相看:上映于2022年4月的《东北告别天团》电影通过一场不寻常的葬礼展现出人间悲欢:故事的起点是生活不顺的范大明白意外地接下牛硬朗价值300万的丧葬大单,而此后发生的一系列窘迫趣事却传递出感动人心的温情。因而,该片一经上映便备受好评,其脑洞大开的故事走向吸引了众多观众,成为同时期网络电影中的饺饺者;2022年9月30日上映的《钢铁意志》则通过战斗英雄赵铁池这一英雄人物形象再现了中国钢铁事业最辉煌时的宏伟篇章。黄珊编剧的作品《李诺的梦想》从一名年轻拳击运动员的视角,书写了一段努力拼搏的励志人生……可见,辽宁电影制作者善于对传统文本进行颠覆和解构,用技术和艺术等手段重构这一文本的荧幕呈现,让辽宁地域电影得以在故事、节奏、美学等方面带给观众更好的审美体验。
(二)形式的突破
2013年后的辽宁电影发生了巨大转变,其以多样化的题材选择打破了传统辽宁电影钟情于人物传记的传统,并以迎合市场大众为主要目的进行商业化转型。实践证明,辽宁电影的多元化转型是成功的,传统的辽宁地域电影形象逐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积极乐观的精神,展现出辽宁的全新风貌。
汤姆·甘宁认为:“每一个时期的电影也都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建构它的观众。”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里,人们观看电影大多是为了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这当然离不开好莱坞大制作体系对当下时代观众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境下,人们对电影的需求源自于一种不加以思索便能直接获得的快感,也正因此,喜剧电影才能经久不衰地存在于历史舞台上。甚至有人曾预测,喜剧片将会是类型杂糅时代里传统类型电影的终点。辽宁电影借助地域书写,不断寻求着形式上的改写与突破。比如,利用架空的建构形式将影片设置于一个虚构的时空背景下,进而摆脱单一历史事件的局限,开拓题材的更多可能性,如《我和我的家乡》中的《回乡之路》便是一个导演视域下的农村脱贫故事。当邓超站在群众之间时,小朋友的讲话让邓超的人物形象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巨大转变:“老师说,每个人都会被别人改变,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影响别人,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观众在此也领会到脱贫英雄人物的伟大之处。邓超和俞白眉通过类型化的表达,让观众自发地在欢快的故事中找寻扶贫意义真谛;再有徐峥执导的《最后一课》,片中范伟所饰演的国外知名大学教授在晚年痴呆后,心中所想的仍是当年乡村支教的画面,影片结尾,范伟说:“你画的画,老师现在看懂了!”正寓意着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对乡土文化的自发传承。
“乡土情怀”一直是辽宁电影乃至整个东北电影固有的文化气息,薛晋文曾指出:“完整的农村电影叙事应当包括‘经验的叙事’和‘虚构的叙事’两种样态。”经验的叙事应当忠实于现实的本来样貌,真诚而客观地与现实对话交融,根植于鲜活的现实生活和在情感之上完成艺术创作。虚构的叙事则应忠于艺术之美和艺术之善的诉求,对于大多数辽宁电影而言,乡土情怀是其建立的基点,如《我和我的家乡之神笔马亮》正是通过将“经验”与“虚构”加以结合,既忠诚于现实经验,也服务于艺术表达,从而实现叙事层面上的价值突破。当下,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进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辽宁电影尚未从“农村电影”叙事的这一建构中彻底解放出来,辽宁电影仍面对着叙事拖沓、情节老套的种种困境,因此,必须从形式上进行创新,而不仅仅停留于叙事层面,务必要打破辽宁电影给全国观众留下的落后、封闭等固有形象,这正是辽宁电影在叙事层面上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著名编剧董凌山曾说:“坦白讲,辽宁电影的总体质量还有待提高,还缺少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从创作上来看,我们的思想还有些保守,观念不够解放,风格也需要更加多元化,创新能力也有待加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创作力量缺乏整合,编剧、导演、演员大多‘各自为战’”。但不可否认的是,辽宁地域电影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建构出自己的一套“电影模式”,一方面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书写,展现出独属辽宁的历史感伤;另一方面以群众和英雄的合力,呈现出辽宁人独有的人文文化景观;又以多元化的电影书写,紧跟主流电影市场潮流,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电影走出了一条影视的“康庄大道”,后疫情时代,我国正处于电影发展的大好时机,如何有效打破地域壁垒,重构辽宁地域电影形象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参考文献:
[1][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
[2]张芳瑜.中国东北电影研究(1979-2010)[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年.
[3]贾磊磊.中国电影的地缘文化分析——兼论中国电影研究的空间转向[J].当代电影,2020(01):121-125.
[4][德]卡西尔.人论[M].唐译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34.[5]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79.
[6]阎丽杰.论新时期辽宁主流电影的群众英雄观[J].芒种,2014(12):174-175.
[7]张斌.《长津湖》的“纪念碑性”与战争片的新拓展[J].电影新作,2021(05):77-83.
[8]王研.辽宁电影要加速发展必须依靠合力[N].辽宁日报,2013-09-13.
[9][美]汤姆·冈宁.吸引力电影: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J].范倍译.电影艺术,2009(02):61-65.
[10]薛晋文.当代农村电影美学的基本特征[J].当代电影,2014(10):169-173.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585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