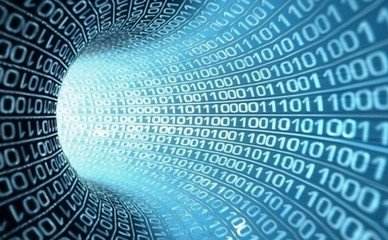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要:大数据为人们提供了优化选择和预测未知的工具。以算法促进的内容精准分发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但技术赋能的乐观主义下不能忽视其对隐私的监视与揭露,对公共话语的挑战与消解,以及对人性的控制与束缚,否则很可能放大数据带来的负面效应。本研究对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批判进行阐释,旨在解开数据所遮蔽的种种弊端,以期波兹曼倡导的教育手段调试数据与用户的关系,使其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数据反思;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
尼尔·波兹曼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创始人,他告诫人们正在处于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强烈批判技术对人性的盘剥。他认为,技术在经历了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后,已经达到技术垄断文化(technopoly)的阶段——“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1]简言之,“人类旧有价值观中的印象、直觉已经被技术话语所舍弃,思维过程也被简化成了计算”。[2]而后果则是人们沦为了数字客体。波兹曼的批判以媒介环境学为轴心,同时触及了批判学派,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他注重探寻因技术作用于社会文化环境所产生的权力集中,这就为延伸其观点至大数据时代去反思数据的负面效应架构了桥梁。
一、数据与技术的偏向
波兹曼对技术的偏向是立足媒介环境学派关于媒介偏向的传统,同时他还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观念。大数据时代,作为科学技术产物的数据通过所谓“科学”的算法去解决社会问题,重构了一套规则体系和知识系统,塑造了新的媒介环境。用波兹曼的观点来看,数据不具备中立性,而是内嵌了操纵技术者的意识。
(一)带有观念偏向的技术
波兹曼继承了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技术观念偏向的传统,如哈罗德·伊尼斯认为媒介具有时空偏向、马歇尔·麦克卢汉转向更加微观的媒介感官偏向论,同时他还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然后他更进一步,认为不同技术有不同的偏向,按照波兹曼的理解,新技术催生了新环境,赋予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新方式——“新技术会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符号: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我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3]
(二)作为唯科学主义偏向的数据
波兹曼认为的从19世纪诞生了一个“计量的世界”。这个世界一切皆可量化,从而提升生活和工作的科学性。这是技术垄断的核心观点,“相信发明的成功必须要遵循以下的所有原理——客观、效率、专长、标准化、计量和进步”。[4]他把这个源头直指奥古斯都·孔德,因为后者认为真实的东西一定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所以波兹曼更加坚定地认为,“技术垄断论缺乏一套明晰的伦理,又拒绝接受传统,却偏要寻求一种权威,它只能在统计学的客观理念里寻找它的源头”。[5]如此一来,人类生存的社会陷入到唯科学主义的境地。在波兹曼看来,唯科学主义是信奉精确,而摒弃真实;相信数字,消除偶然。数据代替了思考,程序代替了对话,科学代替了直觉,从而生成了一种没有情感和道德的权威与秩序。按照波兹曼的逻辑,我们把其延伸至大数据时代,发现数据作为被鼓吹赋能的技术实则内隐的观念偏向就是唯科学主义。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认为,大数据“它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6]也就是说,应该作为人类本性的推测能力交给了数据和算法。当互联网技术能够把我们的饮食喜好、行为习惯、健康状况、风俗信仰、学习进度化作数据,通过算法凸显其潜在价值并转化为效益。例如Facebook公司拥有一款强大的追踪工具Atlas,无论用户使用何种数字设备,其相关痕迹都可以被追踪。还有美国科创公司研制出的Pavelok电击手环,它会根据用户的设定目标释放不同程度的电流以示提醒。作为本能的判断力和知觉被迫让渡,信息的不确定性在被数据量化后的丢失,到底用户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应值得警醒。
作为唯科学主义偏向的数据不仅剥夺了人们的直觉与判断力,还成功了塑造了标准化和一致性。互联网技术催生了个性化,人人都是一部自媒体。但如果深入挖掘,会发现在数据构建的媒介环境只中,用户是在媒介使用层面造就了差异,其可选择不同平台“发声”,编辑不同信息内容进行传播,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反馈。但是在思维方式上,却基本都是靠算法推送的内容去认知世界。用户在网络平台上留下痕迹,其形成的数据则会在算法的帮助下预测其心理状态和行为习惯。所以,“被算法的代码世界挟持,形成冰冷的媒介现实,以及凝固用户认知的受众现实。”[7]所以,这提醒我们,数据不仅构建了当前的媒介环境,更构建了一种控制用户认知的权力,其中充斥着算法偏见。
二、数据与信息批判
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重要旗手,波兹曼信奉媒介建构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口语生成了面对面交流的世界,书写与印刷术建构了语词和逻辑的世界,电子媒介则创造了娱乐的世界。电子媒介催生了技术垄断,导致了信息的意义和价值流失,创造了伪语境,产生了信息超载,强化了信息权威。把其观点延伸至大数据时代,会发现这种恶性循环没有减轻,而是愈演愈烈——数据之争加剧了算法垄断,海量信息资源并没有促进用户获得真正的解放,而是沦陷于无意义信息的汪洋大海中。
(一)无意义信息构建伪语境
波兹曼对布尔斯廷的“伪事件”理念进行扩展,提出了在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塑造了“伪语境”。口语传播时代人们必须运用符合场景的话语进行面对面交流;文字和印刷传播促使人们必须对作者进行创作时的场景进行思考,方能理解其中奥妙。但由电报和摄影术驱动的电子媒介无需对前因后果进行考察,其作用只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8]波兹曼把伪语境塑造的世界成为“躲躲猫的世界”。在该语境中,信息丧失了连续性,形成了一个闭塞和反交流的环境,但和小孩玩的躲躲猫游戏一样,若隐若现产生的娱乐效果让人们并不感到孤独和空虚。波兹曼的论述和沃尔特·李普曼的观点相似,后者提出了“拟态环境”——人们感知超出自身经验之外的事件只能通过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来认知,极容易形成对某一事物的刻板印象。电视塑造的伪语境恰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波兹曼认为“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9]
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看似配合了用户的需要,实则却是毫无关联的信息拼接。基于用户在平台上留下的实时数据,预测其社交、消费、政治、信仰等倾向,从而向其靶向推送,看似为用户节省了搜寻相关信息的时间和气力,实际上产生了平台依赖,沉浸其中却不知已形成了超高黏度。“算法营造了一种高度可信任的逼真环境,因为算法操作所依据的数据本身就是最具说服力的资源,高度拟人化、仿真信息也构筑了各个信任环节,在不经意间看到‘正是我需要的’、‘跟我观点一致’的信息,用户黏性就这样形成了”。[10]
(二)控制机制失灵导致信息超载
波兹曼认为,在前电子时代,信息控制机制的有效运转保证了信息数量与人们所需之间的平衡。在印刷时代,虽然实现了信息的大规模复制,但因读写形成的准入门槛,人们对信息接触和接受力有限。波兹曼列举了法庭、学校、家庭、国家等作为印刷时代典型的信息控制机制,它们共同构成了维护社会文化繁盛的信息免疫系统。电子媒介的普及导致了信息—行动比例失调,信息传播与运输工具分离,人们之间的物理性区隔被打破。简言之,信息的意义不再取决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曾经的信息控制机制失灵。低门槛接触使参差不齐的各类信息大量涌入防线内部,人们在猝不及防中“欣然接受”,选择性机制和纳入—排除机制对电光的酷炫刺激毫无作用。信息超载由此成为技术垄断的一大手段。波兹曼认为“为了应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11]简言之,用技术去管理技术,得到的却是更加严重的信息泛滥。大数据时代,信息接触门槛再次被拉低,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在平台上留下痕迹然后再次被数据找到。信息的控制机制转变为算法,而算法却是传播对数据控制者有利的信息,而忽略用户的真正所需。例如作为传统信息控制机制的学校,如今受到慕课(MOOC)的严峻挑战。慕课将学生处于扁平化的状态,不同国家、地区、人种、信仰的用户都可以实现同时在线接受教育。乐观主义者认为慕课即将取代学校教育成为大众教育的新方式,毕竟无门槛教学可以将知识普及范围最大化。但理性主义者却认为其为商业利益负责而降低了人类的智力。杰里米·诺克斯认为,“运用慕课学习的用户“可以用于改进商业模式和修改教学策略,但不一定对参加学习并签名放弃自己学习数据的众多学习者有利”。[12]从这个角度讲,慕课解决的并不是教育的核心问题——提升用户素养,而是导致信息洪流——淹没其中的用户,使其在无因材施教的情况下随波逐流。
(三)隐形的技术强化信息权威
在对伪语境和信息超载进行批判后,波兹曼探究其根源——到底什么使信息失去了原本的价值而变得毫无意义?他把矛头直指统计学。他认为统计学在19世纪以来成为描绘世界运行的唯一手段。同时他列举历史上对统计学最为滥用的事例是弗朗西斯·高明顿的著作。该人是技术垄断的始作俑者之一,认为只有统计和量化的东西才是真理。他对女孩的形象、厌烦情绪、祷告有效性、智能的遗传性等进行统计,试图科学解释这些研究对象。波兹曼对统计学延伸至人文社科领域极为厌恶。因为它也许并不能揭示事物本源,反而阻碍了真相被挖掘。同时它还塑造了“科学”的假象,让人们误认为数字不会出错,所呈现信息的权威性不容置疑。但是,“技术垄断大肆滥用统计技术,直接导致了统计数字的泛滥及其意义上的不知所云,从而增加了无意义信息的数量,加剧了信息泛滥”。[13]大数据延伸了统计学的效应,以算法揭示事物或事件的相关性。作为大数据时代的隐性技术,算法的不可见性使偏见更加隐蔽。它不像《1984》中“老大哥”那样利用外力对人进行身体规训和思想控制,而是更像是保姆一样利用看似顺从用户的手段去塑造信息权威,让用户无法察觉和无力反抗。可以说,“技术的复杂性使算法偏见的发生十分隐蔽,‘程序设计、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每一个步骤都可能会使偏见悄然嵌入机器代码”。[14]用户对隐匿的算法偏见全然不知,只会在信息接收端等待平台推送,在其构建的权威世界中只关注行事的方式,而忽略行事的原因。再危险一点说,人类不仅会沦为数字客体,甚至数字会打造全新的人类。例如“人脑上传”技术的试验。一位名叫安德斯·桑德伯格的超人主义者早在2008年就开始计划将“人类大脑内容物、精密结构、大脑回路及电信号转移至电脑芯片”。[15]这项计划一旦成功,人脑信息将会被多次复制,人不再担心死亡,因为电脑芯片被移植到人造体中,人会获得“永生”。当数据占领权力和权威的制高点,人再也就无法回到“诗意栖居”的环境,只会在程序设计中束手就擒。
三、运用教育实现数据与人的平衡关系
波兹曼除了媒介环境学学者这一身份外,他还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教育改革的积极倡导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身份,他对技术垄断并不停滞与批判,而是从教育的角度给出解决问题的药方。前文已经提及,学校作为童年迈向成年的中介和印刷时代的信息控制机制,虽然在电子时代受到消解,但波兹曼还是积极倡议恢复学校的传统地位和教育的本能,去唤醒被集体催眠的民众。他的观点在大数据时代依然具有启示,毕竟提升个人教育水平、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等,对抵抗数据带来的负面效应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学校定位要明确
学校是积存、传播人文主义的场所,是构造和运用严肃高尚公共话语的机构。正应为如此,思想的闪光才能助力真理的发现。但如今新媒介进入校园,互联网、多媒体、ipad等数字设备成为教学的主要工具,甚至有取代黑板、粉笔和课本的危险。正如波兹曼的嫡传弟子兰斯·斯特拉特所担忧的那样——“社会却依据数字来运行,没有给质化的、人文主义的评价留下空间”。[16]简言之,人文主义是可以被量化的。如此稍有不慎,学校的定位就会从从思想教育到新技术训练发生转向。学校定位的偏差导致了教学场景对技术的依赖,技术侵入课堂使思想的延伸变为萎缩。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发生,波兹曼认为“学校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给学生提供连贯的意识,培养特定的宗旨、意义和相互关联的意识”。[17]学校定位的明确,重新构建了教育作为恒温器的机制(波兹曼语),抵御技术滥用以破坏人文精神的普及,使大数据变为促进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二)教育传统要回归
在明确学校定位后,波兹曼认为教育不应被新技术牵着鼻子走,应回归其原本的传统——构建宏大叙事。他认为以“人类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主题的叙事,是把育人放在教育的核心位置,以此来设定教育目的和方法,以此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这对于抵抗技术垄断是一剂良药。大数据时代,“计算机程序固然建立基于人工‘语言’,人工语言又依靠字母数字编码和逻辑运算,因而需要一些文化素养,但这样的文化素养是工艺素养,而不是社会素养”。[18]在这样的语境下,新媒体设备进入校园,学校应更为重视技术与人的平衡关系,让教师掌握并提升文化和媒介素养,这样才能应对数据滥用和信息超载,以发挥不同媒介的优势来提高教学水平:以口语实现思想的交流,以书本加深思想的深度,以电子媒介实现思想的可视性,以互联网实现思想关系的连接。这样才能使数据运用到正轨上,使学生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促进技术的发展和人的理性和主体性相得益彰。
(三)课程设置要合理
学校教育要靠合理化的课程设置来实现。面对新技术的冲击,波兹曼建议“在学校课程中开设/强化/改进历史、语言、技术、科学和艺术等科目,将历史观念引入每一门课”。[19]他认为每一门课都要历史化,追溯知识的前因后果,同时增设语义学、科学哲学、技术史、媒介教育、艺术类等课程。但作为理性批判者的波兹曼,并不是对该课程计划进行乐观的研判,因为他承认当前技术发展的势头凶猛。他认为,“或许这个计划有助于开启和维持一种认真的会话,使我们能够和技术思想世界拉开距离,并批评它,修正它”。[20]所以在大数据时代,技术的发展是把双刃剑,算法的优势在于有针对性地对教学资源进行配置,同时根据学生的反馈和痕迹进行再次计算、统计、整合,对资源进行再分配。所以如何发挥其优势并使其不侵害教育的人文性质,应设置关于人文教育、思想教育的相关课程,以及有关科技、技术的发展史课程。如此一来,可以使教师和学生及时规避数据带来的弊端与风险,让技术与人文保持在平衡的状态。
结语
技术发展与传播范式的重构是当前技术哲学和传播学领域的重要课题,技术与人、数据与用户如何保持平衡状态是当前的重要议程。波兹曼对技术垄断的批判,源于现代技术构建了去逻辑性、非连续性、低门槛接触的制度体系和知识系统,以此侵害文化的根基,产生了无道德基础的文化,建立了以技术为核心的社会秩序。把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批判延伸至大数据时代,可以发现数据通过算法提升生产和生活的效率,以及提升思维的科学性,但在技术赋能下如果不思考其负面影响,很容易陷入到被技术奴役的状态。利用波兹曼的观念,揭示数据具有唯科学主义的偏向,以及其构建了伪语境,产生了信息超载,强化了信息权威。按照波兹曼给出的药方,利用教育手段抵制和对抗数据的负面效应,让工具理性与人文主义保持平衡,使数据与用户和谐共生,成为用户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58.
[2]李晓云.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批判[J].新闻界.2009:22.
[3]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9.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363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