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烈日灼心》是悬疑类电影的代表作品,叙事视点的转变作为该片谜题叙事的重要手段的同 时,兼备了叙事修辞的功能。导演通过 说书人视点、全知视点、正反角色主观 视点、监听者视点的来回转换,引导观 众接受导演自身的创作目的,达成了情 节叙事与观众对角色移情的统一。
关键词: 悬疑电影; 《烈日灼心》; 叙事视点转换
叙事视点的转换在悬疑类电影中一 般被用来增加观众理解阻碍、提升影片 接受难度,其在叙事修辞层面的意义则 常被忽略。叙事修辞指的是创作者“(通 过)叙事诱导听众得出修辞者所希望的 结果”[1], 强调的是叙事在完成故事情节 讲述的同时, 也有引导听众(观众)接受 创作者传播目的、价值观立场的功能。 在悬疑类影片中,创作者通过叙事视点 的操控,在完成谜题叙事的同时,也营 造了基于创作者主观目的(如对故事表 达的立场、对角色行为的移情等等)层 面的接受“场域”,从而达到受着意图 与传者读解的合谋。
《烈日灼心》作为此类影片的代表 作品,具有典型性。影片通过全知叙 事、限制性叙事、旁观叙事等多维叙事 手段,不断利用叙事视点控制着观众无 意识的接受创作者的主观表达——从开 篇的刻意间离、到影片中部故意遮蔽、 再到结尾达成受众对角色的移情。观众 在跟随着“电影叙述者”的视点进入故 事、了解故事发展走向、体会作者的主 观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对角色产生了情 感投射。自此, “导演通过叙事实现 (了)对自我和社会“理解”的表达与 分享。” [2]

一、间离:负负得正的非常规主角 切入
旁观者叙事制约和引导着叙事进 程,它通过让观众与故事叙述者、故事 中的人物产生“信息不对等”,形成观 众与故事、人物之间保持原生的“舞台 间离”,从而完成创作者的叙事修辞。
影片《烈日灼心》是以“说书人” 的旁观者叙事视点开篇的。观众跟随着 “说书人”的叙事视点了解故事开端源于 七年前, “三个恶棍”造成一家五口的 灭门惨案。正应了说书人“书说简短” 这四个字, “单式”评书的旁白吸引着 观众快速的建构出故事的戏剧情境:涉 案的三人逃逸七年,摇身一变成正经人 活于人世。
说书人这一视点的存在,构建出与 “听众坐听评书”同样具有“舞台间离 感”的受众体验。这种舞台间离表面上 看,只是叙事手段的一种,其实夹杂着 创作 者的目 的。电 影作为 日常生 活的 梦境化展示,观众对于主人公的设定早 已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模式,善良、 不得志但具有某种“平民英雄”的基因是受众移情的常见基础。而在《烈日灼 心》中,故事的主人公是三个“灭门惨 案”的“始作俑者”,是非常规的主角 设定。创作者明白观众无法在影片开篇 部分对三个带着“原罪”的角色接受和 移情, 因而加入了“说书人”视点——准 确的说应该是带着“道德批判”的说书 人视点。这种夹杂着批判的叙事视点, 在建构基本叙事情境之外,同时还比较 隐秘地完成了创作者对观众的某种“讨 好式”间离:通过对角色行为的批判, 观众变成了相对纯粹的旁观者——不过 是来听个“坏人”的故事——以此减少 了观众对角色的排斥感和接受坏人故事 的负罪感。
而与此同时, 创作者在对角色进行 批判性描述的同时, 画面配置的却是几 个主要角色的“正义行为 ”:作为协 警的辛小丰不顾生死的抓坏人,作为 出租车司机的阿道则一直做着好人好 事。这种讲述与画面的刻意矛盾,其 实是创作者引导观众对“讲述者道德评 判”进行思考和怀疑的某种手段, 它为 几个主人公提供了接近观众的另外一种可能——观众在接受过说书人的道 德评判后, 拉低了对几个主要角色的移 情“期待”, 从而产生某种类似“斯德 哥尔摩效应”的接受心理, 进而更容易 接受画面中所提供的主人公“正义行 为”。受众开始对主要角色产生“负负 得正”的角色评价, 并对主人公产生好 奇与移情。
旁观者视点正是通过这种带着批判 性的道德评价,完成了对观众的诱导和 牵引,表面上的间离其实是另外一种接 近,让观众改变固有的“主角期待”, 接受这样三个非常规的故事角色。
二、遮蔽:立场变化下的谜题叙事
李显杰在《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 例》中提及: “通过对于叙述人的身份 和层次的确认和划分,能够辨认出作者 的意图与风格,故事的重心与指向,观众“视野”及目光所在。”[3] 电影《烈日 灼心》的故事主体采取具有遮蔽性的限 制性叙事,利用不断的转换叙事视点、 镜头视点,模糊主客观叙事边界、模糊 不同角色主观叙事边界等手段,让故事 成为谜题,从而引导观众不断置换自身 立场,以沉浸在不断错位的道德评价和 不断偏离的情节读解中。
观众跟随着说书人的第三人称视点 进入故事后, 《烈日灼心》开始将影片 叙事的重心转移到三人逃亡七年之后, 警察伊谷春和辛小丰三人之间的“猫鼠 游戏”成为故事的叙事主体。自此, 叙事 的视点开始转变为基于“辛小丰”视点 的限制性叙事,从而“强制”着观众以 获取比伊谷春更多的未知信息。“信息 不对等”不仅完成了悬念的构建,同时 引导观众开始接受作者立场——这种引 导其实是基于视点的、基于一种身临其境的移情与投射的。观众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旁观者,而是被拉进影片中“感受”辛小丰作为逃犯的无奈与痛苦。此时的观众变成了缺席的在场,与罪犯的关系转变为某种感同身受的“伙伴”关系。辛小丰为救伊谷春险些丧命、阿道为救伊谷夏受了重伤这些善意的行为与他们为躲避法律制裁而选择逃逸的无奈构成了移情的基础,观众的立场开始确立。
但是有趣的是,在这一段的限制叙事上,创作者很快打破了这种立场,在影片中切入了很多的“他者”视点。房东的监听,其实为观众在接近主人公的同时设置了一道屏障, “亲临现场”的情境被创作者刻意打破,观众得以跳出已然移情的主观立场,进而产生另一种视点的旁观,将移情的主观情绪转变为夹杂着理性的角色评价。在影片中部,创作者又开始不断切入警察伊谷春的视 点,以再次改动观众的价值观立场。
除此之外,影片中还通过很多饶有 趣味的镜头呈现来完成短时的视点转 换,在辛小丰与伊谷春开车同取金鱼的 那场戏中, 两人聊起当年的案子。镜头中 了出现被害一家人被杀前幸福的画面、 辛小丰强奸女孩的画面、女孩吊坠的特 写这些非常规的视点镜头。被害人一家 被杀前幸福的画面很有可能是辛小丰的 主观,而强奸女孩的画面则是客观的、 女孩的吊坠又变成了伊谷春的主观。在 短暂的一场戏中,观众跟随创作者进行 了三次叙事立场的转变。在影片的开篇 部分也有类似的处理,说书人讲述罪案 的过程中所配置的画面同样是不同叙事 视点的,展现女孩洗澡后撩头发的画面 有可能是辛小丰的主观、辛小丰强奸女 孩的画面和三个主人公逃逸的内容是完 全的客观、而不断展现的杀人现场却又 是真正的凶手的主观。创作者通过大量 的不同视点的镜头转换来混淆主观与客 观,夹杂了不同的角色立场,完成对当 年罪案带有主观色彩的讲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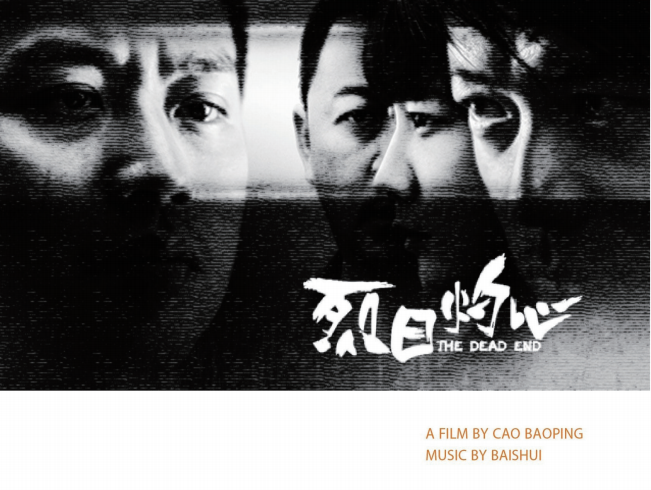
限制性叙事是典型的遮蔽叙事,通 过视点的牵制, 结合开篇的旁观叙事, 创 作者结构出不同的叙事层次,产生沉浸 和间离的不同叙事焦点。利用旁观叙事 视点将观众引入故事其中“隔岸观火”, 利用限制叙事让观众“身临其境”,视 点的不断切换让观众在“隔岸观火”中 “身临其境”。在谜题叙事的情节外衣 下,促使观众在不同的立场下移情、克 制、思考,产生价值观的偏移和摇摆, 构成了受众情感层面的新的谜题。
三、归一:解构多维视点的叙述性 诡计
“叙述性诡计,简称叙诡,是推理 小说中一种常用的创作手段,叙诡通常 由作者在字里行间设置机关,在表达形 式和叙述方式上迷惑读者,以此营造意外性。”[4] 作为一种常见的文本叙事手 段,近年来也常用于电影尤其是悬疑类 电影的叙事中,通过叙事视点的多维选 择、故事信息的刻意遮蔽引导观众错位 理解故事,以强化影片的悬念感,促使 观众产生类似“发现真相”的快感。然 而物极必反,大量悬疑类电影过度使用 叙诡却导致了影片的架空,成为充满臆 想的“编撰”的故事。
《烈日灼心》不同于这类作品。在故 事的主体部分(真正凶犯被抓之前) , 观众对当年案件的真相、人物的身份与 行为、伊谷春的怀疑及探案的经过、甚 至是楼上的监听者都是全知的,并无真 正意义的叙诡设置。正因为全片相对坦 诚的、不绕弯子的创作态度,观众在影 片结尾部分不再对真相抱有好奇——或 者说相信了创作者提供的真相。而有趣 的是,这恰好是作者叙述性诡计的一部 分。
到了影片结尾, 创作者让伊谷春“毫 无技巧”的揭开了事情的真相, 故事文本 的基于“发现真相”层面的讲述像是毫无 保留得展现给观众。甚至为了解构叙事 视点层面对观众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创 作者让伊谷春揭开真相的同事拆解了房 东的监听。在完成叙事层面的解密叙事 的同时,故事主体部分的多维视点也开 始归一, 完全回归全知叙事。相较于限制 性叙事,全知叙事是更加安全的叙事形 式, 加之影片一以贯之的、绕开叙诡的、 相对坦诚的叙事方式,观众放弃了对故 事真相的怀疑,开始对剧中人物——几 个曾经犯错的人的赎罪之旅进行移情。 让观众没有想到的,作者正是用这个全 知的、偏向安全的叙事视点完成了影片 的叙诡。涉案的三人并非真正的杀人者, 杀人者另有其人,不仅如此,三人身上 还负累着善意的普世性美德。自此,沉 浸在移情中的观众在影片结尾部分获得 了“发现真相”的新的快感——几个犯 错的人罪不至死甚至裹挟着某种牺牲。 赎罪之旅的移情和对牺牲的同情两层情 绪被作者巧妙叠加,人性多维的主题至 此达到叙事层面的整体表达。在观众情 绪合谋之后,影片结尾部分创作者又以 陈比觉的纯主观视点的介入,仪式化地带领观众跳海,完成了影片真正意义上 的最终高潮。
叙事视点的适时归一与整个故事的 主体、观众内心对角色的读解是一致的 又是不同的。一致的是移情的达成,不 同的是创作者对角色更丰富的塑造。叙 诡的技巧被刻意磨平,却产生了超越叙 诡本身的力量。
结语
从影片开篇的刻意旁观者叙事,到 影片结尾的完全主观叙事,创作者先通 过批判主角来去掉观众内心的先天排 斥,再通过视点的刻意转换来引导观众 在情节猜想之外进行带着矛盾的价值评 判,最后再通过视点的归一完成最终高 潮段落的主题表达。影片《烈日灼心》 在保留了二元对立的故事格局的同时, 在叙事视点上进行了多维叙事的杂糅。 这种多维叙事视点的运用和转换并非单 纯指向情节本身,而是始终控制和导引 着观众进行价值观的评价、对角色的移 情,是带有目的的叙事修辞。故事开篇 的旁观者叙事、故事主体的多维视点转 换、结尾的视点归一, 不仅营造了动人心 魄的、跌宕起伏的悬疑氛围,还分别从 间离、沉溺、移情等多个层面牵引着观 众情绪,达到叙事与作者表达的统一。 事实证明,多源散乱、有序杂糅的叙事 视点的使用完全可以“(通过)叙事诱 导听众得出修辞者所希望的结果”[5],完 成创作者的叙事目的。
参考文献:
[1][5] 邓 志 勇 . 叙 事 修 辞 批 评: 理论、哲学假定和方法 [J]. 当代修辞 学 ,2012(3):70.
[2] [ 奥 ] 格雷姆·特纳 . 电影作为社 会实践 [M]. 高红岩,译 . 北京 : 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0:95.
[3] 李显杰 . 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例 [M].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225.
[4] 冯斯亮、王止筠 . 聚焦质量 共赢 未来——“第二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 发言摘要 [J]. 当代电影 ,2016(12):23.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1978年, 当年只有20岁的胡宁娜本想报考南京艺... 详细>>
如何设计有效的环境治理政策, 是学术界和政策... 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