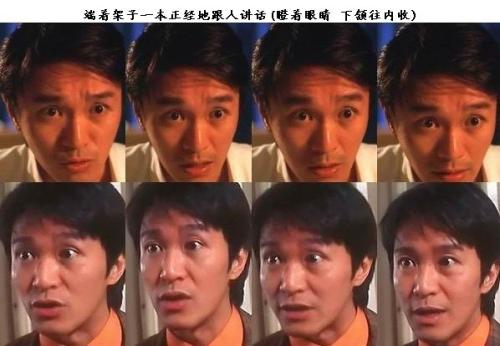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寺山修司是1960年日本新浪潮之后独具个人印记的电影导演。他还是摄影师、先锋剧作家、诗人、文艺评论者……作者的多重身份使他能够打破艺术的边界, 呈现多元的艺术表达。在他的电影中, 经常使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舞台化的表现以及诗歌元素, 在银幕上营造一场瑰丽斑斓的梦境, 呈现亦真亦幻的迷离效果。导演在这些富于个性的镜像中一次次地深入到自己灵魂深处去探寻被隐藏起来的秘密, 表达个人诉求, 形成鲜明的作者风格。
关键词:
寺山修司; 超现实; 女性;
一、电影的多元的艺术表达
寺山修司, 这个光影造梦者惯于游走于现实与梦境之中, 用先锋性的影像表征着电影所具有的梦的特质和诗的意蕴。
(一) 独特的视听语言
1948年, 法国电影评论家阿斯特吕克在《法国银幕》上发表《新先锋派的诞生:摄影机———自来水笔》一文, 提出导演应像作家一样在银幕上写作。如果电影是导演在胶片上写作, 那么电影的视听语言就是这篇文章的词句。而寺山修司不同于大多数导演在胶片上写下哲学思考, 他是一位写诗的导演。
1. 画面。
间离的画面构图:在寺山修司电影中, 经常使用间离的画面构图来展现人物之间的疏离。比如在《死者田园祭》中9:12和10:10出现的构图, 少年与母亲分处于画面角落的两侧, 中间是浓重的阴影, 表现了少年与母亲的间隔, 以凸显他们内心的疏离。少年对母亲说想要割包皮, 这是男孩在遇到喜欢的女人后渴望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青春萌动, 但是母亲并不理解。母亲依然把他当成一个年幼的孩子而制止他一切成人的想法, 认为这是“学坏”的表现。独特的构图揭示了少年不被母亲理解的孤独感。
长镜头与快切结合:寺山修司电影往往并不注重电影的叙事, 而是侧重情绪的传达。导演在电影中经常使用长镜头来呈现完整的电影时空和人物状态, 从而让观众对人物的处境感同身受, 更深入地理解导演在电影中所传达的思想和情绪。另外, 导演在电影中还经常使用快切来组接不同画面, 形成一种突兀的效果, 并配合音乐的使用营造出惊悚恐怖的氛围, 这是导演内心深处对于人物、故乡、回忆的情感外化。
2. 音乐。
在寺山修司电影中, 当人物面临困惑时就会低低地吟唱来抒发内心的迷惘和焦虑, 寻求内心安慰。寺山修司善于运用民族音乐的元素, 将传统的民族艺术与现代前卫艺术相结合, 使两者撞击形成的撕裂与糅合渗入到电影的骨血之中, 配合诡异的画面形成独特的视听表达。在音乐的使用中, 寺山最为人称道的是与日本先锋音乐人J.A.Zaesar的合作。J.A.Zaesar将日本歌演的形式和现代摇滚相结合, 创造出了带有明显地域特征和个人风格的“和风摇滚”。在寺山的授意下, J.A.Zaesar在电影中大量使用古典乐器并掺杂恐怖的咒语独白, 用低沉的和声和反复的曲调制造出强烈的宗教感。[1]而在声效方面, 他们尝试使用短而急促的声效, 与快速剪辑的画面构成惊悚的效果。诡异的音乐与奇怪迷离的声效时时出现于寺山修司电影中, 为其抹上一层瑰丽邪魅的奇幻色彩。
3. 色彩。
寺山修司还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 他对色彩的敏感和对画面的独特品位也融入进电影作品中。他影片中的色彩往往具有叙事和抒情的多种功能, 用外在形象化的色彩来反衬人物内心。如在《死者田园祭》中幻想的部分出现的红衣女子———一袭薄纱, 妖娆妩媚, 正象征着少年萌动的欲望。而当少年路过一群黑衣妇人的围观人群时, 少年看到她们围观的是一间房子里一个女子正在生孩子。导演用黑色预示出女子后来被这群妇人迫害的遭遇, 而少年作为一个在场者见证了这一切。色彩的使用在给观众带来强烈视觉冲击的同时还具有叙事、隐喻的功能, 使影片具有深层的可解读性。另外, 寺山修司电影将事物本身色彩抽离, 而赋予其作者主观化的色彩, 用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随意拼贴夸张地表现色彩撞击所形成的独特意象。在电影12:30时, 赤血月亮高悬空中, 少年在红色和藏蓝色背景的画面中行走, 如同行走在野兽派的绘画中, 狂野的色彩奏出狂放乐章, 如同少年内心迷惘和焦灼下的嘶吼。
滤镜的使用也是寺山修司电影的一大特色, 在电影中滤镜本身经常冲破自身色彩的限制而被导演赋予象征的含义。如《抛掉书本上街去》中愤怒迷茫的青年在萎靡中吸食毒品, 烧毁旗帜……电影以两种不同的色彩传递出人物内心迥异的情感:紫色是梦想中的乌托邦世界, 那里自由而美好;绿色则是充满着禁锢和压迫的现实世界。[2]导演以两种具有强烈对比度的色彩来隐喻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异, 让观众真实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煎熬和绝望。而在短片《疱疮谭》中使用滤镜的同时还大量地使用曝光, 这一手法在巧妙转场的同时使影片带有虚幻迷离的气质。而《死者田园祭》中马戏团的七彩滤镜则是少年成长的出口, 暗示着回忆的斑斓和不真实性。
(二) 舞台剧的表现形式
寺山修司有着长时间的先锋剧作家的经历。多元的文化背景使导演能够实现作品的多维艺术构建。他将独特的先锋话剧引入到电影中, 戏剧的写意与电影的创造性影像结合, 呈现亦真亦幻的如梦气质。如《草迷宫》中, 他将少年秋的欲望与挣扎物化, 借助五位黑衣白面的演员来表现, 这是典型的舞台剧呈现。此外, 寺山修司的电影还具有空间的假定性特征。《死者田园祭》试图打破空间的限制, 当房屋中的母亲掀开门板即是另一个世界———父亲埋葬的恐山。导演在解构原有空间的同时还在电影中呈现“一花一世界”的宗教禅意。《疱疮谭》中人物随身抬着一扇门行走, 并通过这扇门穿越不同时空。在《抛掉书本上街去》中, 寺山将时空关系破坏得最为彻底, 他在影片最后打破了电影的“第四堵墙”, 让演员与观众直接对话, 在沟通电影中的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同时, 让观众进入银幕中去, 产生“体验式”的电影快感。
(三) 诗歌元素的融入
寺山修司电影中随处可见诗歌的元素。如《死者田园祭》中“我们这儿有木匠街、庙街、米街、佛教街, 但是, 小鸟, 这里不是有条可以买老母亲的街吗”;“在这个小女孩松散的头发中间, 有花语拼出的葬礼二字”, 此时一支红色玫瑰坠入黑暗之中的意象化镜头一闪而过, 应和了“葬礼”与“花语”的言说:“就在我埋下亡母曾用过的红木梳时, 只听见风声从恐山上呼啸而过。”这些作为旁白读出的诗句和俳句充满了意境, 配合影片的梦幻画面, 在叙事的同时增加了影片的意味, 使寺山修司的电影独具一种诗化的韵律之美。
此外, 其电影在画面的构成形式上也处处体现着诗意。麦茨认为电影是“想象的能指”[3], 作为一种表意系统, 是有关结构以及结构的构成艺术, 根据电影的“内涵”和“外延”来传达多种可能性, 如象征、隐喻等。在寺山修司的电影中, 我们经常能看到田园、草地、雪山、废弃的铁路、泛起涟漪的湖面、淅沥的小雨和钢琴交织在一起。他电影里的风景绝对不是“表达的零度”, 正如中国元代散曲家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将种种意象组合连接来表达一种情绪。是迷乱, 还是伤感, 都是基于具体的影像形成的表意。
二、“追寻”与“逃离”的命题
寺山修司同费里尼一样, 电影往往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导演通过在电影中营造梦幻的氛围, 以银幕为媒介穿越回自己的过去, 从而完成对自己童年的重新建构和解构。而在寺山修司电影中通过对女性形象 (及其衍化) 的追寻和逃离, 以表达作者对于母亲、故乡、祖国的情感诉求。
(一) 母亲
寺山修司生于1935年12月10日, 卒于1983年5月4日, 在寺山修司短短42年生命里, 母亲是陪伴他最久的人。寺山从小便被母亲约束, 长大后母亲又干预他的婚姻, 最终导致他婚姻破裂。最后寺山便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直到她去世。特殊的经历致使他对母亲的眷恋与反叛这一复杂情感成为寺山修司创作的一大主题。
寺山的戏剧作品《毛皮玛丽》和《身毒丸》曾涉及畸形母子关系的表述, 《死者田园祭》讲述的是少年的成长和对母亲的逃离, 而在《草迷宫》中对母亲的追寻则贯穿全片。寺山的这些作品脸谱化地呈现着母亲的形象, 她们一面是柔弱的, 具有女性的特质, 另一面又是强势的, 对儿子充满了控制欲。儿子面对强势的母亲既有依赖又渴望逃离。而儿子正是在这种挣扎与抗争中得以实现自我的成长与独立。正如《恐怖的力量》所揭示的“贱斥”:这种抗拒, 始自于对母体的抗拒, 若不离开母体, 主体永远不会发生[4]。我们就在贱斥中不断创造自我, 只是这一过程过于痛苦且无休无止。电影中儿子对母亲的感情由一体性的认知发展成分裂性的把握, 只有在不断的反复中, 儿子才能确立自我的主体性, 这种残缺的主体性巩固于反抗母亲的过程之中。[1]
在《死者田园祭》中, 寺山修司企图穿越影像回到过去杀死自己三代之前的母亲。而当电影中二十年后的“我”真正回到故乡和过去时, 面对母亲他却未能下手。电影的结局是成年的“我”与“过去”的母亲相对而坐, 默默吃饭, 这似乎是一种和解, 作者通过影像实现了自我修复。
(二) 故乡
寺山修司对于母亲的眷恋和逃离的情感也延伸到对故乡———青森的感情之中。寺山修司生于日本青森县弘前市绀屋町, 后举家搬到八户市, 父亲参战后母亲带着寺山又搬回青森市, 19岁时寺山离开家乡前往东京读大学。几次循环往复, 最终寺山还是远离了家乡。然而对于故乡, 寺山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深切的怀念, 他甚至戏称自己是出生于飞驰着的火车中。这虽然是寺山对自己的戏谑, 但却印证着作者对家族血缘憎恨的隐秘心理。
而然, 他的作品出卖了他。在寺山修司电影中, 对“精神故乡”的追寻一直是其电影的一贯命题。如《草迷宫》中, 少年秋循着母亲留下的一首《手球歌》来寻找关于母亲的蛛丝马迹。影片最后:“那个戴着新娘发饰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白云是我的向导, 穿越海洋、山脉,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都是为了寻找一种意义。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渴望听到手球歌, 我将继续行走。”寺山修司一直在寻找自己灵魂的家园, 在出逃故乡后, 他拍出这部改编自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再见箱舟》, 实则是写给故乡青森的一首缅怀的挽歌。
(三) 祖国
在寺山修司的电影中, 母亲暗合着故乡的隐喻, 而由母亲延伸出来的完整的女性形象在寺山修司电影中则是对祖国———日本的影射。在《抛掉书本上街去》中, 少年对差点强暴自己的妓女、不通人情而自欺欺人的奶奶、软弱而随波逐流的妹妹发出了呐喊。在《死者田园祭》中, 少年被少妇强暴从而获得“手表”, 暗示少年被迫长大成人。但是影片结尾, 镜头从荒蛮的故乡恐山跌进现代的东京街头, 暗示寺山修司木然接受着时代的种种变迁, 他本停留在“幼年”却被时代所“催熟”。在《上海异人娼馆》中, 少年对妓女O炙热爱慕并为她付出了生命, 最终唤醒了O自我意识的觉醒。寺山遗作《再见箱舟》则是寺山对之前的种种情感做了“纪念性”的回顾。电影中的少妇、妓女、母亲……这些女性形象从各个方面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日本。
寺山修司对于母亲、故乡以及祖国的“逃离”与“追寻”的矛盾复杂心理, 化为电影中浓得化不开的忧伤情绪。他的控诉、他的反叛, 实则是一种赤裸而真挚的热爱的辗转表达。寺山企图在电影中重新构建自己的故乡并杀死母亲纾解自己内心的愤怒和忧伤, 但最终又亲手将自己在电影中构建出的幻境打破, 实现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母亲”的和解。
寺山修司以超凡的想象, 诡异的东方美学以及炽烈的情感, 给观众带来了如同坠入梦境般的斑斓体验。他的电影诡异妖冶的气质、多元的艺术表达以及深入自身灵魂所形成的主题内涵都深深震撼着他的观众。即使在寺山修司逝世35年之久的今天, 他的电影依然具有艺术的先锋性, 并以其深沉的思想吸引着他的追随者。就像寺山修司对大海的迷恋一样, 他的电影也如大海般神秘而深邃。
参考文献:
[1]海带岛.局外人的背叛——寺山修司实验戏剧的时代身份[J].艺术世界, 2015, (05) :23-24.
[2]蒋建兵.诗歌, 符号, 隐喻——从修辞的角度看寺山修司的实验电影[J].大众文艺, 2015, (11) :163.
[3][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C].王志敏, 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36.
[4][法]茱莉亚·克莉斯蒂娃.恐怖的力量[C].彭仁郁, 译.台北:桂冠出版社.2003:11.
《寺山修司电影基于梦幻之上的多元表达》附论文PDF版下载:
http://www.lunwensci.com/uploadfile/2018/0810/20180810031947478.pdf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wenxuelunwen/4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