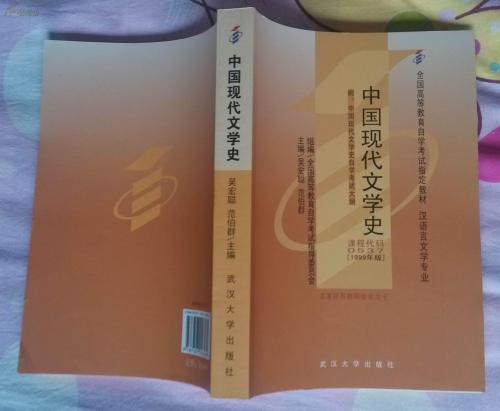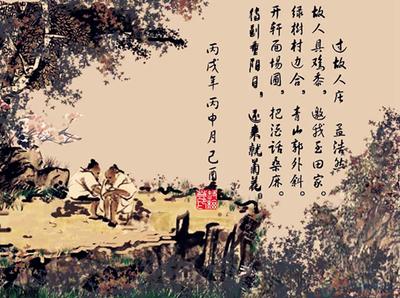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作为文学史的核心要素之一, “分期”问题受到关注。“分期”讨论是对既已成型“历史”的反思与质疑, 主要源自当下历史处理的需要。“分期”在“十七年”成为人文学科的显要问题, 史学界、文学界同时展开讨论。从文学史来说, “十七年”“分期”讨论直接导致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诞生, 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十七年”“现代文学”分期为考察对象, 既探讨作为整体的“现代文学”如何确立自己的时间概念, 也考察其内部时间段落的划分。当“现代”作为一个整体性时间概念时, 与它并置的是“古代”“近代”“当代”等时间概念, 它们之间的变化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学科角度看, “现代文学”经历了一个从重视分期到从现代往前回溯性研究的过程。在“分期”问题上互为参照, 反映出学科间权力的博弈与渗透关系, 因此无论是整体把握还是细部厘清, 考察“十七年”时期“现代文学”分期讨论, 都具有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 古代文学; 近代文学; 古史分期;
Observa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Litera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iodization Discussion of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Tang Lei
“分期”在20世纪50年代的新 (现代) 文学史 (1) 中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并不是特例;此时期, 古代文学领域也正在“文学标准”和“历史标准”的艰难抉择中进行分期探讨。1949年以前, 不可能有一本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史, 分期问题无从说起;即便在看似“完结”的古代文学领域, 分期也是相对自由的, 有些史家按照自己的文学史观做分期, 有些则是出于教学需要简单划分, 更多是按朝代更替自然划分。何以在1949年后, 分期成为具有绝对意义的问题?作为文学和历史的交叉地带, 文学史对于“分期”的重视, 恐怕少不了史学界的影响带动。彼时, 史学界正在进行被誉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古史分期”大讨论。20世纪50年代初期, 郭沫若根据殷墟考古发掘材料, 提出“古史分期”问题, 迅速引起热议。所谓古史分期主要探讨的是“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早在20世纪20年代爆发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 郭沫若就率先提出了这一问题。其时, 各派学者争论着历史问题, 指向的却是中国的现状, 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同样的, 50年代的“古史分期”讨论虽然看上去观点众多, 但也不是简单的学术研究。随着讨论展开, 各方争执不下, 有研究者向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请中央决定谁对谁错。陆定一觉得学术问题应该由历史学家自己决定, 1956年在颐年堂开会时, 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和自己的意见, 这次会议上, 便据此形成了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 (2) 。作为文化政策形成的重要契机, “古史分期”的热度在“十七年”里居高不下, 本来这场学术讨论从1952年开始, 到1956年下半年已逐渐“散热”。然而“双百方针”号召在前, 郭沫若充当“推手”, 连发数文, 迅速扭转情势, 重新将讨论推向顶峰。从1956年7月开始到1957年上半年, 《人民日报》多次发文报道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史学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鼎盛态势。今天来看这场“争鸣”, 各家观点并无本质区别, 均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的“经典”论述及《联共 (布) 党史》关于五种社会发展形态的论述为基础, 不少讨论是为了配合“双百方针”的推行而展开争鸣。此时在教育部颁布的历史教学大纲中, 已明确规定按照五种生产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 结束了1956年之前“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期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期并存”的多样化局面,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法成为唯一的标准。不仅如此,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以郭沫若等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说成为官方的主流标准, 其他各派虽存在, 只是非主流的学术观点 (3) 。表面上争鸣不已, 但实际工作中, 大家都自觉遵守主流观点。1961年北大历史系接受“文科教材会议”委托, 撰写《中国史纲要》, 作为主编的翦伯赞在古史分期问题上, 认为作为学术问题, 理应百家争鸣;但编写教材, 还是使用统一表述为好, 打算采用郭沫若的观点。后来还是陆定一鼓励翦伯赞, 既然他做主编, 就可以按自己素来主张的“西周封建论”来写 (4) 。由此可见, “分期”之所以在1949年后成为显要问题, 不纯粹因其学术价值主导;而分歧众多也并不意味着学理上的“争鸣”真正展开。“古史分期”问题的提出, 无疑会给文学研究以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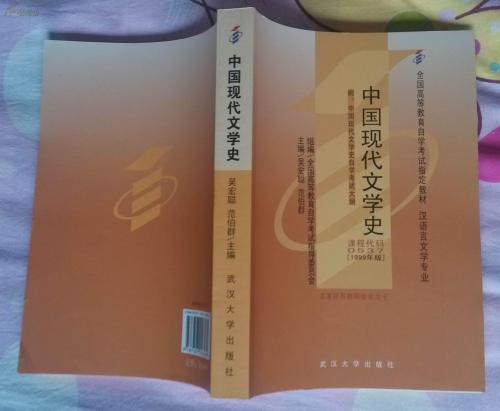
“十七年”新文学史研究中“分期”问题的凸显, 除了史学界的带动作用, 学科内也早有示范,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17—1927) 》 (下称《大系》) 的断限就是一次经典操作。《大系》最初在起讫年限上存在分歧, 阿英主张时间“从五四到五卅”, 前后差不多九年, 作为文学革命期;郑振铎不同意阿英的说法;最后赵家璧请茅盾定夺, 茅盾表示“五四”和“五卅”不过表示了里程碑作用, 看似热闹, 而严格算来这六年间实际作品并不多, 不如定为“五四”到“北伐”, 并且很多重要作品在“五四”之前也已经出现了, 所以从1917到1927, 十年断代是没有毛病的 (5) 。仅从时间上来看, 阿英的“九年”和茅盾的“十年”相差不远, 但相比阿英的“文学革命期”, 茅盾的“十年”断限却得到编者的一致首肯。是因为它既依据中国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来划分时段, 又避免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倾向, 表述上也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和接受习惯, “尤为关键的是, ‘第一个十年’长短适中———太短则无法充分显示新文学的‘实绩’, 太长则难以从整体上加以把握, 作为一段‘始源’式的业已结束却又尚待阐明的特殊的历史时空, 为立于当下的历史叙述创造了广阔的话语空间, 它不仅包含着‘新文学发生’的全部秘密, 而且构成了‘新文学发展’的基本起点, 同时也上升为衡量‘新文学前途’的价值标准” (6) 。《大系》的编纂首先源自众编者希望将这段时空“历史化”处理的共同愿望, 这是差异得以共生的基础, 通过在不同政见、文学观念间恒定地把握现代性的价值立场, 在文学史进程中断裂出一段时空, 赋予它“经典性”的合法地位, 并使之自然化, 具有可复制性。保持“中立”的政治立场, 尽可能广泛地囊括文学发展流变的过程, 不以重大政治事件本身作为分期的标准, 甚至有意淡化, 因此, “第一个十年”比“‘五四’到‘五卅’”的说法表现出更小的功利性, 更容易被接受。《大系》的处理无疑是一种成功的示范, 它说明了完全可以通过对时间的控制使历史“经典化”。
一在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交叉中考察“现代文学”的时间定位
“现代文学”是如何被确定的, 首先需要将其放置在更大的时空中考察。1949年后, 同现代文学一起进入历史新阶段的还有终结的“古代”、暧昧不明的“近代”。此时期, 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都以五四以来新文学为最高准则改写自己的历史, 改写的一种就是在时间上与现代文学接续, 比如“中国文学史”这个概念的变化。原则上来说, “中国文学史”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囊括“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各阶段。在五四新文学发生的当时, 现代文学还只能是“附骥”式的出现在古代、近代文学史的后面, 无法形成独立体系, 当时不少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就都包括了新文学部分, 像陆侃如、冯沅君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编》。随着1949年后现代文学学科建立, “现代文学”逐渐从“中国文学”中脱离, “中国文学史”约定俗成地等同于“古代文学史”, 另一批新的研究者正积极为现代文学作史。尽管已经形成了清晰的学科观念, 仍有一小部分研究者将“现代”部分放进了“中国文学史”的整体中,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和研究员曹道衡都有相关论述 (7) 。将“现代”融入“中国文学史”, 首先和文学研究所的定位与任务有关, 作为国家级文学研究机构, 文学研究所打算编写一套权威的中国文学史, 涵盖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当时所里负责实际工作的副所长何其芳表示, “我之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学史, 最初的出发点倒是为了现在的” (8) , 希望在古典文学史的研究中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能力。五四新文学中成长起来的何其芳希望在古典文学领域为新中国文学寻找新的突破口, 这种“古为今用”的想法在当时并非个例, 因此“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涵盖五四新文学以来的部分并不突兀。其次, 和“现代”建立联系是此时期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心声。1949年后, 处在边缘地位的古典文学研究一直试图参与到当代文学建设中来。陆侃如、冯沅君在谈到“文学史的任务”时表示:“文学史将帮助我们从丰富的遗产中吸取养料, 获得新的力量, 来更好地创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 (9) 而二人在1949年后重新修订的《中国文学史简编》 (10) 更是在“结语”部分增设了一小节“今后的展望”, 从五四运动一直谈到1949年后两次文代会的盛况。
如果说古典文学领域将“现代文学”容纳于“中国文学史”整体中, 还是一种单向的行为, 那么“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就是双向的趋近了。“近代文学”在“十七年”是一个矛盾的存在, 一方面因其特殊的时空位置, 在文学史上长期处于“两不管”状态, 古代文学史将其放在晚清部分, 简略带过;而在新文学研究者看来, 五四和晚清文学改革运动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不是一脉相承的, 五四文学革命是在晚清文学改革运动萎缩、退化和偃旗息鼓之后, 以更激进、彻底的姿态, 要求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进行现代化的一次文学运动 (11) , 因此作为被五四新文学所扬弃的“近代”进入新文学研究者的视域并不顺利。和史学界在近代史领域轰轰烈烈的开拓比起来, 20世纪50年代初文学界对于“近代”反应冷淡。但同时《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于近百年的历史“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 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12) 的论述又让“近代文学”自然地与“现代文学”汇合了。先是郑振铎将“1840年—1949年”合称为“近代期, 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将“现代文学”划入“近代文学”范围 (13) , 理由不言而喻, 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中革命性质的论述为标准的分期。从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来说, 1956年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增添“附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简述 (一八九八———一九一七》一章, 这是1949年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走进新文学史。吊诡的是, 刘绶松一方面指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研究对于新文学来说是完全必要的, 它是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根源,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或无产阶级现实主义) 的中国新文学, 没有疑问地, 它是以中国文学中的古典现实主义为其主要来源的”;另一方面又通过向近代回溯来说明谁是五四新文学的“真正领导者”, 指出胡适发表的文学主张“几乎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已经有过的”, 从而证明胡适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领导者 (14) 。在叙述的矛盾中不难看出, 刘绶松对“近代文学”入史的真实态度, 首先是用它来证实冯雪峰在《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一文中的观点, 将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源头安放进古典文学;其次, 通过对比胡适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主张, 来说明胡适并未超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理论高度, 因而不可能领导五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运动, 与此时期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合拍;只是在这个论证的过程中, 刘绶松却把自己认为“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有着本质差异的真实态度暴露了出来。
从“中国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交叉关系来看, 在新的历史阶段, 新 (现代) 文学早已不是附骥之蝇了, 但也绝不是在真空中培育出来的, 它时而被囊括在别的时段中, 时而又主动向其它时段趋近, 有时同一段时空被赋予不同的名称, 有时同样的名称指向的却是不同的时段。当我们把研究范围扩大时, 就会看到有关“现代文学”断限的更多可能。从郑振铎对于“中国文学史”和“近代文学”的解释, 能够看到此时处于边缘地位的古典文学正抱持着毛泽东有关“文学遗产继承”的论述, 不断向仍在发展中的新文学寻求资源, 试图巩固地位, 努力使研究合法化、扩大化。从历史的阶段来说, 古典文学是现代文学的源头, 但是从郑振铎的命名和分期来看,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对于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逆向哺育的关系, 新文学成为古典文学的“源头”, 因此, 不论是将“现代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时间框架内, 还是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五四新文学”归纳为同一个历史阶段, 都是通过对时间的控制来改写扩大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但此时期, “现代文学”也并不是与其它学科绝缘地、独立发展着, 刘绶松将“近代文学”处理成新文学的源头, 在实际叙述中将时间向前推进, 这是对于经典论述的积极回应, 也是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趋势。
二“当代文学”的出现决定了“现代文学”的时间下限
然而, 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近代文学”, 它们还只是从学科外部保持与“现代文学”的关联, 对于“现代文学”时间的稳定性难以造成实质影响, 真正与“现代文学”保持血肉联系的是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从“十七年”出版的新 (现代) 文学史来看, 不少版本的文学史都将1949年以后的文学视为新 (现代) 文学的一部分或新阶段。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下册) 文末就专门附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章, 记述了各地文代大会的召开, 文艺界的历次批判等内容。这之后, 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孙中田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复旦大学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 都将1949年以后的文学作为现代文学予以记录。
“现代文学”之成为确定的时间概念, 几乎和当代文学同时发生。1957年颁布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中第九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 (1919—1949) ”不仅明确断限, 还在内容中提出了“现代文学”的概念。这份《大纲》是1954年教育部及相关部门组织高校和教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 作为文学史教科书编写的依据。在《大纲》之后出版的文学史基本都以“现代文学”命名 (15) 。事实上, 作为学科, “现代文学”至少在1953年就已经出现了。1953年8月, 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 会议审定了20种教学大纲, 其中就包括“中国现代文学” (16) 。而“现代文学史”的概念在1949年前也已经出现了 (17) , 只是当时的“现代文学”和现在的概念有明显的时间差距。在1957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出版前和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只有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孙中田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采用了“现代文学”的说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此时期, 使用“现代”概念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正是“冷战”阵营的那一方美国提出“现代化”理论的时期, 由此展开两大阵营的竞赛, 那是一个“现代意识”极度膨胀的年代;另一方面, 从当时翻译自苏联的文艺理论参考书来看, 50年代开始普遍地用“现代文学”来指称20世纪的世界文学。因此, 从50年代后期开始, 普遍采用“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 是为了突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世界”的涵义, 并且和50年代后期左翼话语的进一步激化联系在一起 (18) 。从孙中田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能读出这种与世界接轨的时髦意味。这本文学史“绪论”的最后一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意义”, 作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是属于全世界的进步文学范畴的, 它以其自身的先进性, 加入了世界进步文学的行列”。接下来还强调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是以苏联文学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一个组成部分” (19) 。可见, 丁易和孙中田的“现代”还不是和“当代”相对应的时间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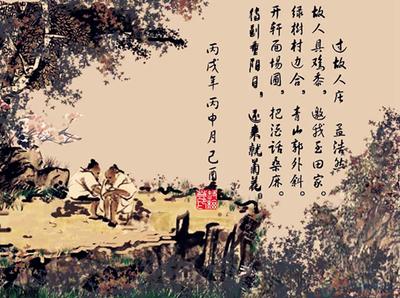
正如洪子诚所说“现代文学”的出现是为了给1949年以后的 (当代) 文学留出位置, 因此作为时间概念, “现代文学”实际上是由“当代文学”的确立决定的。将“1949年以后”从“现代”中彻底剥离, 源自1949年后十年时间段落的出现, 这是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而提出的特定时间段, 当时文学界形成了为1949—1959文学做总结的风潮。1959年10月《文学评论》以“庆祝建国十周年特辑”为栏目发表了一组文章 (20) , 其中毛星的《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从新作家队伍的组建、新题材、新内容、新风格、新形式上介绍了文学的变化, 对十年来文学进行了一次总结。1960年1月, 《文学评论》上突然发表了少知《对〈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一文的意见》和何其芳《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两篇文章;无独有偶, 同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林默涵《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一文, 点名批评了《文学知识》编辑部刊发的《欢呼新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和发展》。《文学评论》和《文学知识》都是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 少知和林默涵的文章引发了所长何其芳的《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少知在文章中批评毛星“仅仅看到了文学在这十年中光辉成就的一部分, 而把最美的、主要的一部分忘掉了或者‘记不清楚’”。毛星忘掉和“记不清楚”的是哪些内容呢?大致包括1956、1957年文学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论战,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创造出的小小说和新民歌等文学形式。而林默涵也在文章中批评有些同志对于这一连串斗争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缺少“应有的愤怒”, “对思想斗争的意义轻描淡写, 略表几句, 相反倒强调地反对思想斗争中的或读者讨论中的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的个别现象”。何其芳“检讨”了《文学研究》和《文学知识》杂志上刊登的几篇文章以及自己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学艺术的春天》一文, 检讨这几篇文章对于1949年后的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估计, 忽视文艺界进行过的思想斗争。几篇文章“还只是从文学本身去肯定, 而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充分估计我们的文学的意义”, “我们的文学完全是一种新型的文学, 人类的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文学。它是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无法比拟的。它的这种根本性质已经超过了过去的一切文学。”
上述批评和检讨说明了一些问题:首先, 对1949年后“十年”的总结不只是简单的文学作品梳理, 除了作为国庆献礼的赞美之辞外, 还需要反映十年来两条道路的斗争。《文学艺术的春天》里, 何其芳将重心放在赞美, 用“也曾经历过播种、除草、除病虫害这样一些工作”的比喻来描述经历的思想斗争。1949年后第一个“十年”文学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应的产物, 拘泥于文学内部的探讨, 就可能被指为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庐山会议后, 年初相对轻松的学术环境重新变得严峻, 文学研究所发表的这组文章表现出一派祥和的态度就显得不合时宜。文章中将十年来文学中存在的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倾向等问题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错误等同视之, 做出文艺界的主要问题是前者而非后者的判断。事实上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 周扬已经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错误定性,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及其它各种错误是可以克服的, 最严重的是修正主义错误。文学研究所自述对此理解不够深, 忽视了八届八中全会的指示, “因而不能正确地估计文学方面的形势, 正确地提出今后的文学工作的任务” (21) 。
其次, 何其芳等人对于1949年后第一个“十年”文学成就的评价显得保守。何其芳在《文学艺术的春天》中将其和五四新文学做比较, 认为“在对于生活的发掘的深刻、概括的高度、典型人物的创造、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成熟等方面”还需要向五四学习。何其芳将其看作“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 认为二者是接续的关系。此时期中央对于文学的认识已经从“新民主主义文学”进入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新阶段。毛泽东在修改《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表明, 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完成后, “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 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 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 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22) , 很清楚地表明随着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的改变, 文学艺术的性质也要发生变化, 从五四新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 无论从社会性质、斗争阶段上来说, 社会主义文学都处在更高阶段, 是超越和替代性质的。因此, 1958年以来为了更好地配合“大跃进”运动,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并且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23) , 在文艺上建设与社会、经济制度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伴随着1949年后第一个“十年”时间节点的提出, “社会主义文学”的表述也越来越成熟, 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和周扬在第三次文代大会的发言中, 都明确将它和“社会主义文学”概念钩连。这种处理方式和《大系》“第一个十年”的叙述同样富有策略性, 通过赋予其时间意义, 将“社会主义文学”迅速“历史化”, 同时这种圆融又所指清晰的表述既符合中国式的思维和接受方式, 也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 而这个阶段也正是“当代”文学脱离“现代”的关键节点。“建国十年”的叙述不能仅仅是历史横截面的铺排, 更是一种纵向的展开, 对于这个新的历史阶段, 正如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明确表示的, 今天必将“创造出比过去任何时代的文艺更为伟大的、新的文学艺术的高峰” (24) , 社会主义文学终将超越五四新文学的逻辑让“当代”呼之欲出。那么, 何其芳等人对于“建国十年”文学的评价就显得过于保守了。应该说, 随着“建国十年”概念的提出, 1949年以后的文学逐渐从“现代文学”中剥离出来, 直至发展为“当代文学”概念;与此同时, “现代文学”开始闭合, 成为封闭的时间概念, 由“建国十年”开启的“当代文学”决定了“现代文学”时间的下限。
三对于“现代文学”内部分期的考察
“现代文学”的分期问题, 除了要确定这个时间整体的定位外, 还需要对它的内部分期做分析。“十七年”出版的几乎每一本现代文学史都有自己的“分期”, 且争议不断。归纳起来, 有这么几种: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 (25) 。
两分法: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学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 (初稿) (1961年出版) 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1919—1942) 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阶段 (1942—1949) 。
三分法: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 (1955年出版) 分为:从“五四”前夕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 从1927年经过抗日战争初期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从1942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三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中分为:“五四”—1927, 1927—1937, 1937—1949。 (26) 1958年“拔白旗, 插红旗”口号提出后, 高校青年学生集体编著文学史开始出现, 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吉林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均分为三期, 前者是1919—1927, 1927—1942, 1942—1949;后者是1917—1927, 1928—1941, 1942—1949。
四分法: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1951年出版) 最早采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分期法。文学史第一期1919—1927, 对应《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第二两期, 并且特意指明了为什么不在1921年分期。王瑶认为《新青年》在“五四”初期承担了重要任务, 但作为综合性的文化批判的刊物, 不可能有更多的力量照顾到文学, 所以这两年没有必要划分为独立的时期;文学史第二期1927—1937, 对应《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三期;文学史第三期1937—1942;文学史第四期1942—1949, 即自《讲话》发表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1957年公布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也采用此分期。

五分法:“五分法”最早的版本来自老舍等人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 (初稿) 》 (1951年发表) , 分为五个阶段:五四前后———新文学的倡导时期 (1917—1921) , 新文学的扩展时期 (1921—1927) , “左联”成立前后十年 (1927—1937) , 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1937—1942) , 由“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全国文代大会” (1942—1949) 。围绕《大纲》“分期”, 引发争议。王西彦提出了自己的五段分期:1.“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 (约从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 ”, 2.“新文学的胜利和扩展 (约从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 ”, 3.“革命文学及其逆流 (约从一九二七—一九三五年) ”, 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战文艺 (约从一九三五—一九四二年) ”, 5.“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与新的人民的文艺 (约从一九四二—一九四九年, 即全国文代大会的召开) ” (27) 。韩镇琪的五段分期是:1.“五四运动后新文学的蓬勃发展时期 (一九一九—一九二七) ”, 2.“‘左联’成立前后十年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 3.“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一九三七—一九四二) ”, 4.“由‘座谈会讲话’到‘八·一五’ (一九四二—一九四五) ”, 5.“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最后全国文代大会召开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 (28) 。同样采用“五分法”的还有李何林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开设的“新文学史”课程:“五四时代” (1917—1925) , “左联成立前后十年” (1926—1936) , “抗战前期” (1937—1942) ,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至文代大会” (1942—1949) , 其中1926—1936时段, 李何林又有“前五年” (1926—1931) 和“后五年” (1931—1936) 的细分, 因此总共分为五期 (29) 。除此之外, 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也分作五期:1917—1921, 1921—1927, 1927—1937, 1937—1945, 1945—1949。
七分法:任访秋分作三期六个阶段:“第一期, 文学革命的前夜。第二期, 从文学革命运动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一期又分为四个阶段, 即 (一) 五四前后到五卅。 (二) 五卅到九一八。 (三) 九一八到七七。 (四) 七七到文艺座谈会。第三期, 从文艺座谈会到第一次文代大会。这一期又分两阶段: (一) 从整风运动到日寇投降。 (二) 从日寇投降到全国解放。” (30)
严格意义上来说, “十七年”时期公开出版的现代文学史, 从分期来看, 几乎都不一样。自1951年第一份教学大纲公布以来, 关于“分期”就存在不少争论, 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时间点。
首先, 文学史的起点究竟是哪一年?官方的表述是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应《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1919年, 但是不少史家仍划在了1917年。1951年老舍等人制定的《教学大纲》一颁布, 就被质疑为什么比《新民主主义论》的分期早两年。“根据什么早走这两年, 教学大纲没有说明, 我们不便猜测, 可是我们由大纲第一编的章节里可以看到, 这两年主要是指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文学革命’, 也就是说, 教学大纲是把这个‘文学革命’提高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革命’, 做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倡导时期’”, 这就是“对文学本质的认识的问题了。” (31) 当时作为教学大纲制定者之一的李何林作了回应, 指出五四不是突变、质变的, 它需要一个前期的酝酿过程, “五四”之前还有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和十几篇《随感录》, 如果以“五四”为起点, 这些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李何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经典论述“五四运动, 在其开始, 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是当时的右翼) 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革命运动”来解释, 但最后又表示并不坚持, “是否可以扩大为‘五四时代’呢?因为实际上还是要从一九一七讲起, 王瑶先生的《史稿》就是例子” (32) 。李何林的窘迫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 如果坚持以1917年为起点, 就可能上升为立场问题, 因此史家在叙述时尽量使用“五四前后”“五四时代”“五四时期”这一类词语, 或者如王瑶本文学史那样直接以1919年为起点, 但在实际叙述中向前追溯。到了后期, 一些编者扬弃了资产阶级文化改良运动, 如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集体编著的文学史都明确将起点放在了1919年。
其次, 究竟以1942年还是1945年作为分界线。早期一些史家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作为分期界限。比如韩镇琪质疑1951年《教学大纲》, 认为应该在1945年“八·一五”断限, 李何林在回应时指出, “其实, ‘八·一五’前后蒋管区的新文学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至于解放区的新文学运动, 更不能用“八·一五”来划分界限。“《讲话》在蒋管区发表以后, 由于反动统治的种种限制, 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虽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 但他的文艺思想实在有不少的影响, 它领导着蒋管区的文学运动在发展进步, 以迎接解放。所以无论就蒋管区或解放区的文艺发展的情况来看, 一九四二年的《讲话》, 都是以后的新文学划时代的界碑!” (33) 。如果说李何林的解释主要是说明了1945年抗战胜利作为分期的“不可行”, 那么《中国新文学史稿》则着重对于1942年作为分期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述, 《中国新文学史稿》证明了1942年《讲话》不仅是解放区文艺的分界线, 也是国统区文艺的分界线。1941年“皖南事变”后, 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完全暴露, 一切有民族意识和希望抗战胜利的作家都对国民党感到了失望与痛恨, 此时“毛主席的著作经常秘密而又普遍地流传于国统区, 新的文艺方向大大鼓舞了作家们追求进步与光明的意图, 因而也有许多思想性很强的作品”, 虽然国统区的作家没有直接与工农兵结合的方便和条件, “但群众的民主运动也经常地用文艺作品和文艺的形式作为武器, 作家们并不是没有战斗的任务和岗位的”, “因此这七年中基本上是新文学获得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领导的时期” (34) 。
此外, 史家们的分期在一些具体的时间上还存在分歧, 但是并不构成本质区别。比如李何林断限时选择了1936年而不是大家通常选择的1937, 原因是1936年“两个口号”的论争基本宣告结束, 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得到了清算, 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具体表现就是《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蔡仪在《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中同样也选择了1936年作为断限, 以“双十二事变”作为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节点。而王西彦则选择了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断限, “有了这伟大的《八一宣言》和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 才有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自然也才有文化界和文艺界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运动。同时, 我认为, ‘七七’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但在文艺运动上, 抗战文艺和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分的。” (35)
细数下来, 这么多本文学史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分期, 可谓“百家争鸣”, 但是从“差异”中感受更多的却是共性。“十七年”的分期无一例外都和《新民主主义论》联系在一起, 差别源自个人对于“经典”论述的理解。史家们并没有掩饰他们以政治历史分期为标准的意图。“如所周知,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的部分, 它的发生和发展是和整个革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相一致的。所以, 中国新文学史上各个时期的划分, 就应该依据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各个历史时期的划分来进行。这样的分期, 才符合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实际。” (36) 第二次文代会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后, 不少文学史中又都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线, 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看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生、发展、壮大和成熟的历史”, 当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仍然是“被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性质所决定的, 是中国现代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要求的反映” (37)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史家们放弃了文学标准, 他们总是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前后寻找文学上对应的节点, 有时这种对应显得牵强, 只能夸大一些文学现象。例如, 新文学运动初期,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于文学能否算一个重要分期, 在当时存在争议, 但是不论是否以1921年共产党成立作为文学分期, 史家们对于这一段历史都没有回避, 张毕来是最先在“1921”断限上做出贡献的研究者, 他在《一九二三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里, 选取了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几篇文学理论著作, 来说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直接地、间接地对于新文学的重要引导作用。其实, 这几位作者发表的大多不是文学主张, 但是张毕来的研究却是开拓性质的, 填补了文学史上的“空白”, 一经论证, 原本比较犹豫的1921年断限变得合理, 后来不少文学史都采用了这种分期法, 即便不以1921年断限, 也都注意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新文学的直接影响。同样的, 有些被当作分期节点的政治事件在文学上的反映并不明显, 为了不让分期隔断, 研究者常使用“不久”“马上”一类的词语, 缓解时间的焦虑。比如张毕来在《新文学史纲 (第一卷) 》中写到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 “它马上在文化思想界起了推动作用”;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将1921年共产党成立对于文学上的影响描述为, “党在它成立后不久的时候, 就开始注意到整个革命事业中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学事业”。
因为分期的敏感性, 一些史家会采用虚化、模糊的方式使表述看起来更稳妥, 其实无论是清晰地划分, 还是模糊地带过, 作者的真实意图都会在对时间的分割中表现出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 (第一卷) 》分期比较特殊, 采用“从一九一八、一九到一九二七、二八的十年间”断限, 说明作者明白分期不可能精确地“一刀切”, 选取节点向前向后辐射, 划定大致范围, 既避免了生硬划分的支离破碎, 也没有刻意强化五四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政治意义, 在与政治的间离中, 整理出文学脉络。从具体分期来说, 张毕来把这十年分为“新文学的五四时期”与“新文学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两个时间段:“‘五四时期’, 是指一个起讫不很明确的时期, 即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一个时期;大约从一九一八、一九前后到一九二二、二三之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 指的是以北伐战争为标志的几年, 大约从一九二三、二四到一九二七、二八的一段时期”, 作者对于时间的叙述, 看上去没有什么野心, 模糊边界代替精密切割, “一九一八、一九前后”的说法既没有将1917排除在外, 也避免了纷争。尽管作者在“分期”上显得漫不经心, 但在实际的叙述中却严守界限。张毕来的文学史是以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和文学领域的传播为主线展开的, 将五四运动前的文化思想分为“妥协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急进的革命思想”, 前者以胡适为代表, 后者以李大钊、恽代英、鲁迅和陈独秀为代表, 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后者;将前者作为不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派排除后, 张毕来详尽地论证了1918年对于新文学的重要性。他指出直到1918年,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播到中国来, 共产主义才在中国快速传播、生长, 在思想界发生作用。但是张毕来自己也承认五四时期“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在文学领域直接地指导创作活动”, 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才在文学领域产生直接作用。张毕来对于1918年的详尽描述, 以及他清晰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主线的“误差”说明了对于分期的考察, 不能仅注意表面的划分, 更需要在具体的阐释中辨析作者真实意图。看似含糊的分期, 可能隐藏着作者的用心。同样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也存在“误差”, 分为1917—1927年、1928—1941年、1942—1949年三段, 三段分期间存在时间“盲区”, 因为文学史的划分大部分以具体事件为界标, 通常会将上一段的下限处理为下一段的上限, 否则, 1927到1928、1941到1942之间一段被遗忘的时光不好解释。但是从这本文学史的叙述来看, 时间“盲区”还不仅是分期不严密的问题。比如文学史的第一段下限划在1927, 对应《新民主主义论》的划分, 采用的是政治标准;但是第二段的上限从1928年开始, 强调1928年“革命文学”再次提出引起的论争, 采用了文学标准, 叙述中无力将两种标准结合起来, 纯粹是为了分期而分期。作者也感觉到了分期中存在的不合理, 在第二版中索性取消分期, 只用“五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前期”这样一些时间概念来代替。
从几本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来看, 分期总体趋于简化, 早期段数多, 越到晚期段数越少, 进入20世纪60年代甚至出现了吉林大学中文系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二版) 那样完全不分期的现象, 用自然时间顺序来代替分期。其实, 现代文学分期的简化、弱化在此时代表了整体趋势, 1949年以来对“分期”问题倾注较大热情的古代文学领域也同样出现了分期简化、弱化的现象。60年代古代文学出版的两套《中国文学史》中都简化了分期, 其中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文学史仅从社会形态分“封建社会以前文学”和“封建社会文学”两个大时期;另一套由游国恩等人编著的文学史也在前言中说明了分期的困难, 因此主要以封建王朝来划分, 游国恩本人曾积极参与过20世纪50年代古代文学史分期讨论, 并做出自己的分期。可见进入60年代, 无论是现代文学, 还是古代文学, 研究者都趋于淡化分期, 用更自然的时间关系去代替“分期”。这种从复杂分期到简化分期, 从“作为”到“不作为”的发展规律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分期”问题从1949年之前的任意自由到1949年后成为显要问题, 从强调到弱化, 既是学科内与学科间进行资源调配的手段, 也是研究者探测的标尺, 在各种主动与被动的时间依附与剥离中, “现代文学”面目逐渐变得清晰。“分期”的出现与消失都是身处“当下”的研究者“重写文学史”的策略, 只是如任访秋所说的,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一个特点, 即一般的都由客观现实决定了政治斗争的方向。由于政治的要求决定了文艺理论的方向, 而理论又领导了文艺创作, 所以“五四”以后, 大抵是理论领导创作, 同时创作也后于理论” (38) , 当研究者确定了“政治斗争→文艺理论→文艺创作”的生产模式, “分期”讨论就只能是有限度的争鸣。那么无论是选择“五卅”“九一八”“七七”一类政治界标, 还是选择“左联”成立、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一类所谓的文学界标, 都是没有实质区别的 (39) 。只是随着“当代文学”的确立, 从时间上将第一次文代会这样的文学界标排除在外, 历史能留给研究者的空隙已然不多, 有关时间的焦虑与惶惑也随之烟消云散。
注释(参考文献):
1 “现代文学”和“新文学”的使用上时有交叉, 当表示整体性时间概念和学科时, 通常使用“现代文学”。
2 参见陆定一:《“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 《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
3 参见刘林海:《论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两次转型》,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
4 参见孙家洲:《“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 《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
5 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 《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6 罗岗:《“分期”的意识形态---再论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 (1917-1927) 〉的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2期。
7 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和曹道衡的《试论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里都有相关论述。
8 何其芳:《〈论《红楼梦》〉序》, 《何其芳文集·第五卷》, 第383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9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稿 (一) 》, 《文史哲》1954年第7期。
10 参见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 (修订本) ,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1 参见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1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 第802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 参见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
14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下) , 第319-320页, 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15 1958年之后不少著作都采用了“现代文学”的说法。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学教研室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学改革小组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学史教研室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 (初稿) 等都已经明确使用了“现代文学”概念。
16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 》, 第510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17 1949年以前已经有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
18 参见贺桂梅:《“现代文学”的确立与50-60年代的大学教育体制》, 《教育学报》2005年第3期。
19 孙中田等:《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卷) , 第31-34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0 包括毛星《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 吴晓铃、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 邓绍基《老舍近十年来的话剧创作》, 卓如《试谈李季的诗歌创作》几篇文章。
21 何其芳:《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 《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
22 毛泽东:《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七册) , 第94-95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3 陆定一:《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 第11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24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 第71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25 这里的分期有些是文学史分期, 有些是用于教学的课程分期, 有些是研究者个人观点, 具有一定代表性, 也摘录于此。另外, 有些史家在大分期中又做了小分期, 统计时, 将小分期也算作独立的阶段。
26 耀东、毅伯、冠星、建领:《三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
27 (35) 王西彦:《关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 (初稿) 〉的讨论》, 《新中华》第十四卷第24期。
28 (31) 韩镇琪:《中国新文学史由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 (初稿) 的意见》, 《新中华》第十四卷第24期。
29 参见李何林:《“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 《中国新文学史研究》, 新建设杂志社出版1951年版。
30 (38) 任访秋:《对〈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商榷》, 《新中华》1951年第14卷第24期。
31 (33) 李何林:《敬复王、韩、任、俞四位先生》, 《新中华》1951年第14卷第24期。
32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上册) , 第20-21页, 开明书店1951年版。
33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上册) , 第12页, 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34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16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35 黄发有在《文学会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指出, 文学会议成为文学史分期的一个核心变量, 其政治功能本身已经被强化, 不能简单视作一种文学标准。
《从“十七年”文学“分期”讨论看“现代文学”的构造》附论文PDF版下载:
http://www.lunwensci.com/uploadfile/2018/0906/20180906034945360.pdf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wenxuelunwen/6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