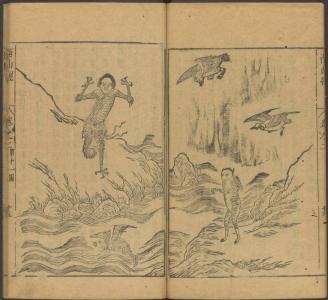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一、为什么是“历史阐释”
英语“Hermeneutics” (德语为Hermeneutik) 的译名, 在中国学术界至少有“解释学”、“诠释学”、“阐释学”和“释义学”等四种译法。
有论者在说明为什么要用“诠释学”时, 作如下说明:“其一, ‘诠’字, 自古就有‘真理’义, (1) 其二, ‘诠’与‘道’相关, 据段玉裁 (1735—1815) 的《说文解字注》:‘诠, 就也。就万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谓, 道之所依也。故曰诠言’。综而言之, ‘诠释’所指向的乃是真理之整体, 因而以‘诠释学’对译Hermeneutics, 显然更为契合Hermeneutics之旨归”。 (2)
也有论者取“解释学”, 认为“人文学科离不开与文本尤其是与经典文本打交道……虽然它也离不开经验, 离不开对事实的关注与探讨, 但处理文本的理解和解读却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历史地看, 文本并不活在作者的原意中, 而是活在后人的解释中, 就这一点来讲, 文本的命运就是理解的命运、解释的命运”。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言, “哲学在解释中存在”。 (3) “然而, 理解和解释背后的‘支点’或下面的‘基础’却十分复杂, 对它进行一种系统的反思是解释学的主要任务”。 (1)
张江取“阐释学”。有学者认为, “国内哲学圈子基本不用‘阐释学’”, 所以不再提它。 (2) 但张江撰文《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纲》时, 先后提出“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概念。 (3) 他认为“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有四点, 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公共阐释”是在反思和批判强制阐释过程中提炼和标识的, 其基本特征有六点, 即公共阐释是理性阐释、澄明性阐释、公度性阐释、建构性阐释、超越性阐释、反思性阐释。
在“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这些概念提出之前, “Hermeneutics”的中译更多地是作“解释学”或“诠释学”, 但有时也作“阐释学”, 不过不多见。例如, 美国文学批评家费什 (Stanley Fish) 在《这门课里有没有文本》中提出“阐释共同体”这个概念, 他认为“文本的阐释并非读者个人随意的自由解释, 相反, 每一个读者都从属于社会的某一权力、经济、文化或宗教共同体, 因而, 对文本的解读必然受该共同体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观念的约束”。 (4)
“阐释” (“解释”或“诠释”) , 与哲学、史学、法学、文艺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有密切的关系。以往出版的与史学有关的“阐释” (“解释”或“诠释”) 著述, 或使用“诠释” (历史诠释) , 或使用“解释” (历史解释) , (5) 但就历史认识的真谛而言, “历史阐释”似更准确, 这是因为“阐”字, 有“开拓、讲明白”的意思。例如汉班固《东都赋》:“于是圣皇乃握乾符, 阐坤珍”。唐吕延济注:“阐, 开也”, 引申为开拓。 (6) 历史不是过程的延续, 更多的是思想的延续;历史认识不是历史的过程性的编年认识, 而是在此基础上的价值性认识和判断, 即历史认识离不开“历史阐释”, 离不开历史的价值判断。揭示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复杂的社会内容, 仅仅靠“解释”或“诠释”是不够的, 因为它们只停留在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和说明, 无法将历史的启迪或教训, 从“过去”转换到现实生活的世界中。
二、构建中国的历史阐释学
在西方, 一般认为施莱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所创立的“一般阐释学”, 是现代阐释学形成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问世表明, 阐释学经历了由方法、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跨越, 逐渐成为一门形态完备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初期, 阐释学传入中国 (当时更多称解释学、诠释学) 。21世纪初, 上海译文出版社曾出版“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丛书8册, (7) 近年, 人民出版社推出“解释学论丛”, 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至少有10种。 (1) 汤一介先生曾四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2) 2002年,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俞吾金的专著《实践诠释学》, 作者在书中提出“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概念。尽管如此, 近20年来创建“中国阐释学”似乎进展不大, 这是因为无论深入探究西方的学术, 还是苦读中国的典籍, 如果只在西方的或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内探求“阐释”或“阐释学”, 而不提出反映现今时代要求的中国阐释学的核心概念或核心范畴, 那么“构建中国阐释学”就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认识历史, 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历史的研究离不开史料, 但史料不等于史学。正如李大钊所言: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 是人类生活的联续, 是人类生活的变迁, 是人类生活的传演……种种历史的记录, 都是很丰富, 很重要的史料, 必须要广蒐, 要精选, 要确考, 要整理, 但是他们无论怎么重要, 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 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 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 (3) 因此, 历史研究就要在广泛收集、占有、鉴别史料的基础上, 揭示历史矛盾运动的本质及规律。而这些, 史料是不会自发地表现出来的, 因此, 就离不开史家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进行历史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 历史研究或历史认识, 是阐释性研究或阐释性认识。历史学的学科特征, 决定了“历史阐释”是这一学科的基本存在形式。司马迁撰《史记》, 强调“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4) 希罗多德撰《历史》, “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 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 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 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5) 这些都表明, 历史的认识和判断, 是通过历史阐释实现的, 没有阐释的历史学是不完整的。
何谓“阐释学”?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概念。伽达默尔、海德格尔, 以及利科 (P.Ricoeur) 、帕尔默 (R.Palmer) 、舒科尔 (L.A.Schokel) 等, 都提出了自己的定义。2001年,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 在“诠释学”词条作了“广义”和“狭义”的解释。近年中国学者潘德荣提出:“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诠释学’。……我们可以将诠释学暂行定义为:诠释学是 (广义上的) 文本意义的理解与解释之方法论及其本体论基础的学说”。 (6) 潘德荣的“诠释学”定义, 与张江的“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概念, 对于当今思考和探究“历史阐释”和“历史阐释学”,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因为这些定义和概念在学理上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平台, 无论是定义还是概念, 都可视作反映历史认识客体的属性的思维形式。这样, 研究“历史阐释”和“历史阐释学”, 不再是各说各话的空泛的“玄学”, 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在具体的概念和范畴中, 同如何构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联系在一起。这并不妨碍学者们独立地思考和表达自己的观点, 提出一定的概念和范畴, 提高学术讨论的效率, 不会产生任何束缚;而且它们自身在研究实践中, 也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基于上述基本认识, 笔者以为不妨将“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拿来”, 结合历史学学科的特点, 并立足中国历史科学的历史与现实去探讨历史阐释。迄今为止, 从中国史学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看, 历史阐释至少应是理性的阐释、创造性的阐释、辩证的阐释。
理性的历史阐释, 和历史的理性认识联系在一起。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考实性的认识。考实基础上的理论阐述, 即“论从史出”, 即对历史过程、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的理性认识或判断, 正是通过历史阐释实现的。只有在这时, 历史的普遍真理、历史矛盾运动的本质内容和规律性认识才能呈现出来。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曾说:“首先, 社会的历史是‘历史’;也就是说, 时间是它的向度。我们关切的不只是结构以及社会的存续与变迁, 还有转变的可能性及类型, 以及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是历史学家”。“实际的历史则是我们必须要解释的。资本主义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能不能发展, 这类问题与我们的关联性只在于它可以帮我们解释这个事实, 那就是资本主义完全是由 (或至少是始于) 世界的某个区域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 它可以将一些社会关系系统的发展趋势 (例如封建制度) , 与其他发展较快的区域拿来对照 (模式上的对照) 。社会的历史因此是社会结构的一般模式与实际特定现象的变迁, 两者间的交流与互动。无论我们研究的时空有多么广泛, 社会的历史就是如此”。 (1) 霍布斯鲍姆所述有一定的代表性, 尽管史家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观或不同的理论与方法, 但就历史认识的路径而言, 历史研究离不开“阐释” (解释或诠释) 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在二战后西方史学发展史上, 可以清楚地看出。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lishilunwen/2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