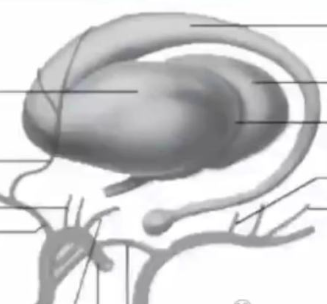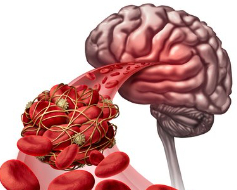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要】中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CNP )是指由带状疱疹、卒中、脊髓损伤、多发性硬化症及腰椎或颈椎神经根病,创伤或手术后 神经损伤等疾病引起的疼痛症状。疼痛被认为是疲劳和抑郁的潜在调节因素, 给患者身心造成长期的伤害。使用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 ) 技术刺激大脑皮层中参与疼痛处理的区域,可能在不影响患者主观疼痛评级的情况下显著降低镇痛类药物的需求,在某些情况下,即 使患者使用较少的镇痛类药物,也能显著降低疼痛评级。这种低成本、简单、安全的治疗方法引起了临床的广泛关注。现就 tDCS 治疗 CNP 的相关机制与临床应用进行综述。
【关键词】经颅直流电刺激,中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疼痛机制
中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CNP)指的是中枢神经系统 结构病变或功能异常所致的神经病理性疼痛(NP),一项 来自欧洲的研究资料显示, 一般人群中的 NP 患病率高达 8% [1] 。根据损伤或解剖位置的不同,NP 可分为 CNP(即 因脊髓或脑的病变所致)和外周 NP [ 包括糖尿病性神经 病、神经损伤、面部疼痛、幻肢痛(PLP)、癌性疼痛及 畸形 ],最常见 NP 包括脑卒中后疼痛、纤维肌痛综合征、 PLP、脊髓损伤(SCI)。疼痛症状的出现和加重通常在病 变发生后的几天内,除影响患者的睡眠、工作以及日常生 活能力外,疼痛还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抑郁、焦虑等情感 障碍。目前临床公认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治疗、神经调控技 术、微创治疗等,但药物治疗对于 NP 效果并不显著。微 创方法则采用神经卡压松解、锥体形成术、神经阻滞及椎 间盘微创治疗等方法针对引起疼痛的病因进行治疗,针对 受累神经微创治疗包括:神经阻滞、射频热凝、神经毁 损,但神经损毁会给患者带来不可再生及修复的损伤。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侵入性电刺激(iES)作为一种有创 的电刺激神经调控技术应运而生,然而在使用过程中慢慢 发现此技术的缺陷,如在使用过程中电极埋置的相应位置 会出现局部感染的情况、维修器械和替换零件成本高等问 题,导致 iES 难以在临床持续改进和广泛推广 [2] 。经颅直 流电刺激(tDCS)技术通过刺激患者大脑皮层,增强大脑 皮质兴奋性,进而改善患者下肢运动能力和认知功能,相 比于非侵入性的经皮 / 经颅电刺激显现出了其无创、安全 性高、易操作等优势,并且临床应用于各种脑功能障碍 的康复治疗中 [3] 。本文选取近些年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 析,旨在探讨 tDCS 治疗中枢性 NP 的相关机制及临床应用进展,现进行如下综述。
1 CNP 发生的相关机制
1.1中枢敏化 中枢敏化是指伤害性刺激的输入增强中 枢神经系统感知疼痛反应的现象,发生在神经损伤背景 下的中枢敏化是 CNP 主要驱动因素。中枢敏化是由低强 度的机械刺激或热刺激引起,所以解除伤害性外周神经 刺激的持续影响也是降低中枢敏化的关键点。神经系统 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其可塑性及可修改性,由于表达改变 或蛋白质转译后状态的改变反映出内在兴奋性及随着突 触传递改变而改变的活动性。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伤害感 受回路中,神经元可塑性构成了中枢敏化,并通过放大疼 痛,成为许多持续临床疼痛状态的主要潜在因素,不同 形式的损伤不仅会导致疼痛来源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也 会导致中枢水平的改变,所以接触伤害性刺激的持续应 用也是降低中枢敏化的关键点。有证据表明,在许多慢 性疼痛情况下都存在中枢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故此需 要在治疗过程中增加对中枢敏化患者的脱敏策略 [4] 。在临 床治疗过程中,医师面对慢性疼痛患者时多数会关注疼 痛周围组织和结构病变,并进行治疗,因为治疗组织是 简单直接的且及时有效的方式,往往会忽略了中枢疼痛 机制也是慢性疼痛中需要考虑的部分,因此当对中枢敏 化机制进行了解后,会为临床提供更多治疗思路,如传 统治疗中药物治疗已被证明能激活并抑制下行疼痛的控 制,并能使中枢神经系统脱敏;外周作用药物已经在临床 试验中证明了具有通过减少外周输入来减少中枢敏化的 能力。
1.2静息膜电位调节理论 膜电位是生物膜的一种关键 特性,也是细胞传递信号的一种方式。膜电位是其功能的 主要调节因子。目前 tDCS 刺激技术在分子水平的作用机 制尚未完全阐明,但研究已经了解到 tDCS 刺激技术可以 对膜电位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即通过改变静息膜电位调 节大脑皮层的神经活性。有研究表明,这种改变对大脑皮 质兴奋性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这与 CNP 镇痛作用紧密相 关,接受 tDCS 刺激技术的阳性刺激后会使受试者脊髓动 作诱发电位波幅短暂升高,使皮质的兴奋性相对增高,而 阴性刺激则能显著降低受试者的脊髓动作诱发电位波幅, 使皮质的兴奋性相对降低,从而证实 tDCS 刺激技术可通 过对膜电位影响而改变皮质兴奋性 [5]。tDCS 刺激技术可以 对丘脑异常活动进行调节,在增加受试者感觉阈值的同 时,进一步抑制其疼痛信号传递,起到镇痛效果。背外侧 前额叶皮质参与调控疼痛的感知及加工情绪成分,阳极 tDCS 刺激技术可影响疼痛形成的环节并形成环路,对大 脑感知、加工疼痛的能力及负面情绪主观反馈能力进行调 节。tDCS 刺激技术可通过静息膜电位超极化或者去极化来 改变皮质兴奋性从而参与疼痛的感知与形成。
1.3阿片肽释放理论 内源性阿片肽是存在于人体内具 有阿片样作用的多肽物质的总称,其参与了疼痛伤害性信 号的调控。纳洛酮是阿片类受体的相关拮抗剂,可以对非 侵入性运动皮质刺激产生抵抗,使得内源性阿片系统调节 颅脑功能起到镇痛作用得以证实 [6]。KNOTKOVA 等 [7] 研 究中,对 8 例难治性中枢性 NP 受试者接受 tDCS 后的阿 片受体利用度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应用 tDCS 刺激技术 后受试者前中扣带皮层、导水管周围灰质及小脑区的二丙 诺啡结合能力明显下降,有力地证实了前中扣带皮层和导 水管周围灰质相关阿片受体结合力明显改变与缓解中枢性 NP 有明显联系。综上所述,刺激皮层并参与疼痛处理的 区域,在不影响主观疼痛评级的情况下显著降低术后阿片 类药物需求,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患者使用较少的阿 片类药物也能显著降低疼痛程度。
1.4其他 突触重塑理论认为 CNP 源于认知系统内的适 应性不良的可塑性变化序列,损伤或疾病会改变伤害性信 号处理并影响躯体感觉系统,因此在没有外界伤害性刺 激的情况下也会感受疼痛,对无害和有害刺激的反应会 增强。tDCS 刺激技术通过下调神经元静息膜电位阈值,使 N- 甲基-D- 天冬氨酸(NMDA)受体功能产生极性- 依赖 性相关修饰,进而使神经突出重塑,增高或降低 tDCS 刺 激技术刺激皮质时所产生的兴奋性 [8]。
伴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引领了脑血流技术及神经功能 成像技术发展,tDCS 对大脑血流的调控及对神经功能的 影响受到重视。有研究发现,阳极 tDCS 刺激技术可增加背外侧前额叶皮质相应区域电极下的脑血流灌注,而阴极 刺激则能降低脊髓动作诱发电位幅度,从而使 M1 区血流 量显著下降 [9] 。伤害性疼痛感知系由脊髓神经传导,经大 脑前扣带回皮层等高级皮质脑区处理及调控,这一理论证 实 tDCS 刺激技术原理可能与刺激增加了大脑前扣带回皮 层中神经元活性,从而对下行疼痛下调产生激活作用,进 而发挥镇痛作用有关,因此大脑前扣带回皮层可以作为一 种新的中枢神经调节靶点用于临床疼痛精准管理。
2 经颅直流电刺激技术的临床应用
2.1脑卒中后疼痛 脑卒中患者病发后可出现 CNP,其 疼痛部位与大脑损伤部位的神经相呼应,而梗死区皮质反 复去极化(去极化信号通过受损的皮质扩散到正常灌注的 脑组织中)是导致梗死面积扩大的原因之一。当 CNP 患 者在疼痛区同时出现感觉丧失与超敏征时,往往提示出 现传入神经阻滞及神经元过度兴奋性双重结合病变。谭娟 等 [10] 研究中通过分析 CNP 患者治疗 4 周后不同刺激时间 下自我疼痛感觉强度、疼痛区与对侧区皮肤温差、镇痛效 果及神经电活动的变化,发现 tDCS 刺激技术能增加 CNP 患者大脑皮质层电活动,降低患侧皮肤温度,并具有镇 痛作用,且其疗效与刺激时间成正比。BEA 等 [11] 研究中 将 14 例 CNP 患者,随机分为 tDCS 组及假 tDCS 组,并 给予初级运动皮层持续阳极刺激 20 min(2 mA),两组患 者均予相应干预 3 周(3 d/ 周),证实 tDCS 刺激技术能有 效改善脑卒中后出现 CNP 患者的感觉识别功能,从而发 挥镇痛作用。在临床康复治疗方案中通过常规的运动疗法 治疗、言语疗法治疗、手功能疗法以使其进行功能康复, 再增加 tDCS 刺激技术既可以精确地探索脑活动的正常与 异常,也可以选择性地干扰某一特定皮质区域的正常活动 以修复脑部因脑卒中而受损的神经环路,以更好恢复患者 神经功能。尽管上述研究显示 tDCS 刺激技术对脑卒中后 疼痛通过多方面发挥作用,但这种治疗方式还面临诸多挑 战,例如目前没有明确指南性文件规定刺激区域及时长, 这就使得这项技术还处于临床探索阶段,预示着该治疗手 段在临床应用上具有更大的潜能,治疗方式具有多元性。
2.2幻肢痛 PLP 是指在截肢术后或意外损伤失去特点 身体部位后,缺失肢体产生的疼痛感觉异常即仍能感受到 该部位存在疼痛或不适(类似电击、刀割、撕裂、烧伤 等)并且疼痛持续、呈阵发性加重。PLP 的病理机制被认 为是由外周神经损伤产生的神经鞘瘤引起的异常放电(外 周机制)、脊髓抑制作用减弱(脊髓中枢机制)、大脑皮质 功能重组(大脑中枢机制)等多种因素诱发的 [12] 。故 PLP 虽在此前被归类为外周性神经病理性疼痛,但随着研究的 深入,发现该病的机制也涉及中枢性机制。PLP 疼痛程度和频率因人而异,其是一种急性传入神经阻滞,是由于周 围神经损伤、脊髓损伤或臂丛撕脱引起,通过脑功能成像 观察 PLP 患者患肢进行伴有不适感的自主运动时可以发 现初级运动皮质、初级躯体感觉皮层、运动辅助区的激 活,除此之外,还发现小脑、前扣带皮质、后扣带皮质的 激活,因此运动感觉系统和疼痛处理相关的脑网络系统紊 乱也被认为是 PLP 的潜在原因 [13] 。情感和心理因素也是 引发 PLP 的重要原因,患者失去身体部位可能会引发悲 伤、焦虑等情绪,而这些情绪可能影响大脑对疼痛的感知 和处理。关于中枢神经系统中患侧肢体和健康一侧肢体的 异同,有学者做出了如下的相关试验,已知两侧上肢同时 运动时, 一侧上肢的运动模式会影响另一侧上肢的运动模 式,继而使两侧上肢的运动向同一种模式转化(如一只手 画三角形的同时另一只手画圆,则会发现画出来的三角形 接近圆形),这种两上肢协调运动的影响可以进行自主运 动的患侧上肢和另一侧健康上肢的运动模式中观察得到, 但在无法进行自主运动的患者中不能被观察到 [14]。PLP 主 要是由于初级躯体感觉皮层(S1)重组,其特征可能是肢 体缺失感觉功能退化及身体其他部分代偿性恢复。有研 究发现,在 S1/M1 缺失的手部皮层上使用兴奋性 tDCS 刺 激技术的刺激方式可显著缓解 PLP,且治疗效果持续长达 1 周,拓宽了针对 PLP 疼痛机制的理解,也为今后机制研 究及临床试验设计开辟思路,即继续刺激脑岛于 S2 区是 否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 [15] 。更重要的是,tDCS 不仅是缓 解 PLP 的一种治疗方法,还能用来研究 PLP 的神经机制, 此观点可以在基础医学领域继续深挖,去探究 tDCS 刺激 技术是如何改变其神经传导通路来发挥作用,建议未来采 用更大样本量且更严格的临床试验,并结合高分辨率的脑 电图(EEG)、功能性磁共振(fMRI)等大脑成像技术来 验证 tDCS 对 PLP 的缓解效果,且进一步研究其背后的神 经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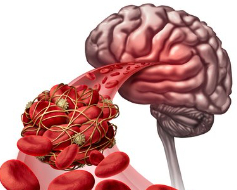
2.3纤维肌痛综合征 纤维肌痛综合征是以肌肉关节疼 痛、身体疲劳、认知功能障碍及情绪障碍的慢性弥漫性 疼痛综合征,其特征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引起感觉 输入障碍的慢性疼痛综合征,可能是由中枢敏化及疼痛 相关的神经回路的适应不良可塑性引起的。最早临床治疗 纤维肌痛综合征常使用镇痛药,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镇 痛药存在治疗局限性,并非治疗该疾病有效的治疗方法, 因此 KANG 等 [16] 基于该问题做出如下研究,对镇痛药 产生耐药性的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使用 tDCS 刺激技术治 疗,治疗结束后 46 例参与者视觉模拟量表(VAS)疼痛 评分与治疗前比有明显改善,后续证实持续治疗 36 d 或 更久的治疗周期的镇痛效果更佳。SILVA 等 [17] 研究中使用 Go/No-go 试验测试了 40 例患有纤维肌痛综合征的患者,发现阳极位于左侧的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区可能会影响感觉 辨别疼痛的处理路径,从而诱导疼痛缓解,并提出背外侧 前额叶皮质接受刺激后观察到的镇痛效应部分归因于一种 间接抑制丘脑的活动。随着大脑功能探测技术的成熟,从 上述研究发现针对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来说刺激背外侧前 额叶皮质区域效果更显著。尽管 tDCS 刺激技术治疗纤维 肌痛综合征的初步结果很有希望,但仍有治疗有限、反应 率低和耐受性差等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利用 tDCS 刺激技 术治疗纤维肌痛综合征的研究对象样本量缺乏双盲、多中 心、对照试验,数据表现出来异质性高,最佳刺激模式有 待设计期待有多中心、大样本量的 RCT 研究进行循证医 学检验。
2.4脊髓损伤 SCI 是指在炎症、外伤及肿瘤等多种因素 作用下所导致的脊髓结构及功能损害,可出现损伤平面以 下感觉、运动、括约肌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等表现。目前 临床针对 SCI 运动功能障碍多以康复治疗为主,然而常规 康复训练存在起效慢,恢复时间长,成功率较低等缺陷, 无法满足患者治愈需求。tDCS 刺激技术能改变脊髓神经网 络兴奋度,促进神经重塑,同时阳极 tDCS 刺激具有能够 增强皮质兴奋性,改善脊髓运动神经传导,修复脑区结 构功能最终能够减轻运动功能障碍,所以基于这一问题, YEH 等 [18] 研究中选取了 12 例 SCI-NP 的患者,随机分为 试验组与对照组,除了接受 12 次刺激还配合连续 4~6 周 适当的上肢运动,对于 SCI-NP 试验组在随访期间似乎表 现出较慢的疼痛缓解趋势,在一段时间的随访才有一定的 效果显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 SCI-NP 患者带来信心。 该治疗方案居家应用于 SCI-NP 患者同样具有可行性,并 提出需要发展更加便携、不依赖于家人及更简易的电极定 位的设备更新意见 [19] 。上述研究得出阳极 tDCS 能保护中 枢神经源性神经,缩短神经功能恢复时间,与等速肌力训 练提高受损部位的功能独立性与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虽然目前的机制研究与临床指南显示 tDCS 刺激技 术在治疗 SCI 疾病方面推荐指数不高,考虑其原因一是 SCI 发生机制尚未完全研究清楚,二是还没有大规模临床 设计观测到可靠的治疗效果支撑。
2.5多发性硬化症 多发性硬化症(MS)是一种中枢神 经系统的炎症性脱髓鞘疾病,是年轻人群中最常见的神 经系统疾病。WORKMAN 等 [20] 进行了一项随机双盲对照 交叉试验,将阳极设置在患者 M1 区,阴极设置在对侧眶 上,治疗前后 VAS 评分存在差异。RUDROFF 等 [21] 首次 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ET)来观察 MS-NP 的 患者在接受 tDCS 刺激技术治疗前后丘脑活动的病例报 告,研究结果表明:tDCS 刺激技术治疗会引起丘脑中相互 连接的大脑结构的功能性改变,且在改善疲劳、疼痛和认知症状方面作用明显。tDCS 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方法在改 善多发性硬化症症状方面具有吸引力,但其他治疗方案仍 然有限,制定出个性化神经解剖学的方案,并在实验设计 中引入网络映射,可能有助于克服研究之间的可变性 [22]。
3 小结与展望
tDCS 刺激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未来应用前景 广阔。但仅仅局限于评估疼痛程度本身并不能全面了解疾 病, 仍应选择从疼痛程度、性质、范围、伴随症状、疼痛对 情绪影响、疼痛对生活的影响等相关量表来全面充分了解中 枢性NP,且神经调节受刺激位置及强度等多因素的影响,加 之大脑功能和疾病间存在复杂性,其在神经病理性疼痛领域 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未来仍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 持续改进和优化临床治疗方案,不断地更新研究优化 tDCS 刺激技术, 继而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可靠的 tDCS 刺激技术 方案,缓解患者躯体症状及心理痛苦,获得更优疗效。
参考文献
[1] MACONE A, OTIS J AD. NeuropathicPain[J]. Semin Neurol, 2018. 38(6): 644-653.
[2] SPUCK S, TRONNIER V, OROSZ I, et al. Operative and technical complications of vagus nerve stimulator implantation[J]. Neurosurgery, 2010. 67(2): 489-94.
[3] LEFAUCHEUR J P, ANTAL A, AYACHE S S, et al. 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on the therapeutic use of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J]. ClinNeurophysiol, 2017. 128(1): 56-92.
[4] 兰岭 , 黄宇光 , 申乐 . 术后慢性疼痛相关炎症反应与免疫调节机 制研究进展 [J].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 2017. 23(3): 161-164.
[5] DADGARH, MAJIDIH, AGHAEI S. Biological and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J]. Iran J Psychiatry, 2022. 17(3): 350-355.
[6] BENEDETTI F, SHAIBANI A, ARDUINO C, et al. Open-label nondeceptive placebo analgesia is blocked by the opioid antagonist naloxone[J]. Pain, 2023. 164(5): 984-990.
[7] KNOTKOVA H, PORTENOY R K, CRUCIANI R A.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relieved itching in a patient with chronic neuropathic pain[J]. The Clinical Journal of Pain, 2013.29(7): 621-622.
[8] GHANAVATI E, SALEHINEJAD M A, DE M L, et al. NMDA receptor-related mechanisms of dopaminergic modulation of tDCS-induced neuroplasticity[J]. Cereb Cortex, 2022 , 32(23): 5478-5488.
[9] JAMIL A, BATSIKADZE G, KUO H I, et al. Current intensity-and polarity-specific online and aftereffects of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An fMRI study[J]. Hum Brain Mapp, 2020. 41(6): 1644-1666.
[10] 谭娟 , 李晓敏 , 苟晨 , 等 .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脑卒中后中枢性疼痛 患者的镇痛效果研究 [J].川北医学院学报 , 2021. 36(6): 753-756.
[11] BEA S H, KIM G D, KIM KY, et al. Analgesic effect of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on central post-stroke pain[J]. Tohoku J Exp Med, 2014. 234(3): 189-195.
[12] FLOR H, NIKOLAJSEN L, STAEHELIN J T. Phantom limb pain: a case of maladaptive CNS plasticity?[J]. Nat Rev Neurosci, 2006.7(11): 873-881.
[13] RAFFAELE N, VICIANA V, LUCA S, et al.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subjects with phantom pain and non-painful phantom sens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J]. Brain Research Bulletin, 2019.148-149.
[14] URITS I, SEIFERT D, SEATS A, et al. Treatment strategies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phantom limb-associated pain[J]. Curr Pain Headache Rep, 2019. 23(9): 64.
[15] KIKKERT S, MEZUE M, O'SHEAJ H, et al. Neural basis of induced phantom limb pain relief[J]. Ann Neurol, 2019. 85(1): 59-73.
[16] KANG J H, CHOI S E, PARK D J, et al. Effects of add-on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on pain in Korean patients with fibromyalgia[J]. Scientific Reports, 2020. 10(1): 12114.
[17] SILVA A F, ZORTEA M, CARVALHO S, et al. Anodal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over the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modulates attention and pain in fibromyalgi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Scientific Reports, 2017. 7(1): 135.
[18] YEH N C, YANG Y R, HUANG S F, et al. Effects of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followed by exercise on neuropathicpain in chronic spinal cord injury: A double-blind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pilot trial[J]. Spinal Cord, 2020. 59(6): 684-692.
[19] CARVALHO V G, ALMEIDA R, BOECHAT-BARROS R. Motor cortical excitability behavior in chronic spinal cord injury neuropathic pain individuals submitted to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case reports[J]. Spinal Cord Series and Cases, 2020. 6(1): 101.
[20] WORKMAN C D, KAMOLZ J, RUDROFF T.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for the treatment of a multiple sclerosis symptom cluster[J]. Brain Stimulation, 2020. 13(1): 263-264.
[21] RUDROFF T, PROESSL F, KAMHOLZ J, et al. Increased thalamic activity and less neuropathic pain after tDCS observed with PET in a patient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A case report[J]. Brain Stimulation,2019. 12(1): 198-199.
[22] RAHIMIBARGHANI S, AZADVARI M, EMAMI-RAZAVI S Z, et al. Effects of nonconsecutive sessions of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and stationary cycling on walking capacity in individuals with multiple sclerosis[J]. Int J MS Care, 2022. 24(5): 202-208.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xuelunwen/712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