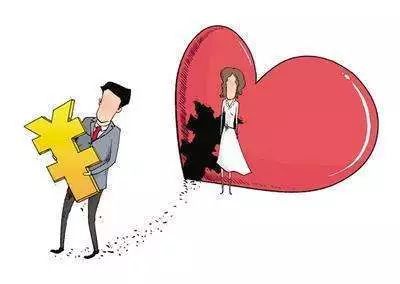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要:婚恋诈骗是诈骗罪中的新型犯罪类型,犯罪分子利用当今社会许多大龄单身青年迫切 结婚的心理,通过婚介公司结识受害人,以恋爱名义与其交往,进而诈骗受害人财产的行为,严重 威胁到公民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因此,加强公民对于法律知识的学习与加强社会管理,能从 源头预防婚恋诈骗犯罪, 同时, 使司法部门严加执法能有力打击婚恋诈骗行为。
关键词:婚姻欺诈,诈骗罪,婚姻法,民刑交叉
一、婚姻欺诈的民刑界限及特点
目前学界有关于婚姻欺诈的讨论主要是在民 法的角度来对此种行为进行规制。例如一些学者 认为,骗婚案件应当从婚姻法角度去探究,探析夫 妻双方婚姻破裂的原因,把对于骗婚案件的规制 限定于民法;[1] 也有学者认为,对于民间普遍存在 的老夫少妻以及骗取彩礼的行为,应当在婚姻缔 结阶段加以严格的法律限制。[2] 综上,对于符合诈 骗罪犯罪构成的婚姻欺诈行为应当进入刑法的调 整范围,单纯通过民事诉讼或调解对该行为规制 力度有限。应当分情况讨论,首先要明确构成诈骗 罪的婚姻欺诈行为。
( 一 ) 婚姻欺诈的民刑界限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以下简称《刑法》) 上的诈骗,是指犯罪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 真相的方式,利用被害人陷入或继续保持认知错 误骗取财产数额较大的行为,诈骗罪是一种行为 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交往型犯罪。[3] 英美法系中存 在诈骗财物罪的规定,其与我国《刑法 》中诈骗 罪的内涵基本相同,即要求行为人一方面存在非 法占有目的,另一方面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 诈骗行为,同时要求诈骗行为与被害人遭受财产 损失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4] 那么对于应当由 刑法规制的婚恋诈骗行为,其行为结构也应当符 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即“骗婚人以骗取财产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 →被骗婚人产生错误认识 →被 骗婚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 →骗婚人取得财产 →被骗婚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 ”。据此可见,婚恋 诈骗与诈骗犯罪的区别点在于前者以人身关系为 媒介,来满足其非法占有的目的。
除此之外,婚姻欺诈主体要件,应当满足男女 朋友关系或夫妻关系中一方的条件,同时要满足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条件,且行为人主观上 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据此,婚恋诈骗应当是指具 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财产 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与他人 交往或者缔结婚姻的事实,使他人主观上产生双 方属于恋爱关系或婚姻关系的认识,从而基于该 认识或对方要求处分财产数额较大的行为。
( 二 ) 婚恋诈骗犯罪的特点
由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当今 社会中年轻人承受着越来越重的婚恋压力。这就 给了一些犯罪分子可乘之机,犯罪分子利用被害 人单身向往情感归宿的心理,根据被害人的性格 等特点,来包装自己的身份以及性格,继而以结婚 或恋爱的名义接触被害人,在交往的过程中进行 财产诈骗。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了产业链 —— 犯罪 分子与婚介公司合伙骗取被害人的财产。婚姻欺 诈行为的具体表现特征总结如下:
1.婚姻欺诈以获取被骗人财物为目的
在一些婚姻欺诈的案件中,绝大多数的行为 人将不动产、动产以及钱财作为取得目标,例如要 求对方买房、买车或给予彩礼。因此,在类似案件 中,常常能发生被害人一方超出正常支出合理范 围的行为,并且从社会相当性的角度来看,并不符 合社会上一般人的观念,且双方在获取利益的对 比上严重失衡,具体来说被害人一方经济上通常 会产生大额、大比例的付出经济利益,而行为人一 方往往没有支出或仅有很少比例的支出。
2.手段的灵活性与欺骗性
骗婚行为人往往事先拟定好计划,实施诈骗 行为的时候,逻辑缜密,行为复杂多样。一方面, 行为人会根据被害人自身的性格特点,来包装自 己身份、性格以及接触方式,因此行为人在行为上并没有统一的行为方式或固定的衡量标准,而是 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另一方 面,行为人往往以发展男女朋友关系或以结婚为 名义与被害人接触,通过与被害人形成恋爱关系 或者婚姻关系,来获取其财物,更有甚者通过离婚 来达到获取财产的目的,由于行为手段具有“合 法 ”的外衣,婚恋诈骗往往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与 迷惑性。
3.婚姻欺诈的普遍性
截至 2021 年 6 月,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 的数据显示,涉及婚姻欺诈的案件多达 7228 件, 其中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数量较多。在日常生 活中,更有甚者以团伙的形式作案,而且其内部分 工明确,结构严明,形成专门的产业链。有专门负 责与被骗者线上接触的人员,也有专门负责与受 害人线下接触的人员。甚至一些犯罪分子通过成 立婚姻介绍公司来获取诈骗对象的隐私信息,如 工资收入、性格、爱好,从而实施诈骗行为。
二 、司法实践中婚姻欺诈的问题
( 一 ) 情感纠纷与婚姻欺诈难以区分
婚姻欺诈往往被当成民事纠纷处理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涉及当事人的情感因素,接警人很难 辨别被害人报警是否出于感情原因而夸大事实或 诬陷,从而对是否存在犯罪行为产生怀疑,现实生 活中也确实存在因为感情出现问题而报警诬告的 情况。[5] 普通婚恋纠纷以双方具有感情为基础;婚 姻欺诈同样也是以双方具有感情基础从而实施诈 骗行为的,这就造成两者难以区分的问题。此外被 害人察觉被骗并报案后,一些犯罪分子会利用对 方感情的“软肋”, 利用被害人来逃脱罪责,被害 人基于对犯罪人的感情或是自尊心而态度摇摆不 定,在问题的焦点上顾左右而言他,也是司法实践 中难以处置的情况。
( 二 ) 证据问题
在一般的诈骗行为中,其行为方式主要表现 为利用虚假的身份或编造谎言行骗,传统诈骗的 行为方式都比较直观、类型化,被害人通常易于察 觉,不容易上当受骗,因此对于传统诈骗来说司法 实践中通常不会存在证据认定困难的问题。
但对于婚姻欺诈的证据认定则存在很多问题。 一方面,婚姻欺诈犯罪中被害人存在较强的主观 情感色彩,因此对于一些事实与线索往往存在夸 张的成分,导致办案人员获取客观真实的口供存 在一定的困难,从而引起放纵犯罪的后果,或者 使单纯的感情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制造冤假错 案;另一方面被害人的处分行为,首先是基于被害 人陷入错误的认知,在诈骗罪中处分行为是“欺 骗行为 ”, 以及基于欺骗行为引起“认识错误 ”,与行为人“取得财产 ”之间起链接作用的要素。 但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被害人都将举证的重点 放在其处分行为并非基于其主观真实的意思表 示,而是出于对方的欺骗作出的处分,而忽略对行 为人欺骗行为的举证,这样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行 为人实施欺骗行为的作用,因此在绝大多数案件 中都因为证据不足的原因而未追究责任。
从诉讼法的层面来看,证据不足反映的问题 就是举证的问题。举证是诉讼中证明对方有罪的 重要环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 信口供。若仅存在被害人的口供,根据“孤证不能 定罪 ”的原则,很难证明婚恋诈骗的客观存在。同 时,由于婚恋诈骗的行为具有特殊性,证明被告人 具有婚姻欺诈的故意具有很大的难度,具体来说 证明行为人主观上以获取钱财为目的,并且实施 了发展男女朋友或者婚姻关系的行为。这往往涉 及被害人的隐私,所以难以取证,或者被害人根本 没有意识收集证据。如果行为人通过登记与被害 人取得了合法的婚姻关系,那么更无法证明其主 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与诈骗的故意了,因此举证 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 三 ) 民事途径发挥的作用有限
目前我国《刑法 》中虽然存在诈骗罪的立法 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利用《刑法 》 对骗婚行为进行规制,对于骗婚行为大部分还是 通过调解或民事诉讼等民事途径解决。在民事法 律规范中与骗婚行为直接相关的法律规定是:《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 一 ) 》( 以下简称《婚姻家庭 编司法解释 ( 一 )》) 第五条规定:“ 当事人请求 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 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 ) 双方未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 二 )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 未共同生活;( 三 )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 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 离婚为条件。”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在行为人取 得彩礼且未进行婚姻登记的情形下,被害人可以 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彩礼。从这个角度 看该司法解释确实为骗婚者返还彩礼提供了一定 的规范基础,明确了骗婚人的法律责任。但民事 制裁相比刑事制裁,所能发挥的事后救济、法律 责任的威慑力以及预防效果始终是有限的,这也 是司法实践中婚恋诈骗如此猖獗的原因。
三、完善打击婚姻欺诈的对策
( 一 ) 明确婚姻欺诈的入刑标准
在上文可以看出仅通过民事途径来规制此类 行为能发挥的事后救济以及预防效果有限。虽然婚恋诈骗行为具有侵犯人身与财产的特殊性,但 通过与诈骗罪的行为结构相比两者存在一定的重 合部分,即一方面两者在刑法的评价上具有等价 性,另一方面婚恋诈骗得到行为结构与诈骗罪的 犯罪构成具有一致性,都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 相的手段,主观上都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所以说骗 婚行为符合诈骗罪的行为结构,这就要求办案机 关在遇到此类案件时,需掌握本罪的入罪标准。
因此,办案机关可以借鉴《婚姻家庭编司法 解释 ( 一 )》 第五条中所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明显 属于诈骗行为的情形,作为诈骗罪客观行为的一 种表现方式来进行把握。并且在此基础上,根据目 前掌握的证据,结合获取利益一方的认知能力、 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感情基础、获取钱款的 去向以及获取利益的一方过去是否存在类似行为 等,来综合认定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诈骗的故意以 及非法占有的目的。即需要办案人员与司法裁判 者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具体判断,从而为司法实践 提供一个相对确定的标准,严密法网。
( 二 ) 明确情感纠纷与婚恋诈骗的界限
在上文中提到由于情感纠纷与婚恋诈骗在司 法实践中易混淆,存在难以界定的问题。要解决 这个问题就要明确二者的界限与标准。一方面来 说,情感纠纷与婚姻欺诈的相同点是两者都涉及 一定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这同样也是两者之 间的易混淆点,仔细分析两者的区别可以发现,两 者所涉及领域的比重不相同,在情感纠纷中主要 的争议点集中在人身关系,继而发展到双方对于 “彩礼 ”退赔、“ 分手费 ”等财产关系的纠纷上; 但婚姻欺诈的场合主要的纠纷在财产关系。具体 来说,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时要对案件纠纷所涉 及的领域作出衡量,对比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纠 纷在案件中的比重;可以根据二人的关系存续过程 中的支出是否具有社会相当性来进行判断,例如 一方对另一方的支出是否超出作为社会理性人的 认知,从而判断其客观行为是否同诈骗罪的实行 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 行为人的主观要素,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以玩弄对 方感情为目的实施欺骗对方的行为,且未造成对 方财产损失或造成较小的损失,只能评价为不道 德的行为而不构成婚姻欺诈。
( 三 ) 降低证明“标准 ”
在正常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举证责任一般是 由检方承担,这一点毫无疑问。王泽滢在《论婚恋 诈骗行为的刑法规制 》一文中提出,婚恋诈骗行 为中牵涉到了很多主观上的因素,这就给检方承 担证明责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参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将本罪设定为法律推 定犯罪且“说明来源 ”是阻却推定犯罪成立的正 当化事由。[6] 这种“证明责任转移 ”的观点在理论 上存在诸多诟病。首先,此观点中所参考的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罪作为一种有罪推定,加重了被告人 一方的义务,属于适用“相对严格责任 ”原则的 情形,但“相对严格责任 ”其本身在学界上就存 在争议;其次,婚姻欺诈在刑法层面属于诈骗罪的 范围,如果转移婚恋诈骗的证明责任,势必会引起 与其他诈骗行为的不协调,破坏法秩序的统一。因 此针对该问题应当在立法层面解决,可以采用司 法解释的方法针对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有针对性 地解释,可以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 “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 ) 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 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 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 二 ) 合同签订后携带 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 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也就 是说行为人的某种客观表现符合法律规定时,检 方只要提供行为人客观上存在特定行为的证据, 便能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主观犯意,即采用客 观行为来进行主观推定,从而来达到降低证明责 任标准的目的。
四 、结语
解决婚姻欺诈的问题,除了通过普法层面在 源头上消灭行为人的动机,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诈 骗罪行为结构的把握,来明确把握婚姻欺诈的入 罪标准;同时建议出台新的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司 法解释,以便为刑事诉讼提供明确指引。并且在此 基础上要明确民事情感纠纷与刑事婚恋诈骗的界 限。通过以上措施可以为规制婚恋诈骗行为提供 支持。
参考文献
[1] 潘建国,王菲.对骗婚案件的调查研究[J].法学杂志,1996(6):36.
[2] 于如涛.现代社会中的骗婚与法律关系[J].法制与社会,2011(26):189-190.
[3] 姜涛.网络型诈骗罪的拟制处分行为[J].中外法学,2019.31(3):692-712.
[4] 张明楷.论诈骗罪的欺骗行为[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3):1-13.
[5] 王志展.新常态下打击婚恋诈骗犯罪问题研究[J].犯罪研究,2015(3):60-67.
[6] 王泽滢.论婚恋诈骗行为的刑法规制[D].昆明:云南财经大学,2019.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falvlunwen/581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