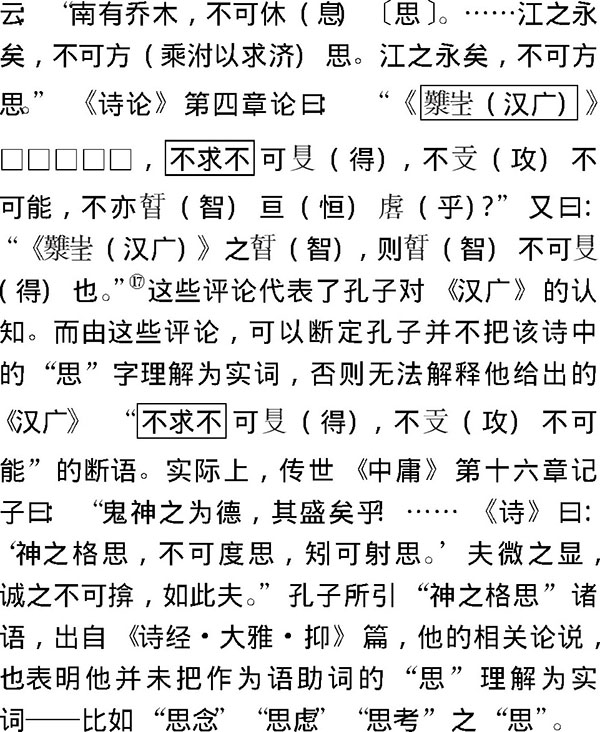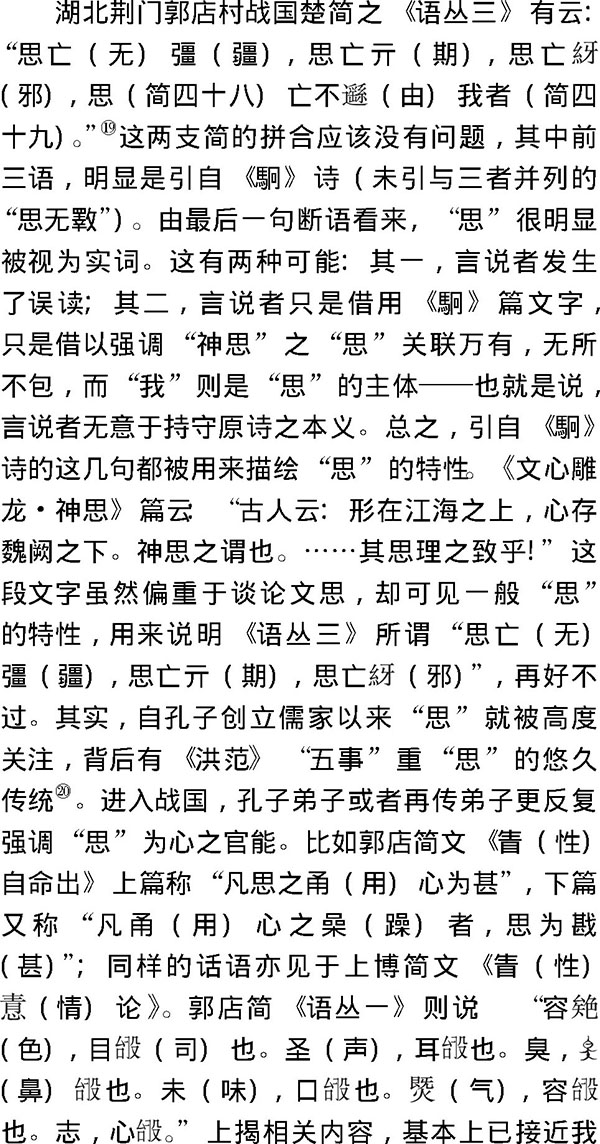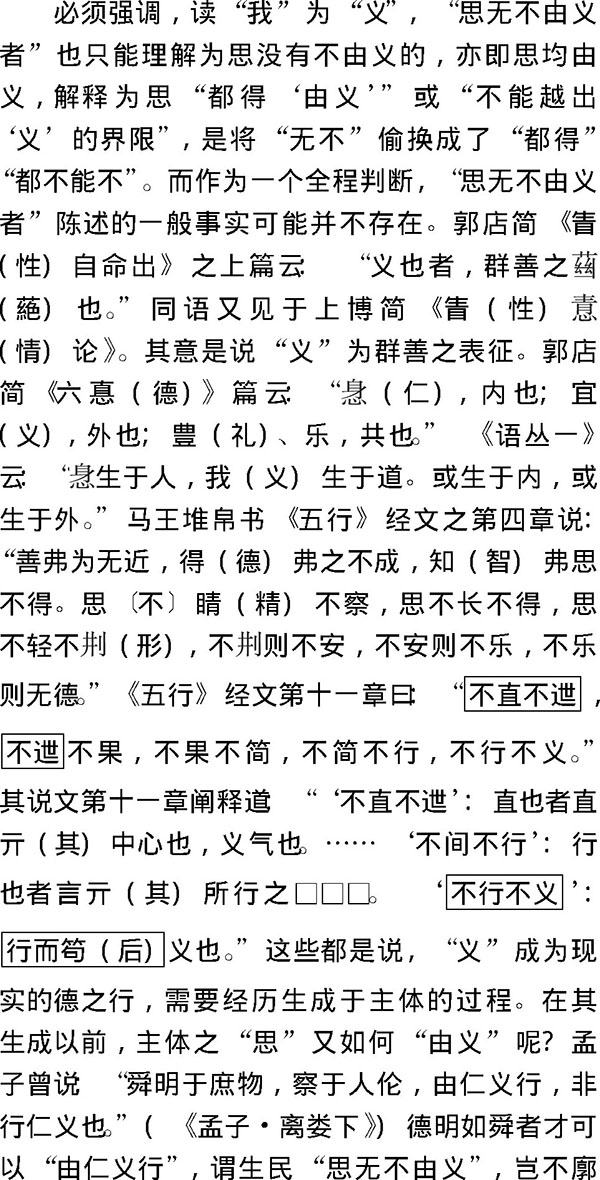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孔子以《诗·鲁颂·駉》篇的“思无邪”概论《诗三百》, 使它成为极为重要的《诗经》学话语。孔子本意是形容《诗》之蕴藏既富且广、无所不包, “思无邪”在这个层面上成了孔子《诗经》学形态模式的表征。但嗣后孔子本意迅速流失, 自战国中后期至汉代, “思无邪”作为《诗经》学话语的意义完成了第一次转换, 被用来指涉《诗》在写作的思维取向上不背离正确价值。由是“思无邪”以其新指向又成了汉唐《诗经》学形态模式的表征。朱熹在《诗经》学史上的重大意义是在相当程度上解放了诗歌文本, 将孔子以“思无邪”概论《诗三百》的意旨, 解释为读《诗》使人思无邪。“思无邪”于是又以一种新指向, 成了朱熹或者宋代《诗经》学形态模式的表征。
关键词:
思无邪; 《诗经》学; 形态模式; 意义转换;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土文献《五行》《诗论》与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重构” (项目编号:14FZX005) 的阶段性成果;
Si Wu Xie, As a Discourse of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Its Meaning Transformation
Chang Sen
孔子曾说:“《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 此后“思无邪”就成了《诗经》学的重要命题。但当历代学者不断追求这一命题的本旨, 并意欲给出一种合理解释时, 他们可能在立场和认知上犯了错, 即忽视了该命题之内涵在历史发展中的复杂变化。孔子这样说当然有自己的界定, 可战国中期以前, 孔子后学对“思无邪”之“思”有一个误解, 促成了汉代经学家的新解释, 奠定了人们对这一命题最基本的认知;宋代以降, 质疑汉唐旧说者渐多, 以朱熹为代表的学者为了消除旧解与《诗经》学发展的紧张对立状态, 再一次完成了对这一《诗经》学话语的意义转换。总之, 历史不断地层累, 而当下对这一命题的所有诠释, 几乎都是不同旧说的余绪。
一、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之本意
“思无邪”一语本出《诗经·鲁颂·駉》篇。该诗首章云:“駉駉牡马, 在坰之野。薄言駉者, 有驈有皇, 有骊有黄, 以车彭彭。思无疆, 思马斯臧。”其次章、三章、末章之内容与表达结构跟首章差不多完全一致, 唯各自侧重点稍异, 而收束语则分别作“思无期, 思马斯才 (在) ”“思无斁, 思马斯作”“思无邪, 思马斯徂”。
首先要明确的是, 《駉》诗各章之“思”均为语助词。宋项安世 (1129—1208) 已经指出:“‘思’, 语辞也。用之句末, 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显思’, 用之句首, 如‘思齐大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乐泮水’, 皆语辞也。” (《项氏家说·说经篇四·〈诗〉中“思”字》) 俞樾 (1821—1907) 评论道:“此说是也, 惜其未及‘思无邪’句。按:《駉》篇首章‘思无疆, 思马斯臧’……八‘思’字并语辞。” (1) 实际上, 项安世固未直接提及《駉》诗八个语例, 却也没有必要穷举, 读者理应举一反三。俞氏之前, 清儒陈奂 (1786—1863) 《诗毛氏传疏》持论与项说相类 (2) 。
“无疆”指马匹满布远野而无边无际。“无期”殆与“无疆”同意, 乃由形容时间无穷尽, 转而为形容空间无穷尽。有学者统计《殷周金文集成》之祈寿嘏辞, 发现“眉寿无期”出现了19次, “万年无期”出现了18次, “男女无期”出现了3次, “寿老无期”出现了2次, 而“万年无疆”出现了150次, “眉寿无疆”出现了78次, “寿无疆”出现了5次, “永命无疆”出现了4次, “眉考无疆”“年无疆”“寿老无疆”“千岁无疆”等各出现了2次 (3) 。“无期”言时间恒久, 是常见用法, 但它可以用原本形容空间无边际的语汇“无疆”来替代;反过来说, 道理完全一样。综合铭文及《駉》诗两方面的材料, 可知“无疆”“无期”之指涉对象每每发生时空转换, 时间性语汇可用以描述空间, 空间性语汇亦可用以描述时间。于省吾解“无期”为“无记”“无算” (4) , 意思虽是, 取径过于迂曲。
“无斁”本亦指时间之无终尽。《说文·攴部》云:“斁, 解 (懈) 也, 从攴睪声。《诗》云‘服之无斁’, 斁, 厌也。一曰终也。”值得注意的是“一曰”指涉的后一种说法。用此意, 则“无斁”实即“无疆”“无期”。“终”字可用于空间层面, 比如《庄子·外篇·天道》篇云, “夫道, 于大不终, 于小不遗, 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 渊乎其不可测也”;亦可用于时间层面, 比如《周易·系辞下传》云, “《易》之为书也, 原始要终, 以为质也” (注云:“质, 体也。卦兼终始之义也”) 。在《殷周金文集成》的祝寿嘏辞中, “霝冬 (令终) ”出现了63次, “霝冬霝后 (灵终灵后) ”出现了11次 (5) 。这些都是以“终”字言时间。故《駉》诗第三章, 以“无斁”形容空间之无终尽, 与其上文之“无疆”“无期”并无差异。于省吾读“斁”为“度”, 解“无度”为无数 (6) , 亦失之迂曲。
值得注意的是, 《诗三百》各篇若使用重章迭句, 处于各章相同功能位置的语汇, 其意指常常相同或相近, 至少往往可以贯通 (7) 。《駉》诗采取重章迭句之表达方式, 其第四章之“无邪”, 与前数章之“无疆”“无期”“无斁”处于相同的功能位置, 其意指与前三者一致, 即同样是形容空间之无边际, 便也毫不奇怪。于省吾尝考证从吾从牙之古字可通, 谓《仪礼·聘礼》“宾进, 讶受几于筵前”, 郑注谓“今文‘讶’为‘梧’”, 《山海经·海内北经》之“驺吾”, 《史记·滑稽列传》作“驺牙”, 《公羊传》文公二年 (前625) “战于彭衙”, 《释文》谓“衙……本或作‘牙’”, 等等, 均可为证。而“圄”与“圉”古同用。《说文·部》云:“圉, 囹圉, 所以拘辠人, 从从囗。一曰:圉, 垂也。”段注云:“他书作‘囹圄’者, 同音相叚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前712) “亦聊以固吾圉也”, 杜注谓“圉, 边垂 (陲) 也”。然则, “无邪”即“无圉”, 犹言“无边”, 指牧马之繁多 (8) 。此说甚是。李光地 (1642—1718) 曾说:“‘邪’字, 古多作‘余’解, 《史记》《汉书》尚如此。‘思无邪’, 恐是言思之周尽而无余也。观上‘无疆’‘无期’‘无斁’, 都是说思之深的意思。……‘思无邪’, 从来都说是‘邪正’之‘邪’……其实他经说道理学问, 至世事人情, 容有搜求未尽者, 惟《诗》穷尽事物曲折, 情伪变幻, 无有遗余, 故曰‘思无邪’也。” (9) 廖平 (1852—1932) 讲《大言赋》《小言赋》, 则谓《诗》“思无邪”读作“思无涯”, “涯”即《庄子·内篇·养生主》“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之“涯”;又谓“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 (绎) ”中, “疆”“期”“绎”三字亦皆言疆域, 非邪正之义 (10) 。20世纪80年代, 薛耀天据《史记·历书》“归邪于终”、裴骃集解谓“邪”音“余”, 而《左传》文公元年 (前626) 同句“邪”本作“余”, 断定在西汉, “邪”“余”二字还是同声通用的, 故“思无邪”之“无邪”犹言“无余”, 与“无疆”“无期”“无斁”同为无穷无尽之义 (11) 。李光地把“思”理解为实词, 其不当已经无须赘言。单就对“邪”和“无邪”的解释而言, 以上三说固然有所不同, 其取意则可谓异曲同工, 于氏之说相对完密。
以上解读的合理性, 回到《駉》诗原文, 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毛传谓, 骊马白跨曰驈, 黄白曰皇, 纯黑曰骊, 黄骍曰黄;……阴白杂毛曰骃, 彤白杂毛曰, 豪骭曰, 二目白曰鱼。这些不必细细解释, 大要均是指各种毛色的马。而所谓“无疆”“无期”“无斁”“无邪”, 正指言形形色色的马儿满布远野, 无边无际, 无穷无尽。首章之“臧”同“藏”———坰野无边际, 形形色色的马儿藏于其林丛薮泽之间。次章之“才”通“在”, 文献中屡见———坰野无尽头, 形形色色的马儿无所不在。三章之“作”指起, 末章之“徂”指往———坰野无终了, 形形色色的马儿卧起往来于其间, 亦无终了。这样理解文从字顺, 义理圆通, 故《駉》诗自身实可证明“无邪”本指无边际、无穷尽。
孔子引“思无邪”一语概括《诗三百》, 当是指三百篇之蕴藏既富且广, 无所不包, 是就其内容而言的 (12) 。欧阳修 (1007—1072) 《诗谱补亡后序》云:“盖《诗》述商、周, 自《生民》《玄鸟》上陈稷、契, 下迄陈灵公, 千五六百岁之间, 旁及列国、君臣世次, 国地、山川、封域图牒, 鸟兽、草木、鱼虫之名, 与其风俗善恶, 方言训故, 盛衰治乱美刺之由, 无所不载……” (《居士集》卷四一) (13) 借用这段话来帮助我们理解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之本意, 至少在方向上是十分正确的。
于省吾诠解《駉》诗“思无邪”之本意完全可以信从, 但他认为孔子谓“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 乃是“以思为思念之思, 邪为邪正之邪”, (14) 则显然是根据通常之见揣度孔子之心。
我们先看看“思无邪”之“思”。有学者谓, 《论语》“思”字二十五见, 一见于人名 (即“原思”) , 一见于“思无邪”, 余者全为实词 (15) , 以此证明“思无邪”之“思”当为实词。这样的考察并不具备完整的意义。
由过去几十年出土的简帛遗存来看, 传世文献在呈现孔子思想学说方面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出土文献中, 最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诗论》, 通常也被称为《孔子诗论》。在文本构成中起引导作用的“孔子曰”得到确认, “卜子曰”“子上曰”诸释文被排除以后 (16) , 《诗论》的基本性质变得十分清楚。首先, 《诗论》现存有六处“孔子曰” (此外当另有若干处遗失) , 它们差不多引导着这个文本的全部文字。其次, 《诗论》之内容是从各个层面上研讨《诗经》, 比如论普遍的诗的本质, 论《诗经》之全体, 论《诗经》各类, 论各部分50余首具体作品或其中具体诗句等。这两方面意味着, 《诗论》虽出于孔子后学之手, 其内容却主要是孔子本人的《诗经》学建构;《诗论》对认知孔子学说的价值约略与《论语》相类, 只不过它侧重于记录孔子以《诗》教的材料而已。总之, 《诗论》是现今所知与《论语》孔子论说《诗经》关系最明确的文献。
二、第一次意义置换之启基:关于“思无邪”之“思”
在孔子弟子至子思时代, “思无邪”的意义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换:“思”字实词化, 即被理解为“思想”“思虑”之“思”, 对《駉》诗“思无疆”“思无期”“思无邪”的接受因此发生了通盘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语丛三》此语尚可作另外一种解释。廖名春将“我”读为“义”, 认为“思无不由义者”就是解释“思无邪”, 同时也是对“思无疆”“思无期”诸语的限定, 易言之, “思无疆”“思无期”等都得“由义”, 都不能越出“义”的界限。李零亦读“我”为“义” (21) 。从小学层面上说, 读“我”为“义”不存在任何问题。从义理层面上说, 如果这种解释成立, 那么对“思无邪”的第一种意义置换便已经完成了。
综上所论, 《语丛三》“思亡彊 (疆) ”云云对“思无邪”诸语的意义置换, 只是将“思”当成了“思想”之“思”。这次意义置换并未明确落实到《诗经》学层面上, 但在儒学范域, 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的强势话语犹然在耳, 称这次意义置换同样有《诗经》学意义并不过分———这里所谓“《诗经》学意义”, 主要不是指对《駉》诗的解读, 而是指对《诗三百》以及孔子《诗》说的认知。
三、第一次意义置换之完成:关于“思无邪”
基于“思无邪”之“思”被理解为实词 (“神思”之“思”) , “思无邪”之“邪”差不多同时被理解成了“邪正”之“邪”。毫无疑问, 这牵动了对《诗经》与《诗经》学两方面的认知。
孔子开启了《诗三百》经典化 (即转化为儒家经典) 的旅程, 战国时期, 数代儒家学者不断加以诠释或再诠释, 《诗》最终被赋予了系统的儒学价值, 成了儒家重要经典;而至汉初, 这一进程又从民间学术层面跃升至官学层面, 《诗经》被立在学官, 《诗》的经典化最终完成。由此, 对传统《诗》学话语的认知、阐释或者再阐释, 都必然地在这一学说体系的基础上进行。
孔子以“思无邪”概括《诗》三百篇, 魏何晏 (190—249) 《论语集解》引汉儒包咸 (前7—65) 之言曰:“归于正。”北宋邢昺 (932—1010) 之正义云:“此章言为政之道在于去邪归正, 故举《诗》要当一句以言之。……《诗》虽有三百篇之多, 可举一句当尽其理也。……《诗》之为体, 论功颂德, 止僻防邪, 大抵皆归于正, 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俞樾曾评价说:“包注……止释‘无邪’二字, 不释‘思’字。邢疏……亦止释‘无邪’, 不及‘思’字。得古义矣。” (22) 这种观察可能有一点表面化。上揭二学者未释“思”字, 殆以之为常语而无须解释;且按照邢疏, 若无诗思之正, 《诗》之为体何以“论功颂德, 止僻防邪”, 而“大抵皆归于正”?“止僻防邪”本身就意味着“正”了。故包注、邢疏虽不及“思”字, 可思正之意却含蕴其中。南朝梁皇侃 (488—545) 《论语义疏》引卫瓘 (220—291) 曰:“不曰‘思正’, 而曰‘思无邪’, 明正无所思邪、邪去则合于正也。”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论语》古注, 直接关涉对孔子以“思无邪”为《诗经》学话语的理解。
在《诗经》学方面, 《韩诗外传》虽是外传体著述 (23) , 却较早显示了“思无邪”被理解为用心纯正的端倪。其卷三第二十一章云:
公仪休相鲁, 而嗜鱼。一国人献鱼而不受。其弟谏曰:“嗜鱼, 不受, 何也?”曰:“夫 (欲) [唯]嗜鱼, 故不受也。受鱼而免于相, 则不能自给鱼。无受而不免于相, 长自给于鱼。”此明于鱼为己者也。故《老子》曰:“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乎, 故能成其私。”《诗》曰:“思无邪。”此之谓也。
《外传》虽牵附《老子》“无私”云云, 可它以“思无邪”为思想之纯正, 则甚较然。《诗序》以“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解《駉》诗, 云:“《駉》, 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 俭以足用, 宽以爱民, 务农重谷, 牧于坰野, 鲁人尊之, 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 而史克作是颂。”郑玄 (127—200) 基于此意解“思无疆, 思马斯臧”, 曰:“臧, 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 反复思之无有竟已, 乃至于思马斯善。多其所及广博。”
总之, 包咸、郑玄以下, 绝大多数学者将“思”解释为动词性的思考或者名词性的思想, 将“邪”解释为“正邪”之“邪”, 将“思无邪”解为诗思之正。其所谓正, 自然是基于儒家政教规范而言的。此时, 关于《诗三百》的所有诠释都可以落实“思无邪”的取向, 这一取向因此就意味着三百篇或者“诗人”全都是向世间提供儒学价值的渊薮 (如上文所说, 并非本然如此, 这只是《诗》经典化的结果) 。我们几乎可以依据这一取向及其嬗变, 来区隔和定义《诗经》学发展的形态模式———就是说, 这一取向凸显了汉唐《诗经》学的特质。
之所以使用“《诗经》学形态模式”这一表述, 而不偏倚于历史时段, 是因为某一历史时段成熟的形态模式往往不会在后来的历史时段中消失, 往往会反反复复发挥其影响作用, 即使新的形态模式正在生成甚或已经成熟。作为一种形态模式的“汉唐《诗经》学”就是如此, 它至今依然会在某些历史层面上浮现 (24) 。比如北宋谢良佐 (1050—1103) 称:“君子之于《诗》, 非徒诵其言, 又将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 又将以考先王之泽。……思其危难以风焉, 不过曰‘苟无饥渴’而已 (案指《王风·君子于役》) 。若夫言天下之事, 美盛德之形容, 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与忧愁思虑之作, 孰能优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诗》者如此, 读《诗》者其可以邪心读之乎!” (25) 略早于朱熹 (1130—1200) 的学者张戒尝云:“孔子曰:‘《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 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其正少, 其邪多。孔子删诗, 取其思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 思无邪者, 惟陶渊明、杜子美耳, 余皆不免落邪思也。” (26) 吕祖谦 (1137—1181) 说得更加简洁:“仲尼谓《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诗人以无邪之思作之, 学者亦以无邪之思观之, 闵惜惩创之意, 隐然自见于言外矣。” (27) 这些论说虽皆出于宋人, 却都呈现着汉唐《诗经》学形态模式的特质。而张戒的说法, 再次明确了汉唐《诗》学形态模式的逻辑前提, 是孔子删诗或编《诗》。
四、第二次意义置换以及《诗》学内在冲突之消解
汉唐《诗经》学形态模式遭遇的严峻挑战, 来自对文本自身价值的认同。朱熹说:“今欲观《诗》, 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 只将元诗虚心熟读, 徐徐玩味。”又说:“……须先去了《小序》, 只将本文熟读玩味, 仍不可先看各家注解。看得久之, 自然认得此诗是说个甚事。”又说:“《诗》《书》略看训诂, 解释文意令通而已, 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 (28) 在文本的力量被释放后, 汉唐《诗经》学的整个体系便出现了塌陷。所以朱熹提出, 变风“多是淫乱之诗”, “今但去读看, 便自有那轻薄底意思在了” (29) 。《诗序》解《鄘风·桑中》云:“《桑中》, 刺奔也。”朱子则说:“此正文中无戒意, 只是直述他淫乱事尔。” (30) 总之, 朱熹认为, 就三百篇之本文而言, “思有邪”者正多。他指出:“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 则《桑中》《溱洧》之诗, 果无邪耶?……如《桑中》《溱洧》之类, 皆是淫奔之人所作, 非诗人作此以讽刺其人也。”又说:“若言作诗者‘思无邪’, 则其间有邪底多。” (31) 朱熹反对《诗大序》“变风发乎情, 止乎礼义”的说法, 称:“中间许多不正诗, 如何会止乎礼义?” (32) 朱熹基于文本自明性建构的认知还得到一般创作经验的支持。朱熹云:“诗者, 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 (《诗集传序》) 朱熹注孔子所说“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论语·泰伯》) , 强调“《诗》本性情”, “以《诗》观之, 虽千百载之远, 人之情伪只此而已, 更无两般”, “天地无终穷, 人情安得有异” (33) 。他批评前儒尽以美刺说诗, 曰:“大率古人作诗, 与今人作诗一般, 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 吟咏情性, 几时尽是讥刺他人?” (34)
在汉唐《诗经》学形态模式成熟以后, 朱熹《诗经》学说从各个方面看都称得上是与之并列的新的形态模式, 它绝对不是宋代《诗经》学的全部, 却足可命名为“宋代《诗经》学形态模式”。在这一学说体系面前, 汉唐儒者以诗人、诗思之正定义的“思无邪”这一《诗》学命题已经不能成立, 它跟这一新体系发生了严重冲突。在传统《诗经》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孔子的论说都受到高度的尊重。既然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 那么这一命题就不会被朱熹彻底抛弃, 再度进行意义置换于是成了历史的必然。 (35)
朱熹认为, 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 不是说“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 而是说《诗》之“用”归于使人“无邪”, 是《诗》之“立教如此”, 是读《诗》之“功用”如此。朱熹《论语集注》注孔子此言, 曰:“凡《诗》之言, 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 且或各因一事而发, 求其直指全体, 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 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 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朱子又说:“‘思无邪’, 如《正风》《雅》《颂》等诗, 可以起人善心。如《变风》等诗, 极有不好者, 可以使人知戒惧不敢做。大段好诗者, 大夫作;那一等不好诗, 只是闾巷小人作。前辈多说是作诗之‘思’, 不是如此。其间多有淫奔不好底诗, 不成也是无邪思?……今使人读好底诗, 固是知劝;若读不好底诗, 便悚然戒惧, 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 是此心之失。所以读《诗》者, 使人心无邪也, 此是《诗》之功用如此。” (36) 所谓“思无邪”者, “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 善为可法, 恶为可戒, 故使人‘思无邪’也”;“《诗》之立教如此:可以感发人之善心, 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诗》之功用“能使人无邪也” (37) 。朱熹认定《邶风·静女》《鄘风·桑中》《王风·大车》《郑风·将仲子》等几十首诗歌为“淫诗”, 却没有像王柏 (1197—1274) 那样力主把这些诗歌逐出《诗经》, 他认为孔子将这些诗歌编入三百零五篇, 目的是使读者“即其辞而玩其理以养心” (《诗集传·关雎》) , “淫诗”虽有邪志而无妨, “读三百篇诗, 善为可法, 恶为可戒, 故使人‘思无邪’也” (38) 。
这一《诗经》学形态模式凸显了《诗》学立教者的存在———很明显, 他就是通常所说删诗、编《诗》的孔子。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回到儒家《诗经》学最原初的立意来重新定义“思无邪”。太史公谓:“古者诗三千余篇, 及至孔子, 去其重, 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 (《史记·孔子世家》) 朱子则说得更加细致:“昔周盛时, 上自郊庙朝廷, 而下达于乡党闾巷, 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 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诗集传序》) 就“思无邪”这一《诗》学话语而言, 由朱子《诗》学表征的新的形态模式只是否弃了汉唐形态模式对它的定义, 孔子依然是这一体系的核心。
在《诗经》学的这一种形态模式中, 阅读主体必须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导性。———由于《诗三百》中存在“淫诗”, 由于其中思有邪者正多, 坚持“即其辞而玩其理以养心”的朱熹必然会强化阅读主体的自觉批判, 缺少这一点, 致力于使读者“思无邪”的立教期待就会落空。故朱熹云:“孔子之称‘思无邪’也, 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 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 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 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 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辨数而归其无邪于彼, 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 (39) 阅读的过程, 恰便是正心诚意的过程。《大雅·抑》曰:“视尔友君子, 辑柔尔颜, 不遐有愆。相在尔室, 尚不愧于屋漏。”朱子释之云:“言视尔友于君子之时, 和柔尔之颜色, 其戒惧之意, 常若自省曰, 岂不至于有过乎?盖常人之情, 其修于显者, 无不如此。视尔独居于室之时, 亦当庶几不愧于屋漏, 然后可耳。……此言不但修之于外, 又当戒谨恐惧乎其所不睹不闻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动而敬, 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显, 诚之不可掩如此。’此正心诚意之极功, 而武公及之, 则亦圣贤之徒矣!”朱熹注《论语》孔子蔽《诗》以“思无邪”事, 引范祖禹 (1041—1098) 之言曰:“《诗》之义, 主于正己而已。故一言可以蔽之, 思无邪是也。学者必务知要, 知要则能守约, 守约则足以尽博矣。经礼三百, 曲礼三千, 亦可以一言蔽之, 曰毋不敬。” (40) 朱子自己又说:“‘毋不敬’, 《礼》之所以为教;‘思无邪’, 《诗》之所以为教。” (41) 在朱熹的阐释体系中, 以“思无邪”概括《诗三百》, 跟以“毋不敬”概括“经礼”“曲礼”, 是一样的道理。
朱子《诗》学代表的这种新的《诗经》学形态模式虽然重新给出了一些定义和设计, 目的则仍在实现《诗经》所负载的儒学价值 (毫无疑问, 儒学价值本身也有承继前人和重新解释的问题) 。故朱子论学《诗》之大旨云:“本之二《南》以求其端, 参之列国以尽其变, 正之于《雅》以大其规, 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 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诗集传序》) 朱子将读经纳入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完整模式中, 同时, 其《诗》教还从“《诗》”向一般的“诗”延伸。故曰:“诗者, 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 则其所感者无不正, 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 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 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诗集传序》)
朱子《诗》学代表的这种新的形态模式可以说是儒学内部“拨乱反正”的结果。不过, 这一体系既释放了文本, 又释放了阅读主体, 最终会导致一切经学附会的崩塌, 而走向现代《诗经》学形态模式的建构。这恐怕是朱子本人未尝料及的更伟大的历史意义。
余论
孔子最先将“思无邪”定义为《诗经》学话语, 这一定义, 不出意外地成了见载于竹书《诗论》以及传世《论语》等著述的孔子《诗经》学形态模式的表征。此后, 对该话语的重新定义以及对其原初意指的复归 (这种复归不是重复孔子, 而是基于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来认同孔子) , 则又表征了《诗经》学另外几个具有复杂关系的重要形态模式, 比如汉唐《诗经》学形态模式、朱熹或者宋代《诗经》学形态模式、现代《诗经》学形态模式等。不可否认的是, 现代《诗经》学研究大抵都承袭着上揭《诗经》学的历史存在———或者重复某种旧有模式, 或者混合几种旧有模式, 或者拾取甚至曲解某种旧有模式接着说。
当下有学者说:“‘思无邪’作为孔子最重要的诗论, 其原始意义清晰、明朗。孔子从礼的层面给于界定, 认为诗即周代礼乐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诗三百篇合于礼。” (42) 又有学者说, 孔子以“思无邪”一言概论《诗三百》, “是对《诗经》全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内容作出的合乎其哲学和道德观念的肯定评价”。又称:“孔子欲发挥《诗经》在上层社会和中下层社会的政治作用, 是本于《诗》是‘思无邪’的;……因此可以说, 在充分相信《诗经》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思无邪’的论断, 乃是孔子政治、哲学、教育等各种思想和观点的协奏曲中一个格外响亮、格外重要的音符。” (43) 还有学者说:“毋庸置疑的是, 无论后人对‘思无邪’作何种解释, 它的意思仍是说:《诗经》中的所有篇章都合乎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 (44) 这些论断不过是重复汉唐《诗经》学的形态模式而已, 孔子本人实际上并未如此定义“思无邪”;换句话说, 这些论断仅仅是从汉唐《诗经》学的形态模式上看才正确, 跟孔子本人的《诗经》学形态模式则相距甚远。
有学者提出:“《诗》是周代礼乐文明的重要载体, 是周代贵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重要方式, 孔子以《诗》为教, 是他承传周代礼乐文明的文化理想的重要实现途径。……因此, ‘思无邪’既不是对《诗》的思想内容的概括, 也不是强调学《诗》、读《诗》之法, 而是指称《诗》全面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 实质是强调学《诗》的重要意义。” (45) 对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本意的这种论析相当含混。乍看起来, 它接近孔子的原初立场, 但将孔子之意归结到“《诗》宽泛广阔、包罗万象的实用功能”亦即“学《诗》的重要意义”上, 接近的则是朱子以《诗》之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来定义“思无邪”的理念;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其实就是对《诗》的内容的认知, 这一点, 上博《诗论》便是有力的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 今人常常基于对旧说的误读“接着说”。比如, 有学者提出:“……对礼崩乐坏的痛心疾首, 对‘克己复礼’的热忱执着的追求, 促使孔子对‘诗言志’的‘志’予以特殊的限定, 即要求其‘无邪’。他企图以《诗》‘无邪’来取代‘诗言志’。”又称:“‘无邪’论由于它根植于社会的政治、伦理、道德的土壤里, 因而理论本身带有浓重的社会政治色彩, 而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片面性。‘言志’论, 尽管也不是一个纯文学的命题, 却由于它是‘诗用话传达出内心的意向’, 既表现了广阔丰富的社会内容, 又展示了主体情感意志抒发及其内在生命活力的独创性和多样性, 它无疑更符合艺术规律。” (46) 这大抵是基于汉唐《诗经》学形态模式, 来诠释孔子以“思无邪”概括《诗三百》的意图, 进一步则将该命题与“诗言志”对立 (质言之, 此说与汉唐《诗经》学家对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的解读仍有差异, 即汉唐《诗经》学家认为孔子之意是说《诗三百》呈现的诗人之思纯正无邪, 而此说则认为孔子之意是要求诗人呈现无邪之志) 。论者误解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之本意, 无需赘言。他甚至还人为制造了孔子所谓“思无邪”跟其“诗言志”观的暌隔。上博馆藏《诗论》第三章称“ (诗) 亡 (无) (隐) 志”, 作为该文本的核心意指之一, 此语其实已从诗作认知角度上确认了诗言志。上博简文《民之父母》及传世《礼记·孔子闲居》均记载了孔子的“五至”说, 前者记孔子称“勿 (物) 之所至者, 《志 (诗) 》亦至安 (焉) ”, 后者记孔子称“志之所至, 《诗》亦至焉” (47) 。郭店简文《语丛一》综论六经, 则谓:“《诗》, 所以会古含 (今) 之恃 (志) 也者。”孔子《诗经》学形态模式根本就不存在用“思无邪”替代“诗言志”的情况———“诗言志”对于三百篇之“思无邪”其实是前提性的。
又比如, 朱熹《论语集注》解孔子以“思无邪”概论《诗三百》之意, 引程颐 (1033—1107) 之言说:“思无邪者, 诚也。”今人或将程、朱诠解“思无邪”之“诚”理解为真实不虚, 谓:“子曰:‘诗, 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言志抒情, 贵在‘思无邪’, 即真诚不虚假。” (48) 朱子确曾慨言, “思无邪者, 诚也”一语, “每常只泛看过”, “子细思量, 极有义理。盖行无邪, 未是诚;思无邪, 乃可为诚也。”或问朱子:“‘思无邪, 诚也’。所思皆无邪, 则便是实理。”朱子回答:“下‘实理’字不得, 只得下‘实心’字。言无邪, 也未见得是实;行无邪, 也未见得是实;惟‘思无邪’, 则见得透底是实。”朱子还说:“‘思无邪, 诚也’, 是表里皆无邪, 彻底无毫发之不正。世人固有修饰于外, 而其中未必能纯正。惟至于思亦无邪, 斯可谓之诚。” (49) 这样的诠释可能有更强的一般诗学的价值, 但它不仅误解了孔子本意, 偏离了孔子《诗经》学形态模式, 而且也不符合汉唐《诗经》学形态模式以及朱子所表征的《诗经》学新的形态模式。总之, 今人将孔子以“思无邪”综论《诗三百》的主旨解释为泛泛的真诚, 往往是错误地理解和衔接了朱子的学说体系。
注释(参考文献):
1 (22) 俞樾:《春在堂全书》第三册, 第182页下, 第182页下, 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2 有学者认为, 至陈奂才提出《駉》诗八个“思”字均为语助词, 而一般解者俱以为“思虑”之“思” (参阅薛耀天:《“思无邪”新解:兼谈〈诗·駉〉篇的主题及孔子对〈诗〉的总评价》, 《天津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3期) , 殆亦非是。
3 孙孝忠:《周代的祈寿风与祝嘏辞》,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6期。
4 (6) (8) (14) 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 第116页, 第116-117页, 第117页, 第117页, 中华书局2003年版。
5 孙孝忠:《周代的祈寿风与祝嘏辞》,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6期。
6 参阅常森:《论共时性理解对〈诗经〉〈楚辞〉研究的意义》, 《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
7 李光地:《榕村语录》, 陈祖武点校, 第243页, 中华书局1995年版。
8 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 (十) , 第359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9 参见薛耀天:《“思无邪”新解:兼谈〈诗·駉〉篇的主题及孔子对〈诗〉的总评价》, 《天津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3期。
10 薛耀天称, 孔子用“思无邪”来概括《诗三百》, 是指《诗三百》内容极其丰富, 可以给人多种多样的知识 (参见氏著《“思无邪”新解:兼谈〈诗·駉〉篇的主题及孔子对〈诗〉的总评价》) ;业师孙以昭先生谓孔子借用引申, 发挥为“广阔无边、包罗万象”之意, 用来概括《诗三百》丰富广阔的内容 (参见氏著《孔子“思无邪”新探》,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4期) , 甚是。
11 欧阳修著:《欧阳修诗文集校笺》, 洪本健校笺, 第1057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2 参见余群:《从产生背景看“思无邪”的本义》,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2005年第1期。
13 参见李零:《参加“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几点感想》, 《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 第130-132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马承源:《〈诗论〉讲授者为孔子之说不可移》, 陈佩芬等编:《马承源文博论集》, 第361-366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濮茅左:《关于上海战国竹简中“孔子”的认定---论〈孔子诗论〉中合文是“孔子”而非“卜子”、“子上”》, 《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辑。美国学者夏含夷 (Edward L.Shaughnessy) 清楚地回顾了这一争议的解决过程, 参见氏著:《重写中国古代文献》, 周博群等译, 第20-2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14 本文引用简帛文献一般采用严式隶定, 以方便读者对照简帛原典, 以下不再一一说明。引文文字加方框表示补残缺, 方块表示残缺不能补者, 而圆括号中的文字一般是通行写法或者简注。
15 关于遒人采诗言之说, 参阅常森:《论以礼解〈诗〉之限定---从〈诗论〉评〈关雎〉说开去》, 《国学研究》第39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6 刘钊疑“思亡不邎我者”相当于《駉》诗之“思无斁” (见氏著《郭店楚简校释》, 第219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版) , 殆非。一者意义实不能说通, 二者所处位置与原诗有参差。“”字从陈松长隶定, 读作“邪” (参见氏著《郭店楚简〈语丛〉小识》 (八则) , 安徽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22辑, 中华书局2000年版) 。
17 参阅常森:《简帛〈五行〉篇与〈尚书〉之学》, 何志华、沈培等编:《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116-120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8 参阅廖名春:《新出楚简试论》, 第78页, 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 (增订本) , 第149、152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 汉代《诗经》著述内、外传体之区隔及其各自特质, 参阅拙文《论汉代〈诗经〉著述之内外传体》, 《国学研究》第30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0 本文侧重于从历时性层面上观照对象, 因此不细致考究不同《诗经》学形态模式的共时性呈现或叠加问题, 但显然并未忽视。对于“思无邪”作为《诗经》学话语的不同历史意涵的共时性呈现或叠加, 笔者也并不漠视, 本文仅仅是不在这一层面上过多用力而已。
21 (27) 黄灵庚等主编:《吕祖谦全集》第4册, 第1页, 第109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2 张戒:《岁寒堂诗话笺注》, 陈应鸾校注, 第107页, 巴蜀书社2000年版。案:据陈应鸾考证, 张戒卒于绍兴三十年 (1160) , 参阅前著之“前言”, 第3-6页;并参氏著《张戒生平及其诗话作时略考》, 《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
23 (29) (30) (31) (32) (33) (34) (36) (37) (38) (41) (4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王星贤点校, 第2085、1653页, 第2068、2067页, 第2068页, 第539、538页, 第540页, 第2083-2084页, 第2076页, 第546-547页, 第539、538页, 第539页, 第545页, 第543、544页, 中华书局1994年版。
24 可以作为旁证的是, 《诗经·召南·野有死麇》未被朱熹斥为淫诗, 跟传世《论语》曾记载孔子高度推尊《周南》《召南》有密切关系。《论语·阳货》篇记载子谓伯鱼曰:“女 (汝) 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25 朱熹:《朱子全书》第23册, 第3371-3372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6 朱熹:《朱子全书》第7册, 第64页。案:“毋不敬”一语出于《礼记·曲礼》。
27 姚娟:《“思无邪”新论》,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8 蒋长栋:《孔子“思无邪”本义新探---与詹福瑞先生商榷》, 《怀化师专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2期。
29 董晔、李妍妍:《〈诗经〉和〈论语〉中的“思无邪”比较》, 《唐都学刊》2006年第3期。
30 赵玉敏:《“思无邪”本义辨正》, 《学术交流》2007年第6期。
31 吴瑞霞:《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2期。
32 这两种表达本旨一致, 而侧重点不同, “志”为心之所之, “勿 (物) ”则是心之所之的对象。不过, “勿 (物) 之所至者, 《志 (诗) 》亦至安 (焉) ”一说, 可能更契合孔子以“思无邪”概括《诗三百》的本意。
33 杨化玉:《化玉诗草》, 李一序, 第2页,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思无邪”作为《诗经》学话语及其意义转换>附全文PDF版下载:
http://www.lunwensci.com/uploadfile/2018/0720/20180720124620365.pdf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jiaoyulunwen/1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