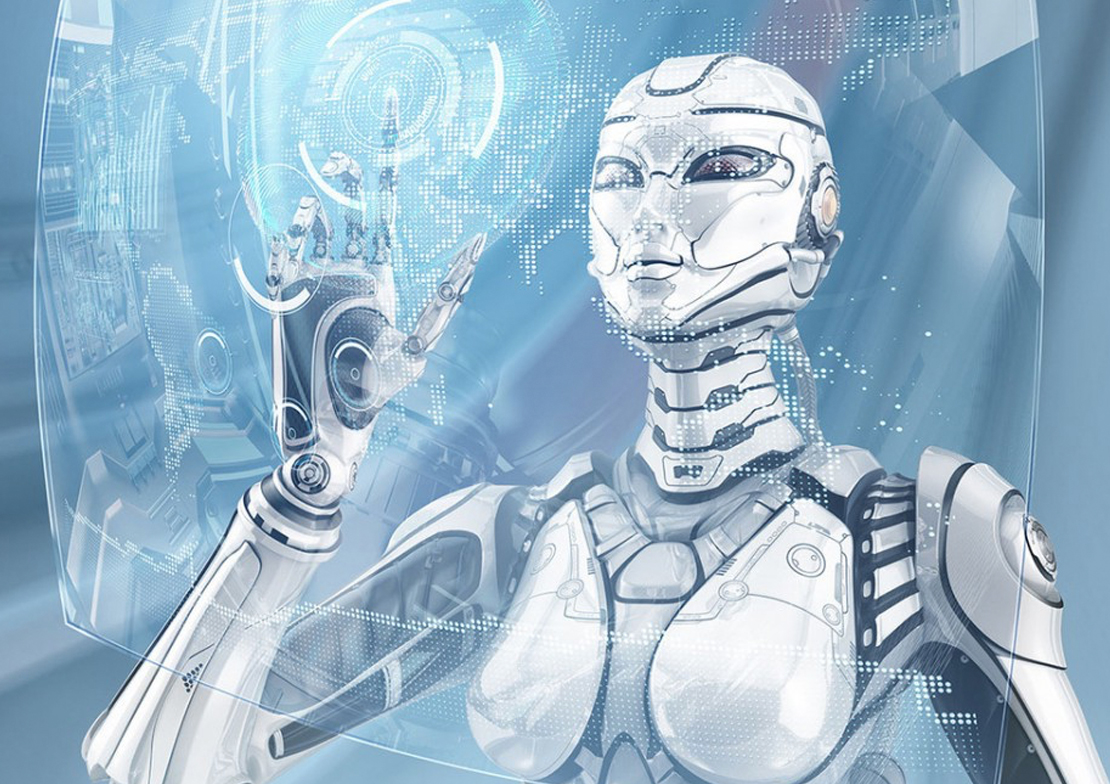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要:人工智能生成物符合著作权法的客观性标准,应受到保护。当前,学术界提议扩大“作者”一词的外延,使其涵盖非人类作者,并根据职务作品、法人作品、邻接权及认定“机器人格”等确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所属权。上述模式均有某些缺陷。在机器创作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下,我国可以制订有关人工智能生成物使用的法规并采用“孤儿作品”的保护模式,避免讨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主体问题,进而允许相关人员在事后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带来的经济利益进行分配,以发挥著作权法的激励作用。
关键词: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孤儿作品保护
On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Xia Shaoji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Hubei,430000)
Abstrac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meet the objective standard of copyright law and should be protected.At present,the academic circles propose to exp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term"author"to cover non-human authors,and determine the ownership of the content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cording to the work of duty,the work of legal person,the right of adjacency and the recognition of"machine personality".The above modes have some defects.On the premise that machine cre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China can formulate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and adopt the protection mode of orphan works to avoid discussing the subj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Further,it is allowed to distribute the economic benefits brought by the content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fter the event,so as to play the incentive role of copyright law.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copyright protection;protection of orphan works
一、引言
“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著作权案”是全国第一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案,本案中,人工智能生成物被司法机关排除在作品之外,并否认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作者并享有著作权。法院虽然认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但是受制于立法空白,无法援引法律原则来予以保护。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其生成物质量也不断提高[1]。2020年,腾讯研发的对联机器人创作的对联堪比大师之作。2021年,彩云小梦机器人可以对输入的任意文学作品片段进行续写。在美国,NVIDIA公司的GAN能够生成现实中不存在的人脸。基于种种因素,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体系必须提上日程。目前,学界已有许多解决这一问题的构想,如“雇佣作品保护模式”“邻接权保护模式”“孳息保护模式”“拟制人工智能人格保护模式”及“孤儿作品保护模式”等。其中,“孤儿作品保护模式”能够弥补其他四种保护模式的不足,在实践中更容易被实施。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指应用某种算法、规则和模板生成包括科技产品及文艺作品等一系列具备独创性的特定表达内容的总称。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受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与著作权客体相似
对于著作权的客体[2],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创造性的智力成果,而刘春田教授将知识产权客体视为知识本身,冯晓青教授则认为边缘客体会随着技术进步纳入著作权客体的范围。促进文学和艺术的繁荣是我国制定著作权法的宗旨,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应纳入著作权法范围内。人工智能将符号表达整合到了具有完整形式的作品中,如歌曲和绘画,这符合上述学者对著作权客体及其未来发展的预期。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实质独创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对“作品”给出的定义可知,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学者王迁认为,独创性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劳动者的原创行为,第二种是劳动者的再创作。现阶段,人工智能生成物大多属于第二种情况[3]。目前,人工智能可以运用“神经网络”技术,即通过简单计算机处理单
元互相连接,形成模拟人脑运行的复杂网络系统。这样,人工智能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也能对信息进行分析与筛选,形成自己的判断,并通过迭代对算法进行“遗传”。在实践中,人工智能生成物已具有“独创性”的特征,不能简单地将其认为是人类的创作。
(三)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有利于市场稳定
一方面,大量不受版权保护的人工智能作品纷纷出现[4]。在法律真空区,人们只需支付相应对价便可随意使用人工智能作品,这直接导致了人工智能生成物价值的贬损。另一方面,市场缺乏对人工智能作品版权的监管也从侧面助长了部分人恶意利用人工智能作品的行为。这无疑会对著作权市场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也不利于社会利益的平衡。
图1智能生成物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模式
学界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尚处在初步探索中,其主要分为两大派别,一派主张通过化用、扩张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手段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保护;另一派更为激进,主张赋予人工智能著作权主体地位,以解决生成物权属争端等核心问题[5]。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雇佣作品保护模式
一些学者将当前雇佣作品规则类推,提出了雇佣作品保护模式[6]。雇佣作品是指基于雇佣关系或委托关系的创作行为产生的作品。在这种模式下,人工智能被视为在自然人或法人控制下的雇员。因此,其生成物可被视为雇佣作品分类中的雇员作品,雇主也就是人工智能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是生成物在投资和创作意志方面的动因。但是,该模式难以解决投资者、研发者、所有者、使用者利益竞合的问题。这是由于在传统意义上,这一模式更倾向保护投资者利益,而仅对其他主体赋予署名权。这与实践中使用者对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更大贡献这一事实相悖。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邻接权保护模式
根据邻接权本身的开放属性,相关人员可以将人工智能生成物增设为新的邻接权类型,并明确权利主体、内容、保护期限等具体规则。但是,这种方式存在以下局限。首先,这一模式无法满足人工智能生成物多元主体的利益分配需求。人工智能生成物利益分配涉及的主体相对复杂,包括人工智能的设计者、所有者、使用者等,而邻接权保护主体限定为著作权人。其次,人工智能生成物与邻接权保护对象的性质不匹配。邻接权保护的对象是作品传播者的利益,是再现、复制和传播他人作品时产生的权利,其并不会产生新的作品。但是,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学习素材得到模型,不过这个模型生成的作品却属于一种创作而不属于对原有作品的传播。最后,邻接权是版权制度的补充,旨在保护不符合独创性标准的演出、音像制品、无线电信号等权利客体。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孳息保护模式
人工智能生成物被该模式定义为孳息[7]。孳息是指由原物所生的物或创造的收益。该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创作物应当属于人工智能程序与使用数据相结合而产生的孳息。
这一模式依然存在以下缺陷。第一,无法精确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作为孳息对应的原物。人工智能的生成过程依赖大量数据。如果根据对孳息产生贡献度大小来判定原物的理论,此时的原物可能是人工智能,也可能是数据。这导致人工智能生成物出现“双重孳息”的属性。其次,当事人对孳息归属意思自治范围需要限制。《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一条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判定其归属。不难看出,人工智能生成物可能由于当事人的约定不受保护而放任其进入公共领域,进而可能存在被侵权的风险。
(四)人工智能拟制人格制度保护模式
建立人工智能拟制人格制度一直是热门议题。例如,2016年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在《就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的报告草案》中提议,为机器人创建“电子人格”。根据这份报告草案可知,当机器人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或独立地与第三方互动时,就拥有特定的权利和法律义务。此时,第三人造成的侵权责任通常与其背后的特定自然人存在关系。在不远的将来,当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得到广泛应用后,在侵权行为发生时,法律将难以迅速做出反应来确定责任主体。
然而,人工智能及其产品本质上是人类的劳动产品,若将人工智能定义为著作权主体,则实质上就是把人工对象置于实际创造者之上。这可能导致人的价值的贬损,违背了法律应当为人们发挥自身价值提供支持的原则。
法人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必须独立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虽然人工智能拟制人格构想能解决人工智能生成物主体和权利所有权等问题,但是人工智能本身不具备独立人格的物质条件,例如拥有财产。尽管人工智能的人格可以进行法律拟制,但它们不能独立进行民事和商业活动,因此,对于人工智能主体而言,建立代理人制度也是不现实的。
四、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路径的探索
上述四种模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这些缺陷可能会使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受到主体纠缠不清或保护不够全面等问题的限制。孤儿作品保护模式能有效回避人工智能生成物主体这一问题,并着眼于解决利益的现实分配,实现著作权立法的根本目的[8]。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孤儿作品保护模式
孤儿作品问题的本质是作品使用者无法与作品版权者取得有效联系,无法得到使用作品的许可,这导致作品使用者在使用作品时陷入困境。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孤儿作品属性。
第一,在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即使人工智能有明确的所有者和用户,自然人也不是作者,因此很难在作品上签名。即使发现人工智能生成物与自然人有某种联系,也难以确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原因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过程是多主体参与的过程。第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传播需要利用互联网形式,权利人身份不明的问题让使用者难以与权利人取得联系。
(二)孤儿作品保护模式的独特优势
1.解决主体争端
与邻接权和雇佣作品模式相比,孤儿作品保护模式可以规避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主体问题,提高知识要素的流通性和利用率。在该模式下,他人可以先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物,再通过提存或事后补偿的方式补全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人的利益。
2.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
孤儿作品保护模式与邻接权和雇佣作品保护模式相比,更有利于平衡人工智能投资者和产品用户的利益。另外,两种模型将人工智能程序和人工智能产品的版权归投资者所有,有过度保护的嫌疑。但在实践中,人工智能用户一般会付出相应的对价,并在创作过程中添加具体的创作命题和规则。即使他们没有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参与。孤儿作品模式允许用户先行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物[9]。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投资者对产品使用的垄断问题,使利益分配更加均衡。
3.提高人工智能生成物使用率
提高作品使用率和激励创作是著作权法的立法目标[10]。孤儿作品保护模式就是这一立法目标的具体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闲置而未被著作权人重视的人工智能生成物资源,将著作权属争议搁置,尽早将这些资源投入知识产权市场,并对其加以利用,这无疑是符合立法目标的。
(三)孤儿作品保护模式的完善
1.限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类型
孤儿作品有两种状态,即推定的无权人孤儿作品与事实的无权人孤儿作品。在实践中,只有推定的无权利人孤儿作品才能被权利人收取使用费。因此,我国在立法设计中,应明确孤儿作品的范围,具体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美国的限制模式、北欧部分国家的集体授权模式及加拿大、匈牙利等国家的强制许可模式。
2.确定勤勉检索义务
美国《孤儿作品法》首创“勤勉检索”原则,随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发布《孤儿作品使用原则》,并将其列为首条原则,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11]。第一,潜在用户在使用孤儿作品前应当合理且主动地搜索著作权所有者。第二,用户不仅要调查当前著作权人的身份和地址,还要了解获取上述信息的所有可能方式。第三,使用者在检索过程中必须保持理性。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潜在使用者如果能证明该作品在互联网络、著作权登记机关、著作权数据库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无法查明其著作权人,就有权将上述作品作为孤儿作品加以使用。
3.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以适应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冲击
为使人工智能作品的使用不受限制,我国必须建立著作权管理机构,并对相关制度加以改进。一方面,建立自治和独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提高集体管理组织的管理和运作的成熟度;另一方面,加强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的现代化发展,完善著作权登记注册程序、作品检索程序、作品授权程序、作品使用监督程序和作品使用费支付程序等。
4.公益使用免费
企业在考虑知识产品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忽略其带来的社会效益。解决人工智能生成物难以确定其权利人的问题的核心目的是促进对这些作品的使用,因此,无需采用孤儿作品申请批准和预付款制度。真正的无主人工智能生成物应当进入公共领域。如果用户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用于教育、宗教、慈善,或者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及公共广播机构等方面,则仅需向权利人证明其使用目的,无需支付使用费亦可使用。
五、结语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创新能力的代表,冲击着以往以“人”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体系。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伦理学和经济学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著作权主体、客体到内容,人工智能却动摇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固有观念。在立法时,相关人员必须具备前瞻性思维,且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制度,并将人工智能技术对知识产权体系的冲击视为一次法律变革的机会,革新传统知识产权法中“独创性”必须源于人的观点。因此,相关人员可以效仿孤儿作品保护模式构建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制度。这不但有利于加强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还有助于保护人类作品免受无序市场的冲击、创新现有著作权保护模式,以便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智力成果领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林爱珺,彭琪月.人工智能图表作品著作权归属探析——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百度网讯抄袭案[J].南方传媒研究,2019(4).
[2]焦和平.人工智能创作中数据获取与利用的著作权风险及化解路径[J].当代法学,2022(4).
[3]王文敏,高军.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信息分析的著作权例外规则[J].图书馆论坛,2020(9).
[4]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5).
[5]吴汉东,王毅.著作权客体论[J].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0(04).
[6]刘春田.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7]冯晓青.著作权扩张及其缘由透视[J].政法论坛,2006(06).
[8]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9]巫影,陈定方,唐小兵,朱石坚,黄映云,李庆.神经网络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06).
[10]黄晖,朱志刚译.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1]吴雨辉.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问题、争议及其未来可能[J].现代出版,2020(06).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jisuanjilunwen/47459.html